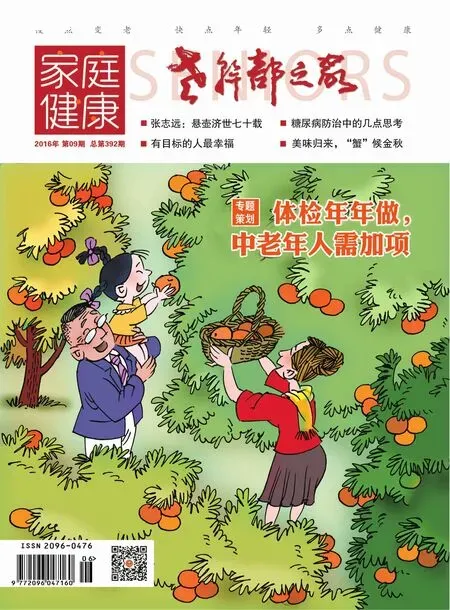说生病
文 贾平凹
说生病
文 贾平凹

有一种病,在身上七八年不愈,要想想,这一定是有原因了。泄露了不该泄露的天的机密?说破了不该说破的人的隐私?上帝的阴谋最多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那么,这病就特别的有意义,自感是一位先知先觉,勇敢的普罗米修斯,甘受惩罚吧。或许,人是由灵魂和肉体两方结合的,病便是灵魂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契合出了问题,灵魂已不能领导了肉体所致,一切都明白了吧,生出难受的病来,原来是灵魂与天地自然在做微调哩。
真如果这么对待了生病,有病在身就是一种审美。静静地躺在床上,四面的墙涂得素白,定着眼看白墙墙便不成墙—如盯着一个熟悉的汉字就要怀疑这不是那个汉字—墙幻做驻云,恰有穿白衣白帽白口罩的“天使”女子送了药来。吊针的输液管里晶莹的东西滴滴下注,假想这管子一头在天上,是甘露进入身子。有人来探视,都突然温柔多情,说许多受感动的话,送食品,送鲜花。生了病如立了功,多么富有,该干的事都不干了,不该享受的都享受了,且四肢清闲,指甲疯长,放下一切,心境恬淡,陶渊明追求的也不过这般悠然。
最妙的是太阳暖和,一片光从窗子里进来跌在地上,正好窗外有一株含苞的梅,梅枝落雪,苞蕾血红,看做是敛羽静立的丹顶鹤,就下床来,一边掖了下坠的衣襟一边在光里捉那鹤影。刚一闷住,鹤影已移,就体会了身上的病是什么形状儿的,如针隙透风,如香炉细烟,如蚕抽丝,慢慢地离你而去的呢。
暂不要来人的好,人越多越寂寞,摆一架古琴也不必装弦,用心随情随意地弹。直挨到太阳转黑月亮升起,插一盘小电炉来煎中药,把带耳带嘴的砂锅用清水涤了又涤,药浸泡了,香点燃了,选一个八卦中的方位和时分,放上砂锅就听叽叽咕咕的响声吧。药是山上的灵根异草,采来就召来了山川丛林中的钟毓光气,它们叽咕是酝酿着怎么扶助你,是你的神仙和兵卒。煎过头遍,再煎二遍,满屋里浓浓的味,虽然搅药不能用筷子,更不得用双筷—双筷是吃饭的—用一根干桃棍儿慢慢地搅,那透过蘸湿了的蒙在砂锅上的麻纸上蒸汽弥漫,你似乎就看到了山之精灵在舞蹈,在歌唱,唱你的生命之曲。
躺在床上吧,心可以到处流浪,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从未有过这般的勇敢和伟大,简直可以要作一部类屈原的《离骚》。当你游历了天上地下,前世和来世,熄了灯要睡去了,你不妨再说一些话,给病着的某一部位说话。你告诉它:呀,你对我太好了,好得使我一直不觉得你的存在。当我知道了你的部位,你却是病了。这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终于明白了在整个身子里你是多么的重要,现在我要依靠你了,要好好保护你了,一切都拜托你了!人的身体每一处都会说话,除嘴有声外,各部无音,但所有的部位都能听懂话的,于是感受会告诉心和大脑,那有病的部位精神焕发,有了千军万马的英雄在同病毒战斗。什么“用人不疑”的仁,什么“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瞬间里全体会得真切和深刻。
生病到这个份儿上,真是人生难得生病,西施那么美,林妹妹那么好,全是生病生出了境界,若活着没生个病,多贫穷而缺憾。佛不在西天和经卷,佛不在深山寺庙里,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生病只要不死,就要生出个现世的活佛是你的。
- 老干部之家(健康)的其它文章
- 读懂体检报告
- 编读往来
- 中老年人应该体检什么项目
-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亮点解读
- 健谈
- 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