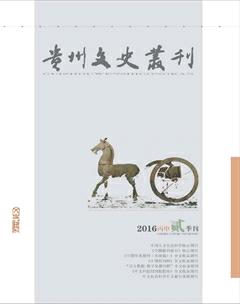发愤说:儒家人生理想下文士的焦虑与救赎
刘 楚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发愤说:儒家人生理想下文士的焦虑与救赎
刘楚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三不朽”的人生理想和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古代文士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可以发掘文士发愤背后的个人境遇和集体意识,以及发愤说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总体而言,在政治统治较稳固,士人入仕有制度化保障,儒家稳居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时代,文士追求“立德、立功”的心理焦虑会更突出;而在政治现实不尽如人意,儒家思想遭到人们质疑的时代,文士则常通过肯定“立言”而努力达到自身身份认同,其发愤为文的艺术性、政治性也得到凸显。对古代文士而言,发愤为文既是其人生理想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化解其心理焦虑、反抗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强大能指秩序的一种自我救赎。
发愤说 文士 “三不朽” 文化研究
对于发愤说,人们往往侧重于揭橥屈原“发愤以抒情”及孔子“诗可以怨”对后代文士的影响,却忽视了“三不朽”的等级式人生理想和孔子树立的积极进取的儒家人生态度对后代文士造成的“影响的焦虑”;往往侧重于阐释发愤说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和审美意义,却忽视了文士发愤背后的集体意识和权力关系;往往侧重于揭示文士个人的穷通际遇与发愤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语境及其影响下的士风与文士发愤“立言”之间的关联。这就需要从审美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不再只是“测量艺术象牙塔的结构和造型,而是寻找规训着这结构和造型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①冯黎明:《文化研究:走向后学科时代》,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1页。。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观照文士发愤背后的个人境遇、集体意识和权力关系,揭示儒家人生理想、人生态度对一代代古代文士所造成的心理焦虑,并对发愤说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探寻其在不同时代内涵的延续与新变。
一、士之人生理想与“发愤”
春秋战国是士阶层崭露头角的时代。王纲解纽、战事频仍,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对有助于加强其统治的士极尽笼络恩遇之能事,但孔子认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②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页。,庄子选择像龟一样自由地“曳尾于涂中”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4页。,都体现士以各自信守的“道”为凭借,对统治者的权势并非一味的盲从、屈服,而对个体的尊严和理想有更多的坚守。其时,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才能获得极大的发挥空间,士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和人生理想也有更加自觉的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叔孙豹的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8页。叔孙豹提出 “三不朽”,认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于实现“立德、立功、立言”,并认为三者包含了由上而下的等级次序——道德的树立最高,现实功业的建立次之,流传久远、泽被后世的言论的确立再次之。在“立言”内部,又有高低等级之分,具有审美意义的文章与安邦济世之言相较,毕竟为第二等事。
对“三不朽”人生理想的追求,儒家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子堪称表率。在为学上,夫子自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页。;在教学方法上,他认为应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页。孔子这里的“愤”是落实在求学上的,指人内有郁结的心理状态,但仍不失“求通”的主动选择和不尽追求。整体而言,孔子的“发愤”体现了他勤奋努力的入世精神,以及积极有为、昂扬向上和重视践履的人生态度。《论语·子罕》载,“牢曰:‘子云,‘吾不试, 故艺'”。刘宝楠《论语正义》注:“试,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见用,故多技艺。”③(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1页。孔子处在其学说不为统治者所用的境地时,没有曲学阿世,也终究没有“乘桴浮于海”,更没有自暴自弃、无所作为。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9页。,他是通过学习“六艺”、编书立说、开坛授业和开宗立派,利用当时民间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实现“三不朽”的。
其时难逢、其遇难有,孔子尽管处在民间,却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而径达“三不朽”之圣贤境界,对后代文士来说,这是可望不可即的高峰。与孔子对后代文士造成的“影响的焦虑”相比,屈原则更具亲和力,因为他“发愤抒情”的观点和实践,为寻求“立德、立功”却无果,在心理的焦虑中运用诗文舒缓情绪的文士提供了一种救赎之道。文士们有心追求“立德、立功”却常常无功而返,其发愤所作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文却反倒能在不经意间与“立言”之人生理想搭上边。
屈原是在《九章·惜诵》中提出“发愤以抒情”⑤(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的命题的。对《惜诵》篇作于何时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以屈原遭馋人构陷被楚王放逐为界,一种认为《惜诵》作于屈原被放逐以后,一种认为《惜诵》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前。第一种观点以东汉时期的王逸为代表。他提出:“《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⑥(汉)王逸:《楚辞章句》,载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121页。认为《惜诵》作于屈原遭逐以后;第二种观点以明代的汪瑗为代表,他认为《惜诵》作于屈原遭逐之前:“此篇极陈己事君不贰之忠。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真可对越神明,宜见知于君,见容于众。然反丛罪谤,使侧身无所,欲去而不能,其情亦可悲矣。而犹圣守素志,不肯少变,可谓独立不惧,确乎其不可拔者也。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隐遁远去之志。”⑦(明)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姑且放下《惜诵》作于屈原遭逐前还是遭逐后的争论,实际上两种观点有一个可以沟通的基本认识,即:屈原遭逐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遭逐前后屈原“忧心罔极”、“情亦可悲”,朱熹在评论《惜诵》时就证实:“其言作忠造怨、遭谗畏罪之意,曲尽彼此之情状。”⑧(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由此可知,屈原提出“发愤以抒情”与他遭人构陷,被楚王放逐的个人遭际和由此导致的内心愤懑的心理状态有关。这就呼应了《说文解字》对“愤”字的解释,“愤”意为“懑也”。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512页上。
在研究屈原的思想根柢与儒家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有两种偏差:其一,往往只注意到道家和楚国民间文化对屈原的影响,而忽视了儒家文化对屈原思想的濡染。其实,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学已经入楚。据《史记》记载,楚昭王即准备“兴师迎孔子”,并以“社地七百里封孔子”。①(汉)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评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768页。稍后,孔子的亲传弟子澹台灭明、商瞿等或居楚或将孔子的学问传授给楚人。屈原的发愤说,儒家思想起到的形塑作用不可视而不见。看似屈原这里的“发愤”已经见不到孔子那样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儒家思想对屈原的影响仍在,屈原忠君的观念自不必说,孔子“诗可以怨”与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观点亦有可沟通之处。其二,即使承认儒家思想与屈原之间的联系,人们也往往只注意到孔子“诗可以怨”对屈原的影响,却忽略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和孔子树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他造成的心理焦虑。事实上,屈原早先锐意进取,意欲创造一番现实功业和不朽声名,但迫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他最终遭到贬谪。基于这样的不幸经历,屈原胸有块垒、心有郁结,才转而发愤抒情,将满腹心酸委屈挥洒于辞章。他的这一人生行状即是积极地“立德、立功”不成,退而发愤抒情以“立言”的文士生命轨迹的现实演绎,此后,这一生命轨迹在后代文士中不断得到重现。
综上所述,孔子和屈原在轴心期对“发愤”的使用,奠定了“发愤”在后世使用的两种基本路向。孔子奠定的是“勤奋努力”的路向,屈原奠定的是“勤奋努力”而不得,心有郁积然后“抒发愤懑”的路向。两种路向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与人们对“三不朽”人生理想的追求密切相关。
二、“耻作文人”与文士的救赎
余英时说:“‘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立下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所以‘士'在中国史初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仅限于儒家。司马谈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士对于“治天下”的诉求,本不限于儒家,诸子百家亦概莫能外,而成为他们的集体政治意识。自秦王朝建立,始皇帝打击“游士”的政策施行之后,民间自由的活动空间被大为压缩,“立功”有很高的政治门槛,士人要想实现“立功”之志必须走向仕途。本来实现“道”是士人的目的,入仕为官只是践行“道”的手段,但在政治压力和现实利益③自秦以降,专制王朝建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士面对的“政治压力”包括专制皇权延伸而来的“势尊于道”的压力;而“现实利益”是指自秦王朝建立以来,士从战国无根、浮动的“游士”转变为与宗族、田产紧密结合的“士大夫”,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面前,有些士人由“志于道”向“以利禄为心”急剧蜕变,把仕途经济当成了目的,结果实现“道”这一终极目的反而被遮蔽了。随着儒家思想被西汉统治者所合法化,特别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儒家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以来,儒士入仕为官逐渐有制度化的保障,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更是渗透在其意识深处,要想实现“立德、立功”之志,入仕为官更是成为士人们的不二选择。虽然有许多儒士入仕为官是为了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之公心,但也有很多人汲汲于功名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宋儒郭雍说:“大抵自汉以来,学者以利禄为心,明经抵欲取青紫而已。责以圣人之道,固不可得而闻也。”④(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可见,儒家思想在合法化、官方化之后难逃被政治异化的命运,学术、文化很难脱离政治独立发展,士人所追求的“立功”也被其追求仕进所置换。一边是其他士人争相踏入仕途,以图获取功名利禄或实现“立德、立功”的人生理想,一边是皇权出于实用理性对文士采取的歧视态度⑤汉高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司马迁也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这两则材料说明皇权对文士的轻视。在乱世急于平定天下时,皇帝不太需要在他看来只事空谈的文学;在天下安定时,皇帝也只是把文士当作消遣娱乐、“润色鸿业”的工具。,两者对文士造成的心理焦虑和身份困扰可想而知。依此逻辑演变下去,中国文化逐渐形成“耻作文人”的畸形观念,“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便是这种畸形观念的形象表达。一些真正的文士也以自己的文士身份为耻,离开自己适合、擅长的文化领域,寻求在自己不适合、不擅长的仕宦领域建功立业。①参见钱钟书:《论文人》,载《写在人生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2-55页。然而,仕宦之路并非一马平川,当士人政治理想落空、仕途受挫时,许多人便转向文章诗艺,以文章诗赋来发愤抒情、言志载道。
西汉王朝上升阶段,统治力不断增强,士风奋发向上,士人积极入仕,“立德、立功”的入世之心深深地激荡着人们的心怀,但仕途艰险,贾谊便是在政治失意之后借辞赋来“发愤抒情”的一个例子。满怀希望,始于对“立德、立功”的努力追求,在现实中遭受挫折、理想遇阻、心怀焦虑,终于发愤抒情,在诗文中寻找心理重负的释放和救赎,因发愤所作之文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在不经意间达到“立言”的效果,这往往是屈原、贾谊等文士走过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道路。事实上,贾谊和屈原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们由经历相通带来的心灵相通,刘勰已经认识到:“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1页。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借凭吊屈原的不幸经历,来抒发自己由仕途失意引起的内心忧愤。桓谭认为,贾谊如果“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③(汉)桓谭:《新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页。,也就是说,贾谊是在宦海沉浮、怀才不遇、心怀焦虑之后才转向文章辞赋,是在“立德”、“立功”受挫之后才发愤抒情以求心理焦虑的化解与救赎的。这样的例子当然不胜枚举。在交待撰写《史记》的动因时,司马迁就努力寻找同遭厄运退而发愤作文的隔代知音:“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菱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史记·太史公自序》)④(汉)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评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779页。概括起来,司马迁“发愤”的心理动机由因“李陵之祸”而被除以宫刑的耻辱感,先人所传卑贱职业被主上戏弄、倡优畜之所引起的身份自卑的焦虑感,以及其父司马谈因病错过汉武帝封禅悲愤而死,临死嘱托司马迁修史以承担家族责任的使命感三者叠加而成。庆幸的是,司马迁没有因悲愤而自暴自弃、凝滞于心,而是由“愤”而“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满腔悲愤和未竟的抱负付诸名山事业,通过著书立说,太史公逐渐实现了心理由自卑、悲愤向移情、升华的转移和超越。⑤参见李建中:《自卑意识与悲剧意识——司马迁悲剧心理探幽》,载《唐都学刊》1995年第4期,第26-35页。从中除了可以看出屈原“发愤以抒情”对司马迁的深刻影响,还不应忽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和孔子树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三、“立言”与文士身份认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积离乱,风衰俗怨”的社会政治状况打破了前朝的大一统格局,在思想领域,儒学独尊的局面也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儒学与玄学、佛学、道家思想并立的局面。面对玄学和佛学、道家思想在士人群体的兴盛,虽然有统治者大力维护儒家思想,学者如王弼等人也想通过“以儒释道,以道释儒,会通孔老”的方式达到“调和自然与名教”⑥高文强:《老子“自然”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生成及流变》,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第155页。的目的,但终究没有取得成功,儒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无法挽回其衰颓之势。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与其他时代截然不同的时代,诚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⑦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与思想、审美的高蹈超越相对照,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他们的现实生活却更形沉重。由于身处乱世,这一时代的士人比起两汉士人的忧国忧民又多了一层对个体生命的担忧。他们在关注外在功业之外,更致力于表现自己对生命底蕴的深沉思考和清醒认识——既然生命实体并非梦幻泡影,那么人就要考虑如何赋予这短暂的生命存在以意义,如何突破稍纵即逝、朝不保夕的短暂人生和不如人意的现实,进而寻求永恒和不朽的可能性,这也就成为当时的士人需要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的存在性人生课题。①参见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基于这种情况,发愤说在这一时期就带有浓厚的个人生命体验的特征,文士为文也大胆突破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有感而发、追求自由的艺术本性逐步凸显。宗白华概括道:“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镂金错采'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②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人走向自觉、文也走向独立的时代,文士面对丰富而不如意的社会、政治现实,文士有话要说的心理诉求高涨,他们有感而发、发愤为文,在诗文中更加自觉地表现自己的人格和个性、情感和思想。他们从自身的文士身份出发寻求“立言”不朽,从而使“立言”获得了不逊于“立德”、“立功”的社会价值,曹丕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③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这就是对文士“立言”价值和文士身份的认同。
当然,文士发愤所作之文,往往并非“经国之大业”,而是以个人生命体验为基础、具有较独立审美意识的诗文。《诗品》卷上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④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页。钟嵘将李陵“文多凄怆”的特点与其多舛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作为他分析诗人作诗风格及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根据。刘勰将钟嵘的论述推进一步,在诗文写作的内部,他进一步分析了文士“发愤”而作与不“愤”而作对文章所造成的差异。他通过肯定“情文”而达到肯定文士“志思蓄愤”合法性的目的。他指出,“志思蓄愤”是“为情而造文”,与此相对的“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则是他深恶痛绝的“为文而造情”(《文心雕龙·情采》)⑤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8页。。他将“志思蓄愤”的楷模追溯至儒家经典《风》、《雅》,这也就为人正常抒发情感,尤其是文士抒发愤懑之情时突破“止乎礼”的儒家诗教找到了正当理由。为什么“志思蓄愤”、心有郁积能写出好诗呢?刘勰认为:“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才略》)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9页。“蚌病成珠”之喻是“发愤”说的发展,刘勰认为文士经过身世坎坷、命途多舛的锤炼,可以使文士爆发出旺盛的创造力,从而孕育出“文”的结晶和珠玉。由上可知,刘勰和钟嵘通过对不幸文士出彩文章的肯定,以达到认同文士身份和肯定文士发愤为文合法性的目的。
四、“文穷益工”与士人的进退心态
钟嵘、刘勰的上述理论话语逶迤而下,与韩愈“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理论话语具有家族相似性,共同构成将文士作诗为文与其穷通境遇联系起来的话语谱系。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荆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 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 而穷苦之言易好也”⑧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在文辞形式之“工”、“好”与作者“怨”、“愁思”、“穷苦”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此俨然可见“文如其人”的思路。虽然韩愈力排佛老,其“文以明道”的儒家诗学理念与儒道兼修的钟嵘、儒释道融通的刘勰有所不同,但他提出“文穷益工”的命题,将文士身世经历的坎坷性与其发愤之作的高度艺术性嵌合,又与刘勰、钟嵘的相关话语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这一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话语谱系的延长线上,值得注意的还有白居易和欧阳修等人的理论话语。
先看白居易的话语:“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 次及鲍、谢,迄于李、杜,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①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74页。文章憎命达,痛苦出诗人,文士遭遇人生困境,“立德、立功”受阻,胸中有块垒,发愤为文,往往因符合有感而发的艺术本性而使诗文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能在不经意间达到“立言”的效果。流传久远的发愤之作,既道出了文士求而不得的坎坷经历和痛苦心情,却也是对他坎坷经历和痛苦心情的一种补偿。只是白居易受初唐、盛唐踔厉风发的时代精神的影响,渴望建功立业,内心深处排斥止于文士诗人的身份,如扬雄般认为作诗为文“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②引文出自:(唐)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3-964页。,更何况出奇的诗文还会带来“诗人多蹇”的厄运,有鉴于此,他宁愿采取知足保和、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从中透露出中唐士子经过种种政治风波之后瞻前顾后、进退失据的精神风貌。
再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话语。宋代统治者将儒学奉为官方意识形态,重文轻武,尊重士人,以科举制选官。风气所向,士风昂扬向上,士人渴望“得君行道”的心理诉求十分普遍。当时的士人也的确普遍想跻身有机会“得君行道”的文官之列,而不情愿做那处江湖之远的文士。在身居庙堂的文官与遗落草野的文士之间,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舆论更尊重的也是有可能身居要津、建功立业的文官,而非一般只能在市井或江湖“浅吟低唱”的文士。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士大夫与最高统治者关系较和谐的宋代,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会继承韩愈标举儒学的大旗,志在匡扶社稷、兼济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得君行道”的政治意识和文化精神,已渗透到其内心最深处,使之渴望通过仕宦实现“立德”、“立功”的理想抱负,而对失意文士只能发愤为文深感无奈和焦虑。《薛简肃公文集序》有言,“至于失意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③(宋)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载《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8页。,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在欧阳修看来,人当有所施于世,失意之人无奈之下才苦心积虑为情造文,“穷者之言易工”只是不能通过仕宦“立德”、“立功”的补偿和替代性选择。《梅圣俞诗集序》云:“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④(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载《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 1092页。。由此可见,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话语倒并不一定是在为诗的艺术性正名,反倒体现出文士念兹在兹,深心所向往的仍然是建功立业。
五、小说与“发愤”的批判性
明代士风与宋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或“断裂”,即便是王阳明所代表的心学大儒也已很少谈论“得君行道”,而以“思不出其位”为由转向关注“百姓日用之道”⑤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遑论受心学泰州学派、社会世俗化影响而思想和个性得到很大解放的落魄士人。明清两代很多小说批评家就是这种落魄文士,正统的儒家思想遭到他们的质疑和抵抗,他们已很少以“立德”、“立功”为念,与统治者的关系也已更显紧张。以小说这一古代的边缘性文体⑥小说从边缘走向中心,与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整体语境有关,它在近现代被赋予了“开启民智”的启蒙之责。参见张荣翼:《从边缘到中心——词、曲、小说的文体变迁与知识分子话语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8-11页。为突破口,以《水浒传》等封建统治者所称的“禁书”为爆破点,他们在小说批评中通过挪用儒家忠义等思想,将统治者视为草寇的水浒好汉翻转为忠义之士,并进而批判统治者不忠不义的言行,从而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内部爆破,以此怀疑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同时,他们对“发愤著书”的传统命题进行新的发挥,将内心的焦虑和对统治者的不满外化为言语文章,这既缓解了其心理的焦虑,也释放了其个性和人格,也使“发愤”说化为其反对专制统治规训的有效武器。因而,这一时期小说批评家的发愤“立言”具有强大的批判功能和强烈的审美属性。
明代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竟,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①张建业、张岱:《焚书注》,载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李贽极为认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他也提出“不愤则不作”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观点。首先,他不胶着于个人的穷通出身,反而质疑统治者能否选贤任能,并认为“乱自上作”,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其次,他不止为一般怀才不遇的文士表同情、鸣不平,还对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行颠覆,敢于为啸聚山林、落草为寇的反叛者正名。李贽所“发”之“愤”是郁积的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一旦喷薄而出,就具有锐利的锋芒和明确的政治介入性。
李贽之后,不但谈论小说要发愤而作的批评家时有所见,而且有的作家正是在这一命题的影响下进行小说创作的。明清之交的金圣叹便在李贽“发愤之所作”观点的基础上,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八回回批中更进一步,推演出“怨毒著书”的观点:“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②(明)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82页。从情感的强度、烈度、浓度方面进行考察,金圣叹的批评理论和实践将“愤”与“怨”两种情感混同使用③有论者发现,“愤”、“怨”、“怒”、“恨”等不同情感在具体情境中常出现被古人混同使用的情况。参见袁劲:《“诗可以怨”梳理:根柢、 阐释分歧与方法启思》,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九期,第75-79页。,而“怨毒著书”的情感强度、烈度、浓度更是达到了“怒”、“恨”的程度,可见他是借水浒英雄心中之块垒,浇自己心中之酒杯,间接地表达他对当时政治现状的不满。虽然他也认识到《水浒传》痛骂官吏秀才的部分言语愤激,“殊伤雅道”,不符合儒家要求雅驯的思想观点,但他接着将“怨毒著书”的历史传统追溯至司马迁,并说明历史和小说两种文类的不同,用以论证小说创作“怨毒著书”的合法性,这也就为人们利用小说“发愤”,表达不满、发泄情绪找到了出口。陈忱《水浒后传论略》亦直接点明其创作的《水浒后传》是“愤书”,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腐败奸诈、贪婪堕落的统治者:“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客,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理淫奢诳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④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5页。陈忱用一系列的排比句,气势充沛而充满雄辩地指出他悲愤的缘由,直斥高居庙堂之上的统治者实际上奸诈误国、骄奢淫逸,流为草寇的水浒众人却忠义爱民、倍偿民利,从而揭露了统治者行为与言辞的悖论,高喊忠义其实奸诈,高居庙堂实为民贼,这大大溢出了官方意识形态,从而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
小结
由于在“立言”内部具有审美意义的文章低于安邦济世之言,而“立言”又始终处在“立德、立功”的阴影笼罩下,在后来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皇权出于实用理性对文士所持的轻视态度,以及对民间自由活动空间的挤压使士人寻求“立德、立功”须进入仕途,再加上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的作用,多种因素叠加,这 促使士人发愤建功立业、竞相追求仕进的风气盛行,最终导致中国孕育出“耻作文人”和“官本位”的畸形观念。这种畸形观念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我国政治以外的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有消极作用。王国维纵观历史时发现,中国古代无论哲人还是诗人一般都想做政治家,从而感叹“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①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王国维运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提出我国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不发达,这一论断真确与否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在此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还有:在现代社会,哲学、文学、艺术与政治紧密联系甚至成为政治的仆从,这是否影响了其独立价值和独立发展?“耻作文人”和“官本位”的畸形观念会不会妨碍政治之外的文化、科学、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发展?
第二,对古代文士造成了很大的心理焦虑和身份困扰。通过上文对“发愤”的梳理,可知轴心期树立的“三不朽”的等级式人生理想和积极进取的儒家人生态度,已沉淀至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最深处,对后代文士造成了心理的焦虑,但在不同时代具体表现又有所不同。大体而言,在政治统治较稳固,士人入仕有制度化保障,儒家稳居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时代,文士积极入世,以自己的文士身份为耻,其追求“立德、立功”的心理焦虑会更突出。
而在政治现实不尽如人意,儒家思想遭到人们质疑的时代,文士迫于现实环境的限制,其“立德、立功”的入世之心稍减,常通过肯定“立言”而努力达到自身身份认同,其发愤所立之言也往往不是安邦定国之言,而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审美意识的发育成熟。与此同时,文士发愤所作之文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介入性,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者,其感情之浓烈或表达方式之直接常会溢出儒家“发乎情、止乎礼”思想框架的宰制,从而象征性地实现了其自身人性和情感的释放。或许可以这么说,对古代文士而言,发愤为文既是其人生理想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化解其心理焦虑、反抗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强大能指秩序的一种自我救赎。
责任编辑:胡海琴
The Theory of “Dissatisfaction Relieving”: Ancient Scribes' Anxiety and Salvation Affected by Confucian Life Ideal
Liuchu
The life ideal of “Three Immortalities”and Confucian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have caused ancient scribes'mental anxiety in varying degr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we can explor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behind the scribes' making determined effort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dissatisfaction relieving” in different eras. Overall, when political domination was firm, the intellectuals have institutionalized security in being an official, and Confucian ideology ranked mainstream, ancient scribes' mental anxiety of “virtue setting”and “meritorious service” would be more prominent. When the political reality was not satisfactory, and Confucianism was questioned by people, scribes often strived to achieve their own identity through “creation of words”, the articles writing in the state of anxiety also highlighted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properties. In terms of ancient scribes, when their ideals got frustrated,scribes' s writing under the state of dissatisfaction was a kind of helpless choice , but also a kind of self-salvation to resolve their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revolt powerful signifier order of political and official ideology.
the theory of “dissatisfaction relieving”; scribes; “Three Immortalities”; cultural studies
I209
A
1000-8705(2016)02-80-87
刘楚,生于1988年,男,汉族,江西吉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