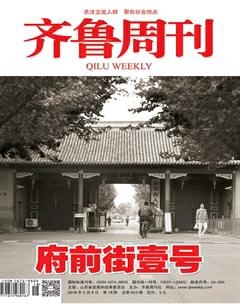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切尔诺贝利。这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民,有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召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他们的故事透露出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本书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人们坦白地述说着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历其境却又难以承受。
这是当代罕见的纪实文学经典,人类恐怖的科技悲剧,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经历过这种事,我们如何相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一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一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