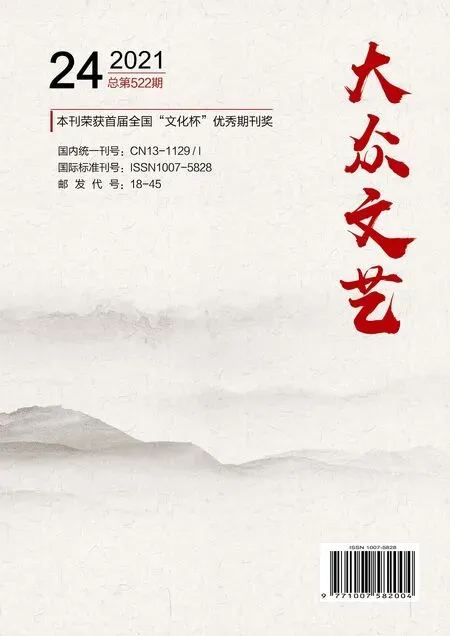中晚明小品文中戏曲创作过程所反映的戏曲观
朱俊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01331)
中晚明小品文中戏曲创作过程所反映的戏曲观
朱俊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01331)
明代中后期小品文作家们日常接触的戏曲表演成为他们关注、评论的对象之一。这些小品文中所涉及的戏曲创作过程,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戏曲创作观念。
小品文;创作过程;创作观念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理学规范的松动,适情尽性的小品文应运而生。小品文突破正统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修短适宜,形式灵活,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表达真情实感。由于晚明时期观剧之风盛行,因此作家们日常接触的戏曲表演自然就成为他们关注、评论的对象之一。这些小品文中所涉及的戏曲创作过程,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戏曲观念。
首先,艺术创作应能“练熟还生”。
张岱《张子文秕》卷八《与何紫翔》一文中,专门论述艺术创作中生与熟的问题。他批评何明台弹琴,认为他的根本缺点是“不能化板为活”,即未能克服生硬、板实,结实有余而萧散不足;但过犹不及,王本吾无生硬之病,纯熟是长,但匠气太大,不能练熟为生,“其弊也油”,“油”到缺乏生鲜之气。二者皆是大病,后者更重于前者。前者是只知一板一眼,按谱而弹;后者则是熟到不能自制,以至油滑。练熟还生就是在技法熟练之后仍能在艺术活动中以新的生命活力来表现崭新的艺术境界。毋庸置疑,艺术家在技法上自是纯熟的,而在十分纯熟之后,却能自熟中走出,将个人主体精神贯注其间,从而是他的艺术创作过程始终具有一种生鲜之气,实属难能可贵。禅者论禅,有一段著名公案,参禅者观山观水,初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再则见山非山,见水非水;最终则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张岱的入熟还能生出,与此禅道异曲同工。
具体到戏曲表演中,练熟还生就是一种常演常新的高层次的艺术境界。许多优秀演员为演好一场戏,倾尽心力投入剧情,甚至不分究竟是戏中我在还是我在戏中。在戏曲表演中,演员融入个人的强烈情感和生命体验,使剧中角色日日富有生机和活力,给人新鲜动人的美感,这种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张岱《张子诗秕》卷三《祁奕远鲜云小伶歌》中称赞祁家家班伶人“鲜云小傒真奇异,日日不同是其戏。揣摩已到骨灵节,场中解得主人意。”“老腔既改白字换,谁能练熟更还生?出口字字能丢下,不配笙箫配弦索。曲子穿度甚轻微,细心静气方领略。”这个家班伶人鲜云歌喉美妙,能唱多种戏曲,所以“日日不同”。可见在戏曲表演中,乃至所有的艺术活动中,由“熟”而走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艺术虚构不能超出“情理所有”。
传奇,非奇不传。传奇创作追求奇异,正是传奇这种文体的特点所规定的,但是,过犹不及,一味追求奇异,不顾人情人理,就不能表现生活真实,反惹人生厌。张岱就发现了这种弊端。他在《琅嬛文集·答袁萚庵》一文中这样写道:
“传奇至今日怪幼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妆,兼以非想无因,无头无绪,只求闹热,不问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跄。热闹之极,反见凄凉。”
张岱反对“狠求奇怪”而提倡“情理所有”,也就是传奇创作的虚构和真实关系的问题。虚构只要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符合人物情感发展的逻辑与生活发展的逻辑,就是成功的艺术真实。正因如此,张岱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袁于令的《西楼记》,却大加赞扬:“兄作《西楼》,只一情字。讲技,错梦,抢姬,泣试,皆是情理所有,何尝不闹热?何尝不出奇?何取于节外生枝,屋上起屋耶?总之,兄作《西楼》,正是文章入妙处,过此便思游戏三昧,信守拈来,自亦不觉其滑熟耳。”《西楼记》的情节都是由“情”生发开来,符合人物情感的正常发展逻辑,没有为求奇幻、求热闹而故意地“节外生枝,屋上起屋”,它的“热闹”“出奇”,“皆是情理所有”,没有超出故事情节本身允许的“情理”界限,故仍不失为“文章入妙处”;而《合浦珠》的不足,就在于它一味狠求“出奇”,超过了“情理”所能容许的度,故而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
最后,戏曲语言应能“极情尽态”。
戏曲语言是剧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语言运用得体,才能创造栩栩如生的戏剧人物。对戏剧语言是应当骈俪化的雅致华美,还是家常化的本色通俗,明代戏理论家何良俊、沈璟等各执己见,未能统一。对此,晚明徐渭和孟称舜在他们的小品文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总结。
徐渭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一文中,批评梅鼎祚杂剧《昆仑奴剑侠成仙》,开篇即道:“此本于词家可站立一脚矣,殊为难得。但散白太整,未免秀才家文字语,及引传中语,都觉未入家常自然。”徐渭认为此剧虽好,但念白不够“家常自然”,是“秀才家文字语”。那么何谓徐渭所说的家常自然?文中一段文字即体现了他重要的戏曲观点:
“语入要紧处,不可着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小碓,不杂一毫糖衣,真本色。若于此一恧缩打扮,便涉分该婆婆,犹作少年哄趋,所在正不入老眼也。至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着一文字,与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补少,促作整句。锦糊灯笼,玉镶刀口,非不好看,讨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处矣!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以媚人,而不知误入夜狐,作娇冶也。”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徐渭的“家常”就是“本色”语言,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本色就是宜俗宜真,这是他对本色的理解。“宜俗宜真”具有丰富的内涵,俗即是通俗易懂。戏曲是舞台表演艺术,与诗词不同,他要演给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看,所以登场搬演要使观众能够理解接受,语言贵浅不贵深。但徐渭所言的“俗”又不是“俚俗’而是“家常”。“俚俗”语是一种原生状态下的语言,不加选择,显得粗鄙。“家常”语是对生活用语的选择、提炼、加工,即脱去“俚俗”语的粗鄙,又呈现出自然质朴的色彩,易为观众欣赏接受。戏曲本色语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个性。
极为推崇徐渭的孟称舜继承了他的本色理论,并把本色当行联系在一起。他在《古今词统序》中明显表达了者一观点“: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动心声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孟称舜以为作词者各有不同风格,有张三影、柳三变之属的柔音曼声,有苏子瞻、辛稼轩的清俊雄放。但二者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只要能“极情尽态”,表达出真情实感,都是本色当行之佳作。这一点与徐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怎样才能创造出当行之作呢?他在《古今名剧合选序》给出了具体而经典的答案:“曲之为妙,极古今之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型,随物而赋象。”“非作者身处于百物云为之际,而心通乎七情生动之窍,曲则恶能工哉!”他认为,写作诗词只需尽言一己之意,而创作戏曲则不然,忽为百姓人家,忽为帝王将相,忽为仆妾青楼,忽为文人端士。以一己之身而写百人之心,是以“不化身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更准确地说,是不能创作出当行之曲。戏曲艺术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戏曲作家必须“化其身为曲中人”,设身处地,充分体验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个性等,寻求符合人物身份个性的语言风格,才能创作出令“听者动心声”的优秀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