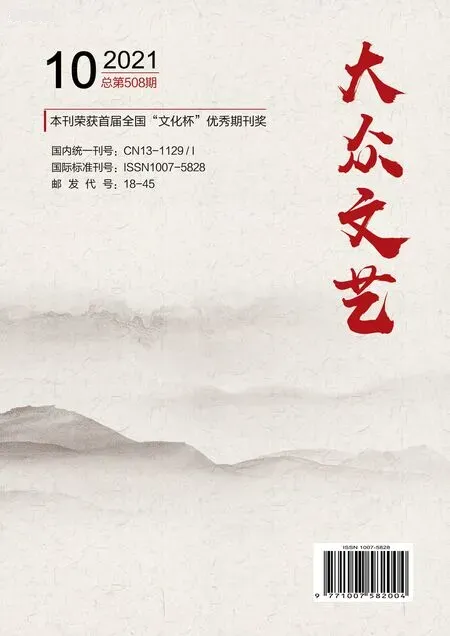黑暗社会下人性的扭曲与灵魂的挣扎
——浅析曹禺经典戏剧《原野》
赵晓坤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黑暗社会下人性的扭曲与灵魂的挣扎
——浅析曹禺经典戏剧《原野》
赵晓坤(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摘要:曹禺的《原野》表现出在强权当道的时代,一个受着道德与封建伦理纲常压抑下的悲剧人物在背负“父仇子报”的观念后,一步步走向复仇“胜利”,却也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生动写照。复仇的悖论彰显人性善与恶,罪与罚。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原野》;复仇;原罪;人性;社会
发表于1937年的三幕剧《原野》,是曹禺早期话剧创作中最受冷落的一部。多年来这部作品一直饱受争议,学界褒贬不一。关于《原野》的主题,过去的文学史较多指责作者对原始荒野“神秘气氛”的渲染,并把仇、焦两家的斗争简单理解为农民与恶霸地主之间的冲突,讴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在此,笔者认为,从原罪意识以及社会伦理纲常之下人性本能来解读《原野》更为合适。
一、人类的“原罪”导致现实罪恶
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教义。它被认为是人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人在原罪的驱使下走向罪恶的深渊,却又难以自拔。《原野》中,“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皓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作者借自然物象营造原始的,野蛮的,令人感到压迫,窒息的气息。“在天上,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像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伴随着狂喊一声,血性汉子仇虎身上带有的野蛮气息展露无遗。主人公在这样的场景中,向读者展现出人性最原始,最具有蛮性的一面,但同时似乎暗示了他们在张着血盆大口一般的社会中的艰难生存,在时代环境中地小心挣扎,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噬,重新失去自由。
原罪与人今生所犯的具体罪过并不等同。但是,现实的罪恶却是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原罪。《原野》中,故事的整个发展,无不渗透着人类的“原罪”。恶霸地主焦阎王为满足自己的贪欲,“仗势欺人,压迫好老百姓。”他把仇虎父亲架走,活埋,强占了田地。最终导致仇虎家破人亡。仇虎为了自由而穿破牢狱,粉碎桎梏,又为报一己之仇而杀掉了焦大星,间接害死了小黑子。金子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爱情,不会在那个年代做出反传统的背离纲常道德之事。所有人凭自己私欲做事,却因被时代,社会,传统,道德这一系列套在人类外的枷锁束缚着,而走向悲剧的深渊。
从戏剧中塑造的角色,设置的情节,人物的对白中,不难读出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原野》中,我们能看到作家曹禺对于人类本能欲望,原罪,渴望自由却又害怕自由等等的一系列哲学宗教意义层面的思考。
二、“罪与罚”中的灵魂挣扎
话剧《原野》中有两条主线,一条写焦阎王的“罪与罚”;一条写仇虎的“罪与罚”。从话剧的第一幕、第二幕看,表面是写焦阎王,但当我们看到话剧的第三幕,仇虎一步步走向自我挣扎的边缘,恐惧,害怕,愧疚,最后走向死亡之时,一切都已了然。一个复仇的血性青年自我审判后吞下自己种的“恶果”。
这不得不说是从罪恶走向另一种罪恶。用罪恶的方式去惩罚罪恶的仇人。从罪恶开始,却也以罪恶作为终结。仇虎一出场即给人一种凶蛮的,充满暴戾气息的汉子形象。当他听到焦阎王已经去世的消息时,错愕,继而愤恨。又知道自己喜欢的金子嫁给仇人焦大星的儿子之后,他现出狰狞的笑容。仇虎的复仇计划彻底打乱。做了八年牢狱只为报两代之仇的仇虎却意外碰上了仇人的去世。从此刻起,看似正义的复仇带着仇虎对于爱人被抢夺的个人私情而变质,一个受害者在准备,谋划,杀害,复仇成功这一系列的悲剧中变成一个罪恶之人。他噬血,杀戮,却都朝向了不该为仇虎一家的死付出代价的无辜人。
仇虎个人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次“复仇”的催化剂。他爱金子,但金子已经嫁给了焦大星。一个妇人出轨是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在仇恨的控制之下,他还是向老实没有坏心眼的焦大星下了手。至此,他的心里陷入深深的愧疚,良心开始不安。小黑子的死亡是仇虎造下的又一慎重的罪孽。作者在戏剧的安排上做了充足的铺垫。第二幕的开始,小黑子在摇篮里不住的啼哭,仿佛有感于即将到来的灾祸,悲泣着自身的命运。仇虎让金子把小黑子报到自己房间的床上。焦母用自己的铁拐杖亲手毁了自己的孙子。这之后,仇虎的恐惧之心延展了。想到自己屈死的父亲与妹妹,想到自己在牢狱中遭受的种种,他又为近乎残忍的复仇做着辩护。试图减轻内心的不安。但越是重复这样的辩解,越能体现仇虎内心的挣扎,内心的彷徨。他在逐步看清无辜人已逝去,自己无法洗刷种种罪孽的事实。
对于焦阎王一家的报复心理使仇虎用罪恶地伤害无辜人的方式去惩罚罪恶。这无疑导致了仇虎走向人生最后的悲剧。焦阎王自己没有承担自己的罪恶,本不该承担的焦阎王的家人承担了。这样巧妙的情节设置值得我们深思。
三、社会伦理重压下的人性觉醒
整部话剧就像是一个灵魂的自我审判的过程。有气力,一身是胆的仇虎本应该走正常的青年该走的道路,但家庭突如起来的灾难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灾祸发生之时,他就开始着自己的复仇计划。这种“父仇子报”的旧社会农民的传统心理使仇虎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他身上戴着镣铐,心里同时也有着精神的镣铐。这样压抑地活使仇虎早已忘记欲望满足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当他逃出牢狱,看到金子之后的情欲难收,杀害焦家的嗜血成性,某种程度上让他收获了一种欲望满足的快感。这种快感的满足之后是极大的空虚,是欲壑难填的巨大恐惧。从本质上来说,仇虎仍是一个心存善良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有良知,有悲悯的情怀,他不会在杀人之后,陷入愧疚。这正体现出社会道德良知对于人性的约束。
社会伦理重压下,人性开始变得扭曲,而后又在道德的感召下觉醒。个体命运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在曹禺的话剧《原野》中得以显现。
话剧《原野》某种程度上是在演绎“恶有恶报”的故事,但这种“恶”和“善”的概念在这部话剧里却带给人无尽的深思。仇虎从善变恶,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完成了内心灵魂的审判,完成了对于心灵的救赎,摆脱了加之于人性之外的一切束缚,换取最终的宁静。读者仿佛是站在上帝的角度俯视着人类,看人性在种种压抑与束缚之下走向偏执,最终走向死亡,继而生出无限的悲悯与同情。作者则希望借此唤起理性良知的觉醒,由此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安宁。
参考文献:
[1]曹禺.经典作品选[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2]梁淑安.话剧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黄会林.中国百年话剧史稿[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邹红.作家导演评论:多维视野中的北京人艺研究[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5]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三联书店,2006.
[6]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张露晨.曹禺《原野》:现代复仇者的“罪与罚”[D].北京,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