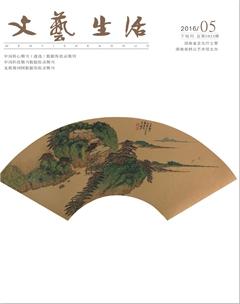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体认
陈美佳
摘 要: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无论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识地叙述,其作品中的人物总会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苏东坡说“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是在强调作品与创作者之间的联系。有人说,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这是真情之笔,也是经验之谈。这里说小说与作者生有联系,并非以“自传”论,有些时候小说情节甚至与作者没有任何联系,但它也无疑会受到作者无意识的影响。本文仅就萧红《小城三月》、张爱玲《金锁记》和《半生缘》为例展开。
关键词:张爱玲;自我体认;小城三月;金锁记;半生缘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5-0009-02
一、《小城三月》:人鸟低飞
萧红的一生充满苦难,《小城三月》更是她的绝笔,整篇小说读下来,有许许多多可以显现翠姨心事的细节都让人为之动容。脑海中那样一幅画面久久挥之不去:翠姨和“我”坐着马车赶往集市,只为一双绒绳鞋,而场景却是白茫茫一片,洁净无尘。这是脱离了小说笔墨之外的想象,不一定紧扣内容,但这些是紧扣作者情感的。小说以“我”的视角写出一个个片段,而一个个细微无比的细节甚至可以让读者错以为就是自己在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这视角是平静的,但也是含泪的;情绪是柔和的,但最后却当得起一个“柔肠寸断”。
小说开始于一片春天的原野,由一个孩子的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在揣度着、想象着,翠姨是她目光的焦点,其余的背景全都被虚化掉了,只有翠姨的形象才是有色彩的、饱满的。整个文本甚至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没有人关注也没有人来体会的落寞与伤感,一种满是期待与渴求却只能却步的情绪。
翠姨深爱着堂哥,而没人能够像“我”一样关注到她的心事,她的爱是强烈的也是隐秘的,作者这样写道:“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这又仿佛是作者的独白,萧军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了她最强大的安全感,却又在之后的生活中给了她几乎同等的伤害;端木蕻良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最后,可是懦弱的端木真的是她想要的那个守护者吗?
小说不是在写萧红的经历,但谁又能说在这短暂而美丽的春天中发生的不是萧红的故事呢?王小妮给萧红写传,正题就写作“人鸟低飞”,萧红热爱着这个世界,她渴望着能有一双坚强有力的翅膀带她高飞,把她以前种种的不幸全部消解,而每一次急切的尝试无疑都又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萧军的强势如此,端木蕻良的懦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的爱与热情也只能随她一同埋葬到坟墓里去,眼前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她(或是映射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值得她去倾诉衷肠。于是她在《小城三月》里写了一个“我”,她是在寻找,或是怀念那一双强壮的翅膀吗?
小说的前四章不紧不慢地铺叙着,而从第五章开始,节奏却陡然加快,翠姨一病不起,很快便永远地走了。这是作者在狠心为自己宣判吗?——这是认命,也是血的控诉。而堂哥虽然提起翠姨常常落泪,却并不知道她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这才是真正的寂寞身后事,也恰恰是作者的自我嘲笑。这无疑是作者的死亡、毁灭倾向,翠姨的命运出自她的设计,如此悲惨的命运恰恰是她要实现给翠姨的,这是故意的,是精心设计的,是通过毁灭自己达到一种超脱。为了拒绝苦难,她也不得不向她热爱着的世界说再见了。
二、《金锁记》:自虐与自省
张爱玲是喜欢看旧小说的,《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都是她爱不释手的作品。在她自己的创作中,旧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也很明显地保留了下来。很多的描写都有着中国旧文人的传统,又加上她受过的西式教育,如下面这段描写:
她(七巧)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色窗帘,季泽正从穿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裤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这一段这是张爱玲写景的代表,她的笔触是游动的,但最终却停在一处流连,有电影镜头的特点,又好像水墨画的场面。这是传统与西方很好地结合的例子。
《金锁记》女主人公曹七巧的命运,很像是由作者为自己假设的一种可能人生推衍来的,就像小说结尾曹七巧想象着另一番可能的人生。而张爱玲在《怨女》中对它做改编,这一切的苦难反而又好似一个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一个梦,这或许也是作者心态的变化。
读完整篇小说,读者并不会去讨厌、怨恨曹七巧的丑与恶,反而会陪她一起辛酸、无奈。这不像鲁迅那种真实的刻画与反映,而是通过假设的情境,写出真实的人性。龙应台在台大演讲时说:“作家也分成三种,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金锁记》当得起第三种评价。
余斌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张在父亲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的话,那么她在母亲家里尝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见得比那一枚更易于吞咽。”在这样的生活中,张爱玲是孤寂,是落寞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是进行着各种幻想的,有着许许多多现实中不能做的事情,都在思绪里尽情驰骋着。笔者认为张与萧红一样,也是有着自虐倾向的,曹七巧的变态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这是张爱玲对外界生活的回复,也是一种自省。她在慢慢试探着这个令她伤心透顶的世界,也在慢慢试探着自己,她是在叩问自己的人生,是在向自己的内心深处走,走进那个可能一步之异就是另一个曹七巧的自己,同时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苦难。
三、《半生缘》:人情甚不美
张爱玲一向以一双冷眼审视人生,她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都以悲剧收场,而且是由性格造成的必然的悲剧,而《半生缘》中顾曼祯与沈世钧的爱情悲剧却完全是一连串巧合与作祟的恶人导致的。这是张在写作《十八春》时为迎合读者和时代而做的改变,最后也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二人来到东北支援建设,顾曼祯与沈世钧妻子相处融洽,但《半生缘》对它的改写却删去了这个尾巴,打破了大团圆,归结到悲剧上来。
《半生缘》的悲剧意味是命运层次上的,而这种貌似大而无当的悲剧命题在她的笔下却也那么悲凉感人,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她对人生的理解,深入到了人性层面,每个人都有着大大小小一连串的由往事构成的悲剧,当看到这样的悲剧故事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深挖出自己的那一份悲剧认知来添上几句唏嘘,留下几行泪水,为主人公也为自己。所以当顾曼祯对沈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读者此时是否也化身成了自己故事里的沈世钧?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不幸中不同的是事件,相同的是缺憾。人都有缺憾,一个个回不去的缺憾都可以成为悲剧感的来源。人生就是这样,一件爬满了悲剧虱子的华袍,外表华美,绒毛底下却是不堪的。
对于荀子性本恶的观点或许存在争议,但“人情甚不美”的观点是没有质疑的,《半生缘》里在人物性格上处处抓要害,蔓璐的嫉妒,沈世钧的懦弱、沈母的偏见都在改变主人公命运上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都体现着人性的轻薄与无常的源头。在张的小说里,巧合来的不再是突然的,而是基于人物性格必然会发生的,这也是一种死亡与自虐的倾向,是撕破假象通过对美的破坏来实现真正的美。
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张爱玲呢?一切的假设都是真实的,是她的尝试,她尝试着一个个的新生命,来缓解她生命深处令人窒息的孤寂与落寞。这是了解的同情,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的悲悯。
一个作家自身的经历往往决定了他所有作品的重大主题,萧红急切地渴求一份安全感,张爱玲却用自身的悲苦去体认众生的苦难,从而超越这种苦难去逼视人性。但不管怎样,作家都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体验着自己,实现着自己所经受的、所渴求的和所厌恶的,这也是与作家经历互为见证的另一个生命存在,他们之间是知己,也只有他们才懂得、才能看穿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