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在国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秘鲁人权监察机构为例
范继增
拉美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在国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秘鲁人权监察机构为例
范继增*
自古以来监察专员制度就存在于每一个文明政体之中。无论在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古代中国时期,执政者普遍地在政治制度中设置监察机构用于监督地方或者中央官员腐败或者滥用公权力的行为。*Enika Hajdari,Ombudsman - Historical Review,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2014),Vol.1,p.516.现代监察专员起源于瑞典。1719年瑞典最高监察专员获得了大法官头衔(Justitiekanslern)。1776年授予此头衔大法官成为议会监察专员,具有监督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运行的权力。1809年的瑞典宪法确认了该制度的宪法性地位并且赋予了监察专员代表皇帝的权力。瑞典模式的监察专员制度在此后被其他的北欧国家、西欧国家、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所借鉴,*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New York:Springer,2004,pp.2-4.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监察专员模式或者传统型监察专员模式。议会选出的监察专员可以独立地行使权力,通过公民个人申诉或者依自身的职权的方式不偏不倚地调查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并且提出建议、矫正其发现的违法或者不公平的行为以及发布年度报告或者特殊性调查报告。传统型监察专员经常通过较为柔性的劝说或者同其它国家机构沟通的方式促使国家或者公共权力机构改进不良行政,但是无法采用强制性或者裁判性的途径纠正相应机构的不良行为。*Marc Hertogh,The Policy Impact of Ombudsman and Administrative Court:A Heuristic Model,in Linda C.Reif(ed),International Ombudsman Yearbook,1998,p.64.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世界各地发酵,设立监察机构成为新兴的民主政权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保障基本权利和抵制不良行政的普遍选择。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的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简单移植北欧模式的监察专员机制,而是赋予其更为积极的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职权,并且通过立宪方式对监察机构给予宪法层面的保障。*Margarita R.Buades,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Constitution and Ombudsman in Spain,in National Ombudsman of Netherland(ed),Ombudsman and Human Rights: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1995,p.42.例如,1975年的葡萄牙新政府成立了“公正维护者”(Provedordejustica),该机构于1976年成为宪法性机构;西班牙1978年宪法将“护民官”(DefensordePueblo)纳入到宪法体系之中,并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其职权的方位和运行方式。与传统的北欧模式的监察专员制度相比,西班牙的人民卫士不仅可以通过调查、建议和报告的方式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同时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人权监察专员可以通过接受个人或者团体申诉的方式调查对国家机构侵犯人权的指控,并且具有协助宪法法院审理案件的权力。*Gabriele Kucsko-Stadlmayer,European Ombudsman-Institution:A 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Regarding the Multifacet Realization of an Idea,New York:Springer,2008,pp.147-149.
除巴西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拉美诸国文化与历史与其前宗主国西班牙有着相似的特点。个人独裁、军事独裁或者内战普遍成为拉美国家生态的主旋律。伴随着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国内各政治势力的妥协,拉美各国逐渐从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型。但是,各国在长期的威权统治下缺乏人权意识和承担保障人权和维护民主制度的国家机构。因此,政治与司法腐败、政治暗杀、党派斗争以及政府缺乏公信力成为拉美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建立人权保障机构成为各派势力或者军事(个人)独裁政府可接受的民主化起点。*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23.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纷纷效仿西班牙模式,在国家以及地方层级上建立人权监察专员机构 ,*根据Reif博士的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监察专员主要分为两类:人权委员会模式和人权监察专员模式。前者一般是在议会的框架下参与研究、人权教育、法律改革提议以及鼓励政府签订更多的国际人权公约。例如,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墨西哥以及巴拉圭等 国家就是设立了人权委员会的制度。除了乌拉圭外,其它的拉美国家普遍设立了人权监察专员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巴西只设置了地方性的人权监察专员制度。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p.188-191.保障公民的权利、维护法治和纠正公权力机关不良行政。*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24.尽管新设立的人权保障机构在各国政治体制内职权有限,*普遍依照各国的宪法与法律,人权监察专员没有作出强制性决定的权利或者司法性决定的权利。受到了统治者或者议会反对党的制约,甚至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危地马拉和秘鲁人权监察机构在任期内就通过对抗当时的执政者积累了不少的政治资本和名望。但是在该制度有力运行的条件下,相比较于其它的国家机构,民众对人权监察机构保障人权的作用更有信心。
尽管拉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独特性,但是各国都经历着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因此各国的人权监察机构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也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将从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职权、与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监察专员个人能力等角度分析其在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比较全面呈现人权监察专员在拉美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情况,笔者选取了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秘鲁这三个国家作比较性的分析。在拉美国家中,除了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等国是在民主社会成功转型后建立国家人权机构以外,上述三国建立人权监察机构的背景几乎包括所有其它拉美国家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危地马拉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建立仿照西班牙模式人权监察专员的国家。萨尔瓦多的人权监察机构是内战双方和谈的产物,用于保障人权和监督政府合理行政。秘鲁的人权监察专员成立于后威权主义时代,具有军方背景的前总统藤森希望通过建立人权机构的方式有限地保障人权,提升政府的国际形象。对上述拉美三国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学术界对拉美国家人权机构研究的空白,同时也对其他正处于民主转型或者和平建设的国家保障人权具有启发性的作用。诚然,拉美国家与中国的政治环境有着根本地不同,但是两者都面对着改革、完善法治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转型等共同的任务。因此,从职权、运行模式以及人权检察官(护民官)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详细研究对我国学者在思考信访制度改革和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等议题上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一、危地马拉人权监察专员机制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
1985年危地马拉宪法仿照西班牙模式设置了国家人权检察官机构(ProcuradordeLosDerechosHumanos),该机构于1987年正式成立。从1960年开始,危地马拉就陷入到了持续的内战状态。即使1985年宪法颁布后,危地马拉军方仍然是真正的幕后掌权人。*Susanne Jonas,The Battle for Guatemala:Rebels,Death Squad,and U.S Power,Westview Press,1991,pp.154-159.但是掌权者清楚地知道由于危地马拉的内战造成了45,000人失踪以及150,000人失去性命,因此必须通过建立人权机构的方式重建国内和平秩序。*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14.
危地马拉人权检察官是由议会选举产生,对议会负责的,可以独立行使职权的国家人权机构。初期的立法对人权监察官的就任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规定由总统提名的人权检察官候选人必须要获得议会全体议员的2/3的支持方能就任。危地马拉宪法为人权检察官制度提供了宪法保障,防止了立法或者行政机构通过修宪以外的方式改变人权监察机构的职权或者地位。拉美国家人权监察机构普遍具有功能性和宣传性职能。从功能性的角度分析,危地马拉宪法第274条规定了人权检察官具有监督行政和维护本国公民在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依据宪法第275条,人权检察官被赋予了广泛的职权:促进政府在涉及人权领域的良好行政、调查和批评侵犯个人利益的行政行为以及依照公民个人申述对涉及人权的问题进行调查。人权检察官有权管辖公共和私人机构中一切人权侵犯的事件。*Ramiro de Leon Carpio,The Ombudsman in Guatemala,in Symposium:The Experience of Ombudman Today - Proceedings,1992,Mexico city: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pp.116-117.除广泛的调查权之外,人权检察官可以向相应的机构提出解决意见,对国家机构违反人权行为作公开的谴责,将违反人权的政府行为直接提交行政或者司法机构以及向民选议会作年度报告。人权监察机构依据宪法和法律还负责向警察机构、行政单位和学校的普及宪法权利和国际人权法知识以及游说议会批准或加入某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职责。因此,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在履行监察职权之外,承担着人权教育与公职人员人权培训的职责。
危地马拉国家人权监察机构不仅对所有的中央22个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和人权侵犯进行监督,同时内战结束后在地方设置了26个专职办公室监督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协助首都地区以外的民众提供保障服务。*Lena Bloomquist,Maria Luisa Bartolomei & Fredrick Uggla,Evaluation of Swedish Support to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 in Latin American:November 2001-June 2002,Swedish Institut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2,p.10.在内战期间,为了最大程度上保障交战地区居民的基本权利,人权监察机构在交战地区设立了五个“移动型监察专员办公室”主要关注妇女、战俘以及残疾人的权利。*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14.在和平建设时期地方性人权监察专员承担了很多法定职责以外的工作。在缺少或者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由于民众通常是求助无门,地方性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变成了不计报酬的义工。*Lena Bloomquist,Maria Luisa Bartolomei & Fredrick Uggla,Evaluation of Swedish Support to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 in Latin American:November 2001-June 2002,Swedish Institut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2,p.12.
除了宪法职权和机构的设置之外,人权监察机构对危地马拉政治转型的作用与国内的政治环境、检察官个人的性格以及获得国际援助都密切相关。第一任人权检察官de la Riva 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但是在军队对政府机构的压制下,国家人权机构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de la Riva 在1989年病逝,de Leon Carpio 成为了新的继任者,个人性格和与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帮助其开创了危地马拉人权监察专员黄金年代。*Stephen C.Ropp &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Chile and Guatemala,in Thomas Risse,Stephen C.Ropp & Kathryn Sikkink(eds),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91.在军队势力依旧强大的年代,de Leon Carpio依靠民众和国内外人权组织力量在保障生命权、消除酷刑以及个人安全的事项上利用宪法职权和社会媒体的力量与军队势力相对抗。不妥协的精神赢得了社会民众和国内外人权机构的尊重和支持,也为de Leon Carpio 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人权监察专员危地马拉民主转型发挥更大的政治与法律作用提供了社会空间。
1993年危地马拉民主转型危机的和平解决和1996年国内和平协议的签署都有着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作用和de Leon Carpio个人努力的成果。1993年5月时任危地马拉总统Jorge Serrano决定发动政变,解散国会和最高法院,终止民权保障程序,希望恢复依靠行政机构为主体的独裁统治。尽管军方支持总统的决定,但是迫于民间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政变只维持10天就宣告失败。在政变期间,de Leon Carpio及其领导的人权监察机构公开批评总统的勇气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国会随即决定由de Leon Carpio 担任总统,完成流亡总统Serrano余下的任期。此后,由于de Leon Carpio 的人权检察官的经历为期积累了充足的政治信誉与资本,反政府军事力量危地马拉全国革命阵线也对其保障民主与人权的作用赞赏有加。这使得de Leon Carpio 成为军方与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的调停人,为1996年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创造了条件。*Rachel Siede,Guatemala After Peace Accord,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998,p.76.冲突双方在停火协议中共同承诺在和平时期将通过强化已有的人权机构的方式恢复国内和平建设和人权保障。
尽管被强迫失踪和遭受酷刑的人数在和平协议签署后有所减少,但是法外处决、滥用警察权力、糟糕的监狱环境以及针对妇女、原住民以及残疾人歧视政策依然严重。*20世纪90年代,危地马拉人权检察官主要致力于保障个人的核心权利。2000年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收到有关人权的投诉中,一半以上都是涉及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社会清洗和滥用私刑的案件逐步上升。*依据一份调查报告仅在2001年上半年,就查出了14例法外处决,330例雇凶杀人,132例谋杀,8例私刑以及49例企图适用私刑。这些案件多数都发生在偏远地区。同时,处理涉及教育、卫生和工作领域的投诉以及监督中央和地方选举和开票的过程也成为人权监察机构在后和平协议时期新的工作重点。*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195.虽然人权监察机构管辖权和作用不断地扩大,但是其本质只是辅助性的人权保障机构,不具有国家司法和行政机关的权威。因此,危地马拉在民主转型时期人权保障更多的是取决于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自身惰性与腐败,并且消除与武装势力的冲突。
在转型过程中,危地马拉监察机构自身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除了各派政治势力暗中通过暴力或者其它的政治方式威胁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工作人员*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37.时任人权监察官Arango指出危地马拉监察机构的工作人员警察受到当地警察的威胁和殴打,甚至被警察成为“我们主要的敌人”。地方的行政首脑也承认警察威胁人权监察人员的现象频繁发生。和其它的社会人权活动人士之外,资源匮乏、受国家机构权力制约以及人权检察官本人作风独断专行都对人权监察机构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自1987年人权监察机构成立以来,财政问题就成为困扰监察机构履行职权主要问题。*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196.在一次采访中,危地马拉人权检察官Julio Arango 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国会)想用财政手段卡住我们的脖子”。2001年,危地马拉的人权监察机构一共雇用了350名人员,并在全国26个地方设置了人权监察专员办公室。但是国会对监察专员只为人权监察机构提供了4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只能维持基本的办公开销。*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13.此后,预算总额未能随着监察机构职权和组织的扩大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援助成为人权监察机构维持运转的关键。依据2002年一份数据统计,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在2001年获得的外援占全部预算的15%。*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36.
作为全国人权监察机构首要领导,人权检察官的态度以及与国内外人权组织联系以及政府机构合作的程度直接影响国家人权机构在转型国家中起到的作用。de Leon Carpio 不屈服军队和总统的作风不仅为其广泛赢得了政治信誉,同时也促成了和平协议的签署。相反,Arango就任人权监察官后的表现则令人失望,无法与前任相提并论。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普遍认为Arango专横的态度和不善待人权监察机构雇员的作风令国内的人权活动者普遍感到失望。Arango在上任不久以后就将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员通通换掉,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工程师、社会学家以及教师等社会身份的个人。尽管Arango一再为自己的辩解,声称律师已将人权监察机构变成了法庭,与国家人权监察机构的宪法任务相冲突。批评人士则指责Arango的行为显然是任人唯亲,将自己的亲属、朋友或者同党同志安插到重要的职位中。针对Arango 另一个批评是不积极与国内外的人权机构建立友好的关系,总有夜郎自大的心态。早在Arango的前任la Guardia 担任人权监察官时期,人权监察机构将联合国核查小组(UnitedNationsVerificationMission)和de Leon Carpio 担任总统期间建立的总统人权委员会(PresidentialCommissionforHumanRights)视为与自身权威的竞争者。尽管联合国核查小组与人权监察机构建立了合作委员会,帮助其进行人权教育与培训,但是la Guardia本人一直与联合国机构保持距离,拒绝参加任何由合作委员会举办的会议甚至谢绝一切与联合国人员的会谈。*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15.Arango 上任后与联合国核查小组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将受到联合国培训的职员统统解雇。然而,Arango将外界对其批评归结于“充满嫉妒的敌对心态”以及“政治迫害”。在2000年的人权监察机构发行的《护民官》杂志中,Arango将自己描述成“正义的化身和法治的骨干”,并将社会其它的人权机构描述成“弥补政治和政府缺陷的伪君子”,“什么作用都发挥不了的社会组织”。*El Difensor,La ética está tallada en la conciencia del hombre,2000,No.95,pp.1-2.同时,Arango对中美洲人权保障委员会,联合国核查小组以及总统人权委员会统统地讽刺了一遍,并且自信地说“只有我才是有良心的法官。我是所有政府机构中最具有良知的”。*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17.
Arango的言行显然不利于团结国内外的人权机构推动。民间的人权团体认为Arango的言行是在不断消费人权监察机构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积累起的政治信誉。中美洲人权保障委员会2002年的年度报告也罕见地对Arango领导的人权监察机构作出了批评:任人唯亲,与国内人权组织矛盾重重,工作成绩乏善可陈。一个由学者团体撰写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公权力机构很少采纳人权监察机构的建议;司法机构,尤其是法院、检察官和警察是采纳人权监察机构建议最少的部门。该报告的学者们认为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的权威在Arango领导下正在不断地削弱。*Lena Bloomquist,Maria Luisa Bartolomei & Fredrik Uggla,Evaluation of Swedish Support to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 in Latin American:November 2001-June 2002,Swedish Institut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2,p.16.
尽管民众以及国内外人权机构对危地马拉人权检察官的态度不甚满意,国内民众却依然对该机构保障人权的作用抱有信心和期望。在Arango任期内,民众向该机构寻求帮助的数量与历史其它同期几乎持平。*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38.依据2001年盖勒普在Arango任期内的民意调查结果,民众对危地马拉人权检察官的信心指数明显要高于其它国家机构。*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20.调查的结果反映了拉美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普遍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国家官僚机构与司法机构常年腐败以及政权对国家机器的暴力迷信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尽管人权监察机构在设立初期职权和成效有限,但是人权检察官积极的态度,与军队和政府不妥协的精神以及其独有的密切联系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特征获得了民众的认可,也为个人和团体在转型社会中解决自身的人权问题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法律渠道。
二、萨尔瓦多人权监察专员机构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
与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建立的背景不同,萨尔瓦多人权监察机构完全是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和平协议产物。1991年墨西哥协议规定战后萨尔瓦多议会应选举专门人权监察机构的检察官负责“促进和保障人权”。1992年查普特佩克和平协定再次提及了建立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并且规定在新的宪法实施后90日内由议会选举人权检察官。1992年2月萨尔瓦多议会首先通过了关于设立人权监察机构的立法,并且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权检察官制度(ProcuradorparaladefensadelosDerechosHumanos)列为宪法保障秩序。
尽管萨尔瓦多人权检察官是由议会直接选举产生并且由宪法保障其独立地行使职权,但是宪法第191条规定人权监察机构设置于公共部(public ministry)之下,隶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与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相似的是萨尔瓦多也移植了西班牙模式的监察专员制度,兼具保障基本权利和监督行政行为的双重功能。宪法第194条授予了人权监察机构广泛职权和管辖权,该条第7款明确规定了人权监察机构能够通过依职权或者依个人申请的方式启动调查程序、得出调查结论、向公权力机构提出建议、当公权力机构不遵守建议时可以对公权力机关进行公开批评、加强与司法和行政机关合作的方式保障人权、对拘留所和监狱进行视察、对国家机构人权项目提出改革意见、对议会人权立法的草案提出建议、游说议会批准或者签署国家人权条约、提出如何制止人权侵犯的建议、发布人权报告以及发展人权教育项目。
然而,萨尔瓦多司法机构的腐败和不健全,行政机构的敌视以及议会对人权监察机构的限制不仅对人权监察机构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甚至也威胁到人权监察机构本身的存在。萨尔瓦多司法机构在内战期间遭受了完全的破坏,*Rachel Sieder & Patrick Castello,Judicial Reform in Central American:Prospects of Rule of Law,in Rachel Sieder(ed),Fragile Transition,St.Martin’s Press,1996,p.182.战后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中直接指出“萨尔瓦多司法机构没有能力调查犯罪和实施法律”。*Truth Commission for El Salvador,From Madness to Hope:The 12 Years War in El Salvador,1993,p.227.尽管战后萨尔瓦多政府迅速地重建了司法机构,并且相应地设置了保障法官独立以及法官评价机制,甚至引入了美国式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制度,然而最终还是无法改变最高法院法官成为萨尔瓦多政党政治的玩偶。无论是总统还是议会都只关注大法官候选人的政治倾向,所以真正有能力且有独立意识的法官往往被总统或者议会排除在外。在萨尔瓦多司法体制框架下,最高法院的权力并不局限于解释法律,同时掌管着全国司法机构内部纪律的制定以及各地方法官升迁的权力。*Margaret Popkin,Peace without Justice:Obstacle to the Building of Rule of Law in El Salvador,University Park:Penn University Press,2002,p.4从UCA在1996年在萨尔瓦多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2%的受访民众认为法官是“诚实”的,高达47%的民众则认为法官是“腐败”的;同时只有35%受访民众认为法官可以独立的行使职权;有75%的受访民众认为许多法官在判案中会受到政治影响。*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p.7-8.
政府和议会对人权监察机构履行职权的行为设置重重关卡。尽管总统和议会无法通过合宪的方式撤销该宪法机构,但是以党派斗争为导向的议会仍然可以通过预算和选举等方式限制人权监察机构发挥预想的功能。相比于司法系统每年一千万美元的财政预算,人权监察机构每年只有不到四百万美元的预算经费。除去支付工作人员低额的薪水外,人权监察机构的经费甚至都无法购买必要的办公用品。显然,获得足够的国际援助是维持人权监察机构运转和保证机构活力的关键。根据一项统计,国际资助占萨尔瓦多人权监察机构2001年总预算的10%。*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36.除了严格限制人权监察机构获得足够的预算外,议会多数党对人权监察机构指责远多于褒扬。甚至全国议会主席Araujo将人权监察机构积极监督政府和保障人权的行为描述成为了“抹黑执政党”,“服务于他们的政党目标”或者“为了实现人权检察官自己的总统梦”。Araujo甚至在2001年接见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时表示萨尔瓦多根本就不需要人权监察机构。为了避免强势的人权检察官对执政党的抨击,议会多数党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限制人权检察官连选连任。同时与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面临的情况相同,具有暴力特征的某些行政部门(例如警察或者监狱部门)以及行政领导对监察机构的干涉是恨之入骨。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经常会受到死亡威胁。尽管还不确定这些威胁信来自何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件比较集中的出现在“政府官员集中地批评人权检察官权威的时候”。*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9.
司法机关的腐败,议会多数党和行政机关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打压不断缩小着人权监察机构活动空间,同时也抑制了监察机构在转型中的作用。因此与危地马拉相似,人权监察官个人性格和决心以及与相应的国内外人权组织的支持对萨尔瓦多人权监察机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监察机构掌握的物力和人力资源有限以及受到政府的限制,在初期民众对人权监察机构普遍地不信任或者不了解。在首位人权检察官Fonseca的任期内,更多的民众选择了向联合国驻萨尔瓦多观察小组请求人权援助。*Ian Johnston,Rights and Reconcilation:UN Strategy in El Salvador,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5,p.66.后期,萨尔瓦多人权监察机构改善与联合国观察组的关系,彼此间加强了合作。为了强化人权监察机构履行职权的能力,联合国观察组为其提供技术和咨询性的支持,并且将主要的工作完全交由人权监察机构办理,必要时协助其开展对人权侵犯指控的调查以及对学校和国家机关的人权教育与培训。*David Holiday & William Stanley,Under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ONUSAL and Challenge of Verfication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El Salvador,in Tomme S.Montgomery(ed.),Peacemak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North-South Center Press,2000,p.56.尽管联合国观察组在人权领域兼具协助机构建设和监督人权监察机构工作的双重任务,但是为了维护人权监察机构的脆弱的权威性,观察组将工作重点放在完善监察机构的建设,因此只有在私下场合才发表对人权监察机构批评的意见。*Reed Brody,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El Salvador’s Negotiated Revolution,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1995,Vol.8,p.152.
1995年随着联合国观察小组在萨尔瓦多的工作结束,人权监察机构完全独立地承担起了调查的任务。同年,议会选举了负责劳工法的女律师de Avilés 就任人权检察官。de Avilés上任之初就积极利用宪法赋予的调查权回应公民的诉求并介入政府机构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积极地调解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de Avilés 重视与国际人权机构与国内司法机构的合作。例如,在资金匮乏的条件下,人权检察官仍然将重要的人权案件邮寄到美洲间人权法院进行审理;积极参与调解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社会冲突的案件;加强同法院以及刑事检察总长的合作,通过司法方式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8de Avilés 努力使得人们逐渐对人权监察机构的能力抱有了信心。在其任期内,监察机构平均每月可以接收到1000封针对人权侵犯和不良行政的投诉信;平均每月可以处理100个投诉案件。UCA于1996年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人权监察机构的信心指数是1.717,远高于法院(1.156),立法机构(0.917)以及中央政府(0.947),甚至也高于广播机构(1.509)和电视传媒(1.704)。即使只有40%民众了解或者稍微了解该机构的运行方式,仍然有超过2/3的民众对该机构有好感。有29%的受访民众认为该机构能够在保障人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超过一半的受访民众认可人权监察机构提出的解决方案。在1998年UCA民意调查中,2/3的受访民众对de Avilés 本人颇有有好感。*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8即使在政府对人权监察机构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后,盖勒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其信心指数(1.67)仍然略高于其他的政府机构。
由于中央政府和议会多数党对人权监察机构和de Avilés本人工作成绩忌惮,所以议会多数党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禁止de Avilés连任人权检察官。为了削弱人权检察官的影响力和社会声誉,议会将腐败丑闻缠身的Polanco推向了人权检察官的位置。更为讽刺的是Polanco本人就因腐败问题成为当时人权监察机构调查的对象。Polanco在上任伊始就开始清理有过人权工作经验的人员,用其在基督教民主党的同志取而代之。终止了同主要的外援机构联合国开发基金署的合作,并且免去了调查部门主管的职务。工作成绩也就迅速地下滑,从de Avilés 时代的平均每月解决100个案件变成了平均每月解决36个案件。2000年2月Polanco由于陷入滥用瑞典捐助的基金而引咎辞职。法律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对于Polanco抱有普遍的否定态度,认为Polanco身上体现出的完全是旧的威权时代的官僚作风,对萨尔瓦多的民主化进程漠不关心;甚至有法官担心Polanco的行为将会导致人民对人权监察机构失去了信任,从而使得萨尔瓦多民众将对所有国家机构失去信心。*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p.9-10.Valladares在议会的帮助下接替Polanco 的职位。Valladares在任期内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政府利益维护者,通过各种途径降低政府在人权方面受到的冲击,对工作人员的利益则是毫不关心。在没有经过任何系统性的权衡下,就将员工的合同仅简单地延长几个月。甚至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试图通过占领办公室的方式将其赶走。盖勒普调查机构在2001年在Valladares就任期间的民意调查显示不到1%的受访民众相信Valladares领导的人权监察机构具有保障人权的能力。值得讽刺的是57%受访民众不信任任何国家或者社会机构人权保障的能力;17%受访民众竟然认为当时最大的人权侵犯者警察是最值得信任的人权保护者。*Micheal Dodson & Donald Jackson,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04,Vol.46,p.12.
从萨尔瓦多申诉案件内容分析,转型时期人权最大的侵犯者依旧是公权力机关。在2000年人权监察机构接到的2752件投诉中有724例是关于公权力机关通过酷刑、不适当使用警力、有辱人格和非法拘禁方式侵犯人权;同时有566例投诉是涉及公权力机关违反了法定程序。*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264.在2002年3303件投诉案件中,多数是对人身以及违反法定程序指控。*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264.缺乏政府支持和资源紧张依旧是危地马拉人权监察机构无法发挥更大作用的绊脚石。尽管在后Valladares时代人权检察官希望延续de Avilés 的思路,积极增强与国内人权组织的合作,加强与司法机构的交流和监督批评政府,并且将关注的领域扩大到儿童权利和社会权利,但是收效并不明显。暗杀、绑架、违法使用警力,受教育权侵犯以及儿童权利缺乏保障依旧是现代萨尔瓦多糟糕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264.
三、秘鲁人权监察机构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
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建立的背景不同,秘鲁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建立于威权统治时代。为了有效地巩固独裁统治,前总统藤森不遗余力地削弱法院和议会权力的同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行政权。*Gladys Acosta & Javier Ciurlizza,Democracy in Peru: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Montreal: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1997,pp.7-14,35-40.在这种体制下,腐败和人权侵犯随处可见。1992年藤森总统通过政变的方式废除了1979年秘鲁宪法。1993年秘鲁议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赋予了总统以及行政机构近乎绝对的权力。然而,1992年宪法第161条授权政府建立护民官机构(Defensordelpueblo),并且独立地行使职权。宪法第162条对护民官的管辖权作出了规定,即保障个人和团体的宪法权利和基本人权,监督国家行政机构以及负有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机构。后者包括监督国家、大区以及市的行政机构、武装力量、国家警察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行政行为。同时,护民官还可以将管辖权延伸到国家司法领域管辖之外的公共服务机构。
尽管秘鲁护民官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会受到藤森政权的制约,但在专制政权容忍的情况下,秘鲁护民官保障人权的实效性以及获得政府支持的程度要好于那些陷入到政党恶斗的转型国家。1992年秘鲁宪法给予了人权监察机构宪法地位,同时也规定了护民官由议会选举产生,隶属于国家行政体系。尽管藤森通过不断扩张行政权力维护自身的统治,但是仍然希望护民官可以发挥监督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积极作用,从而巩固藤森政权在秘鲁的统治。
与其它拉美国家的人权监察机构相同,秘鲁护民官通过依职权或者依照公民申请的方式启动对行政机构及其代理人一切不良行政行为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行为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束后,护民官有权向公权力机构提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警告、提醒以及通过其它必要的改革方式。同时,当护民官接到有关针对司法机构行政事务的投诉时,有权对司法部门展开调查,搜集有关的资料,然而其调查活动不得影响司法机构裁判的效力。如果调查结果确认司法机构违法,护民官有权将违法事项通知司法管理理事会以及司法部。在军队为藤森政权为主要支柱的年代,护民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保障公民在军事法庭管辖的涉及国家和政权安全等领域的宪法权利。例如,在一起由永久性军事法庭审判的案件中,律师Jeri的阅卷权和与蒙面法官的谈话权被军事法院管理机构剥夺。除此案件之外,护民官在一个星期之内收到6位其他律师相同的申请。护民官的介入最终保障了这些律师的权利。*秘鲁护民官资料,编号135-97-DP/AYA。总体来说,除了前总统藤森本人以外,护民官是秘鲁威权统治时期敢于在军事审判过程中挑战军事权威的少数政府部门之一。1996年11月秘鲁军事部门违反法定程序逮捕了Robles将军,人权监察机构对该行为给予了严厉地斥责,因此也受到了来自秘鲁最高军事理事会的威胁。*Mark Ugger,Elusive Reform: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n,Lynne Rienner Publisher,2001,p.37.1997年秘鲁人权监察机构针对军事法院侵犯人权的事件专门建立分析军事审判和军事法令的特别委员会,这进一步增强了军队和人权监察机构紧张的关系。*Tom Pegram,Accountability in Hostile Times:The Case of Peruvian Human Rights Ombudsman 1996-2001,available in website,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5586,p.25.
秘鲁由于从整体上移植了西班牙的宪政模式,因此护民官与宪法法院之间合作关系密切与否将直接影响护民官在秘鲁司法人权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护民官可以依职权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违宪行为,人身保护令、违宪审查以及信息保护令申请,人民请愿以及符合保障公民和团体的人权保障建议交由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和决定。*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201.1998年藤森政权下令暂时中止宪法法院与护民官的违宪审查活动。从护民官与宪法法院合作的期间来看,宪法法院在护民官的帮助下宣布了七件违宪案件。此外,依据政府组织法第9条第3款的规定秘鲁护民官可以作为公民或者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行政诉讼,维护行政相对人基本权利。政府组织法特别赋予了人权监察机构视察监狱和拘留所的权利,护民官有义务对改善、提高监狱管理和保障犯人的权利方面提供必要建议和意见。同时,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下,护民官有权向行政部门、法院或者军事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以纠正上述三个机构违反宪法权利的行为。*Linda C.Reif,The Ombudsman,Good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pringer,2004,p.202.
尽管藤森的支持帮助秘鲁人权监察机构较少地受到军方或者政客的威胁,但是与其它拉美国家一样,财政资源不足是限制人权监察机构有效履行职权的最大问题之一。随着人权监察机构职权和部门的增多,立法机构并没有增加对该机构的预算,甚至在1999年还特意减少了对护民官的财政支持。相比于司法机构九千万美元的年度预算,1998年护民官的年度预算不到五百万美元。获取国际组织或者其它发达国家的援助是秘鲁护民官有效履行职权的关键。从1996年到2002秘鲁人权监察机构获得了总计一千万美元的外援。*Tom Pegram,Accountability in Hostile Times:The Case of Peruvian Human Rights Ombudsman 1996-2001,available in website,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5586,p.9.以2001年年度统计为例,外部援助占秘鲁人权监察机构该年度预算的40%。*Fredrick Uggla,The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4,Vol.36,p.436.
为了有效地维护特殊群体的权利,护民官主动地与国内的人权组织相联系,弥补人权组织财政或者职权上的缺陷。例如,1998年的年度报告显示72%的个人申诉来自于35岁至65岁的男性,儿童、老人以及妇女申诉率较低,尤其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为了有效地保障妇女权利,全国人权监察机构建立了专门的工作部门,用来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性侵犯、国家强制生产以及家庭暴力等问题。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护民官下设的保障妇女专门部门调查大量的国家侵犯妇女权利的案件,并且向政府部门提供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建议或者意见。保障未成年人是秘鲁护民官的另一项重要的责任。尽管依据有关的秘鲁儿童立法,秘鲁儿童和未成年人保护者(Defensoríasdelnioydeladolescente)主要负责未成年的保护工作,并获得国家和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的资助,但是其职权和管辖范围有限,无法向受害者提供任何法律帮助和服务。*Peter Newell,The Place of Children Rights in a Human Rights and Ombudsman System,in Kamal Hossain et al(ed),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d Ombudsman Offices:National Experience throughout the World,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143.因此,护民官会依职权或者相关机构邀请的方式介入到案件调查,给予儿童和未成年保护者机构必要的辅助性帮助。*Defensoria del Pueblo,Al Servicio de Ia Ciudadana,Primer Informe del Defensor del Pueblo alCongreso de Ia Republica 1996-1998 Peru,Defensoria del Pueblo,1998,p.84.
人权监察机构不仅从大众传媒的正面报道中赚取了政治声望,同时也成为解决问题以及向行政机构施压的平台。在秘鲁威权统治时代,护民官与秘鲁的报业达成了默契,后者为护民官在保障人权和监督政府的过程中提供发声的平台,辅助去进行调查活动和公布犯罪情况。*Enrique Peruzzotti and Catalina Smulovitz,Civil society,the media,and internet as tools forcreating accountability to poor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2002,UNDP,Occasional Paper No.13,p.10.媒体的宣传和渲染帮助护民官获得更多的财政预算。在1997年护民官与政府的谈判中,双方就护民官的年度财政预算争议僵持不下。护民官Santistevan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难处,并且向国民许诺在获得必要的资金后增设3个特定部门用于人权保障。Santistevan的诉求显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政府也只能让步。媒体宣传同样帮助护民官得到了更多的外援。
由于藤森政权不承认国际人权法在国内法律体系的效力,因此联合国人权机构无法为秘鲁提供相应的人权教育项目。然而,秘鲁护民官依然与国际人权机构建立了良好关系。除了为秘鲁的护民官提供必要资金外,国际组织和相应的人权机构经常为了声援护民官履行保障人权的职能而向秘鲁政府施压,促使其遵守法律和改善人权记录。护民官Santistevan就指出一旦政府对人权监察机构施加压力,国际人权机构以及各国大使就会站出来保护我们。*Tom Pegram,Accountability in Hostile Times:The Case of Peruvian Human Rights Ombudsman 1996-2001,available in website,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5586,p.21.
Santistevan是秘鲁议会选举的第一任护民官。与危地马拉的人权检察官de Leon Carpio 和萨尔瓦多的人权检察官de Avilés工作作风相似,Santistevan在任职期间积极地履行职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因此与军队部门和行政部门关系紧张。但是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人权检察官处境不同,秘鲁人权监察机构是在威权总统藤森支持下建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在威权体系之下,藤森政权尽管不容忍反对势力的发展,但是也不允许国内警察和武装部门威胁护民官以及人权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护民官以及人权监察机构的人身安全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保证。尽管藤森不是护民官服务的对象,然而与总统保持着良好关系有利于人权监察机构更方便地开展调查工作和解决人权或者行政问题。实际上,藤森本人在人权监察机构建立时就非常支持该机构在不危及自身政权的基础上积极解决不良行政和儿童权利保障等问题,并且默认了护民官在1998年议会报告时提出的其首要任务是维护公民生命与安全的权利。
然而在威权体制内,积极履行保障人权职能的护民官很难与藤森总统和谐相处。这就意味着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在藤森政权倒台之前一直与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处于半对抗的状态,同时也间接地影响了和藤森总统的关系。正如Santistevan所说:“一开始与藤森总统的关系是互相尊重和合作,但是后来就变味了。”*Tom Pegram,Accountability in Hostile Times:The Case of Peruvian Human Rights Ombudsman 1996-2001,available in website,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65586,p.13.由于威权时代的秘鲁政治权威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议会和隶属于行政机构的护民官矛盾重重。两者在日本人质事件后就将摩擦公开化,并于2000年议会选举舞弊事件后矛盾全面爆发。为了有效地控制护民官的挑战,藤森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法院系统之中,试图将秘鲁最高法院变成藤森势力的代言人;并且通过修宪的方式将敏感的政治案件交由特殊的军事法院管辖,并且于1997年中止了宪法法院的运行。
2000年秘鲁议会大选使得护民官与藤森政权的矛盾全面爆发。依据秘鲁宪法和政府组织法,人权监察专员机构有权监督选举过程。选举结束后,贿选丑闻突然被媒体曝光,护民官也收到相应的证据。Santistevan随即声明介入调查,并且公开支持反藤森的政治势力。在媒体和市民社会的帮助下,人权监察机构不断地公布针对选举造假的调查结果,直接导致了民众对选举公平的质疑。护民官也在此次的调查之中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随着藤森贿选视频公开曝光,藤森流亡日本并失去了总统参选的资格。但令人遗憾的是,Santistevan选择了与危地马拉人权监察官de Leon Carpio 相同的政治规划——利用积累的政治声誉参加秘鲁总统大选。
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护民官是秘鲁人民值得信赖的为数不多的国家机构。从1996年至1997年收到的15936例投诉案件到2002年收到的52180例投诉反映了人民对于护民官的信任与日俱增。在后藤森政权从2002至2006年期间,护民官每年接受的个人申诉案件的数量不断地增加,2006年达到了85658例。*Thomas Pegram,In Defence of the Citizen:The Human Rights Ombudsman in Latin American,Paper present V Annual Meeting of the REDGOB,Poitier,6-7 December 2007,p.12.2000年DATUM在秘鲁首都利马市区做的民意调查表明,32%的民众认为人权监察专员是维护民主最有效的力量,25%和11%的民众分别认为是青年学生和媒体是维护民主最有效的力量。从1996年到2000年,人权监察专员受欢迎程度从50%上升到64%。尽管秘鲁护民官在改善国内人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面临由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挑战。
四、结论
除了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选择人权委员会模式外,多数的拉美国家通过移植西班牙模式赋予人权监察机构监督行政和保障人权双重职能。除了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等国是在民主转型后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外,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秘鲁三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相似,都是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建立了人权监察机构。
尽管三国的人权监察机构建立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是国家人权机构在上述三国中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问题在拉美各国具有普遍性。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司法机构的惰性与腐败、恶性的政党竞争以及警察和军队滥用职权导致了人权侵犯现象普遍的发生。民众对公权力机关的不信任直接威胁到尚未成熟的民主政体。因此,拉美诸国宪法赋予了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广泛的职权以及人权监察专员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保障,期待新的国家人权机构能够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以及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或者社会团体提供救济,从而成为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然而,由于人权监察机构无法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所以其只能对国家传统机构保障人权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因此,与国家机关的合作关系将直接决定人权监察机构是否可以发挥预想的效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人权监察机构由于独立行使职权挑战国内行政机构的权威,所以在后威权时代里往往受到议会和警察部门限制和威胁。两国的议会共同采用减少人权监察机构年度财政预算的方式限制人权监察机构履行职权的能力;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限制有能力的人权检察连选连任;抑或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选择倾向与政府妥协的人权检察官,从而削弱人权监察机构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两国的警察和军队等暴力机构是人权监察机构重点的监督视察对象,同时也是民主转型时期人权侵犯的主要责任者。因此,后威权时代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人权监察机构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其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成为国家暴力机关主要威胁的对象。相反,尽管秘鲁的人权监察机构是威权体制下的产物,但是由于获得了来自于藤森政权的支持和尊重,秘鲁人权监察机构可以在政权允许的范围内保障监督行政机构和为受害者提供人权保障的服务。同时,在宪法框架内协助宪法法院和行政法庭保障审查政府机构的违宪行为以及帮助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的权益。
建立国内外人权机构、本国公民社会以及联合国之间的联系是拉美国家人权监察机构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维护自身生存的关键环节。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以及秘鲁的人权监察机构不仅每年接受来自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的资金捐助和人权培训项目,而且联合国、外国政府和国内外社会机构的公开支持为拉美各国人权监察机构抵制政府的压力提供了舆论力量,从而为人权监察机构有力地监督和批评政府机构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国内人权机构负责人的职业态度直接影响着人权监察机构在保障人权和监督行政领域的实际效果,客观上也直接影响着人权检察官或者护民官个人的政治声誉和前途。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秘鲁三国的事例可以看出在民主转型时期积极履行职务的护民官往往受到政府和议会多数党的排斥,然而获得民众、社会媒体甚至反对党的认可。de Leon Carpio 和Santistevan分别以个人政治声誉为资本参选本国总统。相反,如果人权监察专员消极履行职权、无法妥善处理与国内外人权组织关系抑或独断专行,那么尽管不会完全导致民众对该机构信心的丧失,但是会减少民众对其任期之内的人权监察机制的依赖,从而为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和法治的建立提供了负面的影响。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人权监察专员消极抑或积极履行职权的背后似乎都存在着政治目的,不仅限于打击政治对手,同时也有为个人积累政治资本的考量。这就客观地影响了人权监察机构行使职权的中立性,同时也不利于与政府机关缓解紧张的关系以及保障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毋庸置疑,从本文所引述的民调可以看出上述三国的人权监察机构在后威权时代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公民在传统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之外提供了新的救济个人权利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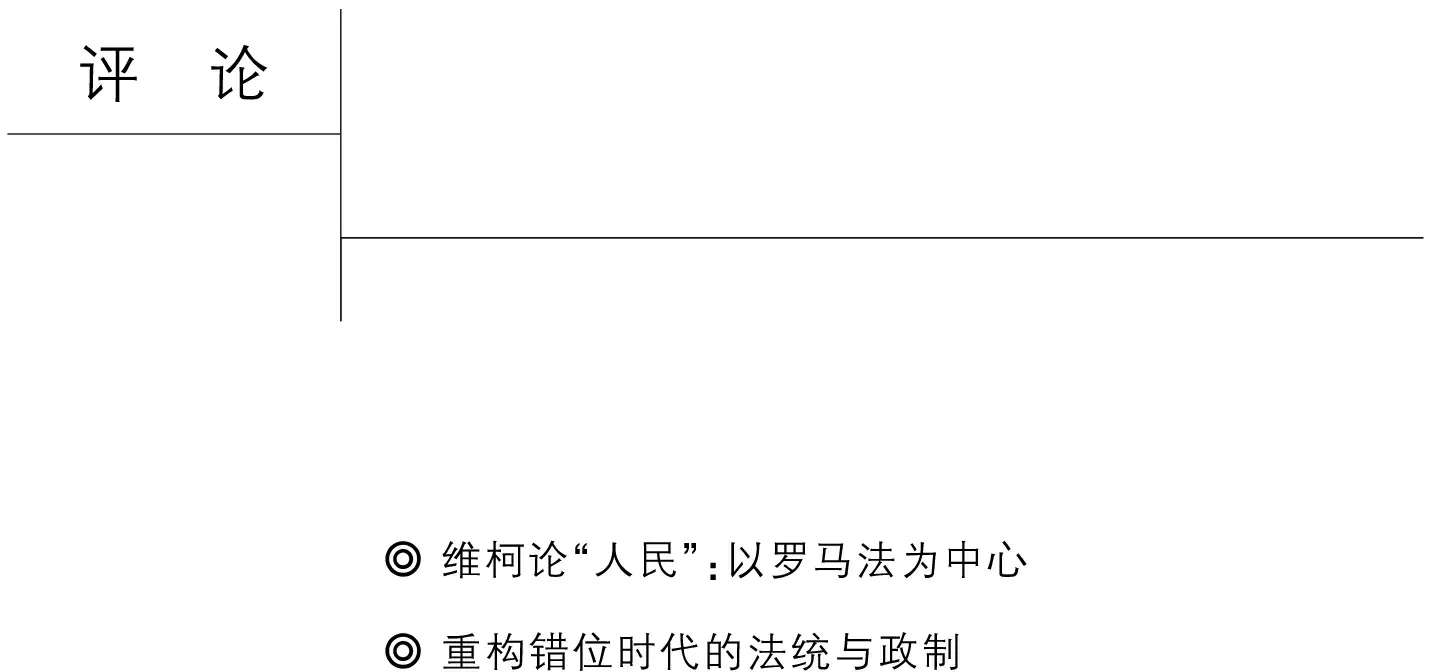
评 论 ⦾维柯论“人民”:以罗马法为中心⦾重构错位时代的法统与政制
《政治法学研究》
*范继增,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博士候选人。本文感谢圣安娜大学Paolo Carrozza 教授和Giuseppe Martinico提供资料和建议,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班文战教授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