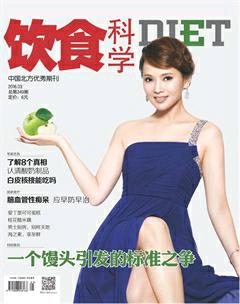旧时岁月甜香炆糖
牛虹
儿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吃零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们半大孩子们都是“吃货”,炆糖成了我们家年前最盛大的事。
炆糖,事先要有充足的准备。自家要准备好的生炒米、花生米、黑芝麻、白糖、老姜和糖稀等材料。每年秋季,母亲找乡下的亲戚买几十斤新上市的糯米和带壳花生,带壳花生买回家后,母亲用布口袋装上一半花生,吊在房梁上,留在春节炒花生用;剩下的一半倒入大筛子里,剥成花生米炆糖用。剥花生是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既烦恼又惬意的工作。烦恼的是,剥久了,手指剥得生疼,筷子都拿不住。惬意的是,可以不时地往嘴里塞一粒花生米,或者将花生米扔在炭火上烤熟吃,乐在其中。自然,被母亲发现了,少不了要被埋怨和责难。
那时,一般人家炆糖都集中在过年前的那几天。糖炆早了,怕孩子们天天惦记,没到过年,饼干筒里炆好的米糖就少了一大截或者见了底。每年,糖坊前炆糖的队伍都排成了长龙。午饭后,母亲领着我们挑着担子到糖坊排队。放下担子后,母亲就去上班了,轮到我们家时,一般都要到深夜了。
那时,我觉得糖坊里的气息是世上最美妙的气息。甜香弥漫在小小的糖坊里,勾得肚子里的馋虫直痒痒。
支一个糖坊要求不高。年前一个来月,炆糖师傅在城郊租用两间带有院子的平房,砌上两口烧柴的大锅,一口是炒锅,一口是糖锅。操作工具也相当简陋,长案板、大糖铲、擀面杖、大菜刀、长方木条和大小不一的筛子及簸箩便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炆糖师傅在我的印象里都长得差不多。通常是两个大师傅外加一个烧柴火的帮工,他们年纪在40岁左右,身板结实,不修边幅,头上压着顶旧的旧军帽。他们话语不多,只顾埋头干活。即便在寒冬腊月,也只穿一件单褂子,腰间系一条大围裙,站在两口大锅的灶台边,娴熟地挥动手中的大糖铲。
炆糖是件技术活,炆糖师傅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先把炒米炒发,花生米、芝麻和黄豆等炒熟,筛尽铁砂后,晾在一边待用。如是花生米,他们会扯着嗓子喊加工的户主,将炒熟的花生米搬到院子里,对着北风口,蹲在地上褪衣分瓣。熬糖稀是整个炆糖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糖师傅将糖稀和少量白糖倒进大锅里,让灶下的帮工少少地添加柴火,便挥动着糖铲,均匀地搅拌,慢慢搅,慢慢熬。待到糖稀挂丝,便示意灶下,不要再添火了。就着灶里的余温,把炒米倒了进去,根据需要加上花生米、芝麻和生姜末儿等。之后,用糖铲快速地翻炒,搅拌,凝成大团后,糖师傅左右操起两把大糖铲,将糖团起锅,摊在了案板桌上,趁糖团软热时,快速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大块,接着切成条状,再改切成小方块,放簸箩里晾着。整个过程需要一个来小时,如果那年炆糖的品种多,有花生糖和芝麻糖之类的,那就要分几锅炆,花的时间会更多些。
时光荏苒,如今炆米糖再也不是孩子们稀罕的食品了,糖坊也逐渐被边缘化。年前,城市一角还会有一两家加工的糖坊,可炆糖师傅都是些60岁以上的老人。母亲每年都要炆糖,给我们每家一筒糖。然而,多数时候我们都忘记吃,直至夏天,炒米糖软化了,就偷偷扔了。母亲一直以为我们爱吃,于是炆糖成了她每年底必做的功课,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