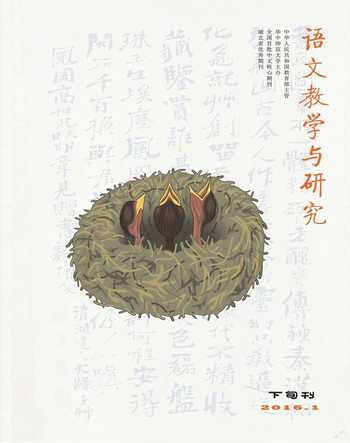点评
李壮点评:在雷平阳的诸多佳作中,这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首。在形式上,这首诗正如其中那个句子所讲,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省和市这样体量巨大的意象(当然还有更宏大的、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热爱的所谓“人类”、“国家”、“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在情感认同上被不断消解,最后只留下自己小小的故乡甚至身边的亲人。这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是情感不断落实、凝聚的过程;意象的减法成就了力量的加法,在一个不断缩小的面积上,压强开始无限增大。在意味上,它具有一种迷人的“不正确性”:作者的爱看上去越是“狭隘、偏执”,反而越显示出它的纯粹和坦诚;而那些看似解答、实不讲理的“因为”,更是强化了一种不可理喻的深情。“针尖上的蜂蜜”作为全诗唯一的比喻,可谓精妙绝伦;它精确、奇崛,并以节奏的变化拓宽了全诗的意味空间,把具体语境中不断发酵的情感漂亮地抽象了出来。而“耗尽”一词里深藏的人间风霜,更值得我们去久久回味。
(李壮: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作者创作谈:我心安处是吾乡。其实,我真正写作故乡昭通市土城乡的文字并不多,而是有些事件、念头,写作愿望,我只能将其放到“土城乡”之上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在土城乡我生活了十八年,对世界、生命、大自然的原初认识大都形成于此,少小经验可以说就是一口永不枯竭的井。需要风景,故乡的风景写起来肯定情真意切;需要河流,故乡的河流就是自己的血管,写它,怎么也不会轻易打滑;需要人物,父老乡亲最动自己的肝肠,写起来自然最贴心。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写作,我才能获得写作的不可遏制的动力,而写作本身也就合理地拒斥了一些悬浮感。由此说,土城乡在我的写作中,类似于一个永恒的母体。再说,在思想、欲望、美学都“大一统”的今天,任何地名都是可以置换的,“昭通市”可以换成中国的任何一个“市”,关键是所谓的地域性是否因巨大的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土城乡又是我写作过程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我大部分的创作都围绕着云南展开。云南,这一个词汇,在心中藏着或在舌头上跳跃,它都存在着丰饶的想象空间,而且因其特有的地理美学和人文精神,它很容易的就会从只有造物主才能数清的地理词汇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它有着辽阔的可塑性,又有着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在古代中国,由于文化和生活空间的互相阻隔,云南一直处在自生自灭、人鬼同在的自然状态中。汉文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征服与吸纳,但往往都是跑马占地式的行政命名,也曾以移民、商屯和军屯等方式建起过一个个汉文化的桥头堡,但乌托邦性质终究撑不起那一片今天多雾,明天又清澈得可以做镜子的天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凭着汉语史料的指引,在云南的山水间去寻找具体的山峰与河流,长期生活在那儿的老百姓往往一问三不知,不是不知,而是他们拒绝认可汉语的命名。汉语命名热衷于传说、谐音、象征,他们命名的山名则看重神迹、祖祇和生活本身。在基诺山,有三个寨子的名字,用漢语说,分别是“初恋”、“热恋”和“婚姻”,这就是汉语假装不能抵达的地方了。
上面原因再加上更多的以“万物有灵”和“道法自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元素,云南从来都有着自己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在西双版纳的一座密林中,我曾看见过一片碑林,人们死后,往往都立三座坟,一坟埋肉身、一坟埋财产、一坟埋灵魂,今生和来世都埋掉,这种有悖于当地习俗的做法,我认为是那些来自湖广的汉人先民把这儿视为了“天堂”,视为了最后的乐土,人世的终点。在这样的土地上写作,“远方”、“世界”都是不确切的,抛开它们,有利于诗歌更贴近于山河。
——昭通市“省耕大讲堂”第二讲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