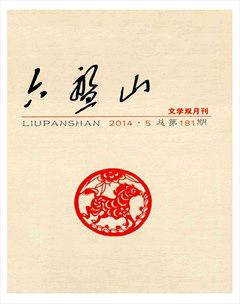兄爱如父
赵凤娟
父母在世时,每到秋天这个季节,我都会收到父亲托公交车捎来的许多农副产品,有土鸡、玉米、毛豆、土豆、小米等,父亲总说城里的东西不新鲜。每次收到这些土特产,我都格外珍惜。我知道,这些土特产沾着父母辛劳的汗水,是父母对我的爱,也是父母的心。尽管我一再叮嘱,我不需要这些,缺了就上街买点,可父亲偏执地说:“自家种的,顺路车,吃不完送同事。”我以为这一切会随着父母的离世将永远逝去了,只能成为一生一世温暖的记忆。
然而,近几年,年近六旬的大哥每到这个季节,总会打电话要我到车站取货,一个大大的蛇皮袋装得鼓鼓囊囊,每次取东西,司机总会和善地问;“是父母捎的吧?”我自豪地说;“是我哥。”车上人总会露出惊奇的笑。尽管我一再叮嘱哥,我的小日子过得很充足,不需要这些,可哥如父般偏执:“自家种的,顺路车,吃不完送同事。”
当我将这一大袋沉甸甸的东西带回家打开,里面一袋袋分装着土鸡、玉米、毛豆、土豆、小米等,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像收到父母捎来的东西那样自然、坦然和踏实,总有一种愧疚感伴随着我。
去年年底,趁着年休,我决定回老家探望一下兄嫂。说实话,自从父母离世,由于工作忙,我很少回去,虽然我生活的地方离老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倒是哥常打电话让我回去,每次我都以上班忙为由推辞了。如今,我们家也买了车,就打电话告诉大哥回家的日期,大哥在电话里喜不自胜,一再念叨:“回来再好不过,回来就好”。我想一来磨合一下新车,二来也让大哥高兴高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大哥辛苦了大半辈子也没坐几回轿车,我要拉着大哥兜兜风,让他在村邻面前荣耀荣耀。
令人苦恼的是离家不远的一条黄泥土路坑坑洼洼、崎岖难行,要是遇到下雨天,别说过车,就是徒步行走也打趔趄。果然,上路那天,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毛毛细雨,一路上我的心始终空悬着,生怕会遇到麻烦,等快到家时发现那条土路修得平平整整,路面上还撒了厚厚一层炉渣。到哥家后,哥远远地就迎上来,被太阳长期照射的古铜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意。几年不见,哥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嫂子早就备好了饭菜,就等我们开饭了。吃过饭,哥和老公攀谈着,我和嫂子在厨房忙活着,顺口就说起出门挺担心那段土路,没想到还挺平整的。嫂子却笑着说:“你哥听说你要开车回来,这些天就没到田里干活,天天修那条土路,拉了几车土才填平那些坑坑洼洼,昨天又害怕下雨,就收集了些炭渣铺在路上。”听到这些,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哽住了,心里涌起了一股酸酸涩涩的味道,眼眶里的泪水不住地打转。我没想到自己回乡这么一件小事,到了大哥那里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突然想起长兄如父这句话。
雨后的深秋,天早早就黑了,屋里也感到一股寒意,我们在大哥的催促下早早休息了。睡到半夜,换了地方的我难以入睡,稍一翻身就觉得寒气刺骨,农村仍用铁炉子取暖。一会儿,听见一阵细小的挪动炉盖的声音,伴随着零碎的一下一下捅火的声音,极其细微压抑着不弄出声响,我无声地注视着那个人,那是哥的身影。大哥一定担心冻着我,半夜加煤捅火,让炉火旺一些,屋里就会暖和一些。哥这些细小的、无声的举动,多像记忆中的母亲。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多少年、多少次就这样默默无闻呵护关爱着睡熟中我们的冷暖,记忆中那个粗粗拉拉高大威武的大哥何时变得如母亲一样细腻柔弱,那时那刻,泪水像泛滥的洪水肆无忌惮地横流。
第二天午后启程,我给哥放下1000元钱,让哥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哥说啥也不要,并一再叮嘱我,父母不在了,哥的家就是我的家,有空常回家看看。看着哥嫂忙碌着将土特产塞满了车的后备厢,我知道说什么也白搭。当车上路走了很远,不经意回头看,村口的大树下伫立着哥凝望我远去的身影,佝偻着腰,飞舞的白发,专注的神情,一如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