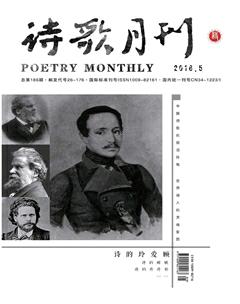难度写作:在精神放逐中坚执
主持人语:
新世纪以来,“难度写作”或“写作的难度”成为谈论诗歌的高频词。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对“难度”的呼唤却众望所归。所以者何?我想时代处境无疑是最大的动因。近二十年来,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泛滥不归的后现代、无孔不入的商品化——这一切深刻改变了时代精神和诗歌生态。诗歌看似走出了小众圈子,变得热闹起来,但其实很大程度上与消费文化形成了合谋,成为装饰后者的花边。在这种情况下,重提诗歌的标准和边界,强调诗歌写作的“难度”,让诗歌重获尊严,也就成了严肃诗人们一致的追求。诗人梁雪波从时代语境的角度分析了当下的诗歌状况,又结合自己的写作历程剖析了自己追求“难度”的心理动因,同时提出诗人应当在现实担当与诗歌技艺之间形成平衡,等。这些观点无论你是否认同,都值得恩考。
——刘康凯
梁雪波:1973年生。1990年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主要写作诗歌、评论、随笔等,作品发表于《钟山》《作家》《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中国诗歌》《诗江南》《诗建设》《山花》等,被收入多种诗歌选本。出版有诗集《午夜的断刀》。曾获江苏青年诗人双年奖、金陵文学奖等。现居南京,供职于某出版社。
“碎片化”已是现代社会的总体表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年马克思在昏暗的煤气灯下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短短一百多年间整个世界变化之快,尤其是随着信息工业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英国诗人叶芝也曾以诗人的敏感忧心于这股文明发展的离心力,他在诗歌《基督重临》中以象征化的手法描绘了人类被抛的现实境况:“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一种没有中心的现代生活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们已被告知并且正在体验着的,它的主要特征是:碎片化、偶然性、易逝性。这种生活被本雅明描述为一种“灵光”消逝的生活,是“断壁残垣”,“新的废墟堆在旧的废墟上”。当年马克思用高度概括性的话语断言了现代性的总体处境,而游荡在19世纪大都市的波德莱尔则在细部上深入体验现代性的“震惊”。都市是展示现代性的主要空间场所。在繁华的巴黎大街上波德莱尔看到了现代生活的新奇、刺激、丰富的一面,也看到了与之共生的颓废、迅疾、丑陋,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出现代生活的两面性:幸福与凄惨,富裕和贫穷。现代都市生活是与传统乡村生活的总体性断裂,它改变了既有的生活方式,包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道德伦理、时间观念等等,人被拔离了土地,成为飘零在光怪陆离的都市上空的无根的游魂。由于宗教的式微和世俗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城市的浮华与喧嚣对个体的湮没,人们每天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却缺少归属感,而物质生活的短暂性和易碎性无法给灵魂提供真正的安慰。
马歇尔·伯曼说,尽管鲜有人将马克思称作现代主义者,但是他的确深刻地洞见了现代社会被“融化”的景象,其深刻性和预见性还在于,他同时指出了现代人无可逃避的命运:“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不得不冷静地直面”,这意味着所有人都置身于其中,无法回避,必须面对和迎战这种“真实的状况”。
随着科技和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中期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时代”,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都在经历着巨变,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相信一种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的断裂正在到来,它将带来全新的社会秩序。这场后来名之为“后现代”的转向最初源自1960年代红色风暴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被证明无效了,愤怒、失望、对抗,使理论家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范式以适应于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的巨变。由于“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和不确定性特点,也因为利奥塔、詹姆逊、波德里亚等理论家在各自阐释上的差异,所以要给“后现代”一个标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可以概括的是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特征:消解中心、反理性、反二元论、强调差异和多元论、消解元话语、反精英、不屈服于权威、蔑视限制、不断创新……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话语,后现代性是以和现代性相决裂的姿态出场的,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利奥塔认为,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是时间顺序上的前后之别,其实现代性中隐藏了后现代性的因子,因此他将后现代概括为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坚定捍卫者,他认为,后现代主张消解主体性,但事实上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后现代敌视理性,但自启蒙以来理性虽然不断被攻击却并没有完全被消解,说明它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哈贝马斯看到资本主义的病症主要是技术理性的过度发展导致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异化,他主张斩断阻碍人交往的“后工业文化逻辑的链条”,建立一种可以对话而不是争辩的“新理性”。他注重语言对存在的烛照作用,并强调现代性本质上是向未来敞开的,它还远未完成。
但是后现代的发展和流行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尤其是在1980年代,后现代成为年轻一代反抗传统的理论武器。在文化和美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其基本特征,即平面化、断裂感、碎片化、复制/拟像等。由于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物质生产空前繁荣,巨量商品所制造的幻觉越来越吸引着人们投身其中,广告、影视、时尚杂志、商城、咖啡馆、酒吧等等共同推动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日常消费品不仅满足了人们奢侈、新奇、爱美、浪漫的享乐主义欲望,它还使商品符号不断激增,以至于消解了商品原来的功用性意义,而导致了一个仿真世界的出现。波德里亚称之为“符号制造术”——花样百出的娱乐节目、瞬息万变的海量信息、丰富奢豪的商业中心、快捷畅达的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经历远比日常生活景象更紧张、更刺激、更具有诱惑力。这是一个超真实的领域,它比真实更真实。凭借这些超真实的模型、形象和编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被其牢牢控制。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而中国的情况是,文革结束之后,从民族创痛里爬出来的国人意识到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个一直进行到现在的过程,就是一个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放弃了滞后的计划经济,转而向西方市场经济学习,大力发展私有经济,鼓励竞争。在对外贸易合作上,通过引进外资,建设发展工业园区,以各种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尤其是城市发展之迅速,已经在各个方面显示出现代都市的属性和特征。就文化方面而言,尽管仍有一些限制,但国门已经打开了,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拦也拦不住。此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各种运动摧折虚弱不堪之际,西方文化因而愈发显示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在诗歌领域,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通过大量译介,被中国诗人迫不及待地阅读、吸收、模仿、转化。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再到中间代,各种诗歌流派和团体,几乎没有不受西方诗歌影响的。因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诗歌理论和文本必然在中国诗人身上留下抹不掉的痕迹。这中间就包括碎片化的精神描摹,强调身体解放的欲望化书写,迎合阅读市场的消费性写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对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探索新诗写作的可能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这个问题要以批判的眼光辩证地来看。现在的问题是,这类写作已经越发呈现出严重泛滥的状况。最初他们以某种极端的形象登场,可能多少是出于一种反抗知识体系的写作策略,但是亮相之后,在其背后却并没有深厚的理论背景,比如对现代性的复杂内涵有所深究,比如对后现代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生态伦理的认识等等。诗人们陶醉于修辞或叙事,满足于摆弄所谓口语,逐渐变得油滑起来,甚至以炮制低俗的色语和秽语为能事。他们试图以反文化的写作显示自身的先锋性,但其实不仅丢失了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切入,而且抓住的也只是西方诗学的皮毛。
“难度写作”的提出首先意味着要面对这两种现实语境,一个是现时代的精神状况,另一个就是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各种病症:精神下滑、道德失范、逃避现实、简单极端、藐视技巧、粗鄙媚俗、哗众取宠、精致夸饰……“难度写作”的命名本身就说明它已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即敢于直面这种“真实的状况”。“难度写作”拒绝那种抚摸生存表面的低吟浅唱,拒绝在语言中放纵欲望、制造官能愉悦,拒绝没有道德底线的写作,拒绝以简单粗陋为特色的反智主义写作,拒绝对词语的沉溺而忽略诗歌的精神维度。“难度写作”强调经验的广度,也就是将“我”放置到广阔的时空当中,万物皆备于心,并以平等之心盛纳和感受事物的存在,以敬畏之心聆听自然的教诲,接续文化的传承。同时,强调一种立足现世而又超越其上的宗教情怀。一颗破碎的心不可能救起一个破碎的时代。“难度写作”倡导一种健康的写作,力图在一个神性隐匿的时代召唤人与自然的整全性存在,通过诗歌这门古老而独特的语言艺术达至世界的“复魅”。
二
由于个人生存的有限性,写作成为一种拓展存在边界的有益方式,这是这门手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秘密所在。所以我说:我写得越多,我活得就越多。而不是活得越长久,因为那不是写作所能给予的。
除了前面谈到的直面时代语境的压力以外,若从具体的写作实践来讲,坚持“难度写作”就是要不断地挑战自己,始终保持精神的纯度和高度,不跟风,不媚俗,努力修炼,使自己保持总体上升的写作趋势,并且不拘泥于单一的表达模式,不断跨界,力图尝试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所以“难度写作”也应包含着“先锋性、探索性、实验性”的自觉追求。
在这方面,我自己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早期我的诗抒情性和歌唱性比较明显,具有叛逆、抗争、激越、奔泻的青春抒情气质,如《诗歌烈士》、《在细雨中呼喊》、《雪夜诗稿》、《雪》、《石头的声音》、《妹妹》、《蒙难的青春》、组诗《歌唱》、《雨意苍茫》等。这类诗写作时间比较早,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当时才20来岁,涉世不深,所以和年轻气盛也有直接关系。后来因为谋生等缘故而搁笔了八年多,几乎没怎么写。直到2006年在周伦佑、蒋蓝等非非诗人的文本感召下,开始重拾写作,写出批判性论文《“后启蒙”时代的奥德修斯》。2008年底写诗的灵感重燃,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这一阶段的作品和以往比较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方面,生存的经验丰富了,思考更加深沉,表达上力求客观呈现,避免过度的情绪宣泄;另一方面,生命的底色变得沉郁了,因此即使是抒情音调也不再那么高亢响亮、一往无前,而是有了更多的低回婉转、隐忍敛抑,我觉得这样才能使诗歌富有张力。
那一阶段我所写的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组诗《利器与兽迹》为代表的抒情诗,其中包括《断刀》《钉子》《雪豹》《雨之书》《闪电》《黑太阳》等,这组诗仍然保持了以往的高音,但是增加了我对社会、历史,尤其是关于权力与体制方面的思考,因而显示出较强的思想力。其实在这些诗的背后有着丰富的阅读背景。在句法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在诗歌气息的运行上不是一泻到底,而是希望实现回环往复、引而不发的效果。《利器与兽迹》这组诗写得很硬,像伤痕累累的战骨挺立在时代的刀锋上,这里面有我个人的伤痛,也有对时代精神困境的承担和批判。诗人周伦佑阅读后给予了“坚硬、明澈、介入”的评价,诗人戴泽锋称这是一组具有“重金属风格”的作品,“其质量是近两年来先锋诗歌中极其罕见的”。另一种风格的诗被我名以《经验之书》,大约20首左右。这组诗语调比较平缓,注重细节与场景描摹,同时着力将诗思深入现实生存经验当中,虚实交错,意象绵密繁复。主要有《修灯的人》《午后》《流水》《活着》《春天的防波堤》等。第三种风格的诗主要是介入现实、以诗的尖钉锲人体制坚壁的作品,现实指向性较强,比如《一个日子正在迫近》、《见证的刀锋》、《一个人的广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等,都触及了最敏感的体制问题。我觉得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正直的清醒的诗人,你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公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自由与公正的缺失,道德的堕落,人心的冷漠等等。因而我认为诗歌不但要有一个能够“消化橡胶、煤、铀和众多月亮的胃”,而且这个胃还应该足够强大,以消化“被失踪”、“躲猫猫”、“开胸验肺”、“强拆”等诸如此类的钢针碎石。我在《为什么我要写<见证的刀锋>》一文中供认:“我尝试在不降低修辞技艺的同时写作涉及时政题材的诗。这并不是为了迎合什么,或以题材之便显示某种道德优越感,不是。我之所以会写,是因为我关注这些,而他们确确实实打动了我、震撼了我,令我揪心,不吐不快。不写出来,就有一种负罪感。”
尽管风格化是一个诗人独特性的标志。但在这里我愿意重温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说过的一句话:“衡量一个诗人的技艺水平,关键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占有、转化以及超越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模式,他的写作是否能使任何现存理论都无法把他摧毁。”
三
面对时代的重重“雾霾”,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压抑而又无力的感觉,诗人由于敏感的天性感受尤深。诗歌究竟有什么用?“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这就像耶稣在沙上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中以这段话说明了诗歌的“无用性”。但同时也揭示了诗歌的无用之用:聚焦、启示、光照、搀扶、以及救赎的可能。
在这个时代,一种不包含道德伦理的写作是可疑的。这种道德立场首先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认识和判断上。作为一名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诗人,他也同时是一个处身于转型时代的现代公民,他的写作能否打入结构性的现实,能否以抗拒现存秩序的方式成为现实的“他者”,从而开启另一种可能的维度,这首先取决于他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认识。黑格尔说,人难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就像跳不出自己的皮肤。而中国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语境,它的特殊性正在于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任何一种标签式的命名都显得幼稚可笑。比如“后现代”为什么不可能涵盖中国的全部现实?这是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能看得清的。由于地区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部分沿海发达城市兴起的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各个地域,而事实上,在西北地区以及广大的农村,生产力的低下、文化的普遍匮乏、生存状况的艰难使人们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阶段。不能因为他们不在我们的生活视野里就认为和我们无关。当我们的诗人沉浸在酒精和咖啡的梦幻当中,品味着一己的小情调,以孤独和冷漠伪饰先锋的时候,有没有认识到这些挣扎在底层的人们也应是我们生存经验的一部分?事实上,当下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文化混合、意识交叠共存的怪胎。一方面,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导,连文化、医疗、教育等本应享受国家政策特惠的领域也完全市场化了,使老百姓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普遍缺少安全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权力并未从经济、文化等领域完全退出,它还时时干预着个体的存在,而伴随金融危机之后的“国进民退”现象,更暴露出在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畸形化发展的实质。在这种时代境况下,那种仍然停留在抚摸事物表面的诗意抒情多少显得轻浮,它们无法嵌入时代的铁幕而留下坚硬的见证,甚至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麻醉意志消解痛苦的作用。而另一些以形式的小小创新来夸大其诗歌历史意义的写作策略,除了说明诗人的机巧心智之外,就只能暴露出其背后灵魂的空洞和回避现实的犬儒与怯懦。
由于后现代的转向,宏大叙事遭到了普遍质疑,北岛那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反抗之声成为历史的记忆。“写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写”,这成为“第三代”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诗人作家的普遍共识。诗人更关心诗歌的表现形式,于是诗歌越写越纯,越写越远离大地,这种不及物的写作因一味强调写作主体的自由和特权、追求文本的纯粹,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关联的纽带,使得当初这种基于良好动机的审美观,于随后的历史运行中在相当程度上走向其悖反,当造就其批判能量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这种批判效能也随之丧失。
诗歌究竟如何呈现时代的道德律令?霍克海默曾经嘲笑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像社会学一样有力量。诗歌的力量何在?诗歌是否可以不与现实发生关联?史蒂文斯推重想象的崇高,认为想象是祛魅时代的最大信仰,诗人通过语言的秩序和内心的整饬来平衡世界的混乱。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则强调,想象力“如果忽略了无法融入到艺术中的现实世界”的话,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无论如何,诗人应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本真的一类人,诗歌在一个真实被遮蔽的时代迫切需要道出真相,唤醒记忆。美国杰出的批评家海伦·文德勒指出:“在一个关注精致多于关注真实的时代,一个人也许必须坚持诗歌的道德力量。”只有极少数诗人敢于站在潮流的反面,在普遍的背弃中面对时代的锋刃。“诗歌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史蒂文斯语)但这种承担只能是个人的承担。当时代的创痛加之于身,唤起你的良知时,你应感恩于这冥冥中的拣选,并把时代的重压在一首反复锤炼的诗中化为精粹的水晶,“在下一个风暴来临之前/把你坚硬的铁一点点熔化在心里”。这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诗歌炼金术,不仅要求诗人有一个能够消化时代尖刺的强大内心,而且需要不俗的诗写技艺,即在审美的愉悦与见证的迫切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我注意到有一些站在体制外立场的诗人,他们的道义和担当令人钦佩,但是他们那种介入式的诗写却常常表现为一种直白和急促的宣泄,有的则近乎谩骂,充满语言暴力,美学意味实在寥寥。更要命的是,那种二极管式思维方式与他们所反抗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异曲同工的。一个诗人不能因为自己站在正义的立场就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允许自己成为诗歌暴徒。中国自古盛产流氓和暴徒,在作家诗人中也不例外。
四
真正的诗人自觉地处身于边缘,对各种意识形态的魅惑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当下,一个诗人的精神立场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权力和金钱的态度上。为什么现在的诗人有很多是人格扭曲的?为什么诗人们那么怀念19 80年代的诗歌嘉年华?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为诗歌保留一块绿茵充足的原野,任诗人们策马驰骋。相反,如今仅靠写诗是难以养活自己的。民刊不用说了,即使是官刊的诗歌稿费也少得可怜,大多是象征性的意思一下,有的甚至发不起稿费。因此与小说家比起来,诗人的现实处境比较尴尬。小说家可以通过出版小说,在图书销售市场上获取码洋上的安慰,还可以改编成剧本在影视方面获取一定的收益。但诗歌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如今一本诗集想要找个正规出版社出版都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诗人高贵的内心开始一点点矮下去了,变得猥琐,甚至分裂。他们可以一面吟诵着神圣的诗行,一面对权力和金钱趋之若鹜;他们可以为一个什么诗歌奖,为一个现世的虚名争来斗去用尽心机;他们今天为节日歌唱祖国,明天为灾难泣不成声,他们夸完了矿工夸首长,他们矫情煽情,Kitesh的眼泪哗哗流淌。
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2009年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对我来说,写作从未成为生活的全部,它只是我用以告别受控的成长,进行精神自治的一种方式。“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同样,诗歌在今天也许难以隔绝大众乌托邦和商业乌托邦的销蚀,但在这个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时代,诗人理应成为权力和市场最难以消化的一根骨头,而在三十年前,它曾经哽住过一个可憎年代的咽喉。诗歌就是思想和语言的骨缝上绽开的鲜烈之花。
所以,从具体现实来看,权力和金钱对诗人仍具有较大的收编能力,它们严重腐蚀和破坏了当前的人文生态。若从全球生态角度来看,人类的过度攫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已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想一想最近这几年频繁发生的大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大旱等等灾难,是不是地球在对我们人类实施报复?)因此学者们从整体主义哲学的角度提出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和自私,以“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平等观消解主客二元的本体论,强调万物与人具有同等的存在价值。这种思想反映在诗歌写作上,就是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对万物和未知保持敬畏之心。而诗歌作为一种延续上千年的精神存在物,它与诗人的遇合蕴含着一种相互拣选的宿命。因此在更高的意义上,写作就是一种精神修炼,即在语言中安置灵魂。
诗人行走在大地,但头顶着天空,他要穿过一片倾圮的圣殿和狂欢的人群,他必须在一种自觉的精神放逐中坚执爱和感恩之心。他倾尽一生努力抵达的地方,是朝霞的远方,是生命的终点,而它或许将成为另一个人的隐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