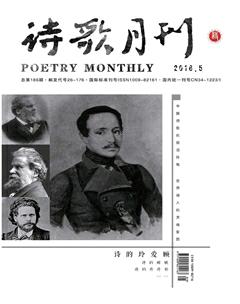姚辉的诗

主持人语:
作为一位有着近三十年诗龄的资深诗人,姚辉一直保持着非常纯正的抒情气质,他的诗富有激情,总是以繁复的意象、跃动的诗句反复表达对生命、世事、时光的困惑与追问j但他并没有滑入浮泛的抒情,而是常在情感的激流中融入智性的沉思,从而让诗意呈现得更为丰富和深沉。舒丹丹以诗歌翻译名家,这多少速蔽了她的诗人身份,其实她在诗歌写作上也取得不小的成就。她的诗惯于取沉恩和回忆的调子,通过对日常细事或微妙感受的描述,传达对生命的复杂体验:既有孤独、隐痛和丧失感,也有宁静的欣悦和深沉的感恩。简洁、克制的表达与丰富的诗恩形成恰到好处的张力,体现了诗艺上的成熟。
——兰坡
姚辉,男,汉族,1965年生于贵州仁怀,出版诗集《两种男人的梦》(二人集)、《火焰中的时间》、《苍茫的诺言》、《我与哪个时代靠得更近》(中英对照)、《在春天之前》,散文诗集《对时间有所警觉》,小说集《走过无边的雨》等,另编选出版了诗文集多种,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卅『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陌生之鸟
或许灵魂深处总有一条邈远的路径
供鸟翅静静滑翔。这些陌生之鸟
嘈杂
锐利坚韧——宛若一片片
闪烁不息的幽深弦月
我不知道它们彤红的啼鸣
是否与我们反复瞩望的旗帜有关
熟悉的天色缓缓上升触及星空与爱
我不知道那些乌翅边缘的云霓
是否仍将覆盖人们坚持不懈的夙愿?
我无法说出它们漫长的等待。鸟
守候鸟的历史守望尖喙中深藏的季候
——我无法说出一代代人欲说还休的苦痛
乌在路途中苍老陌生之鸟
带来我们絮语多年的所有经历
看:一只鸟燃烧成流星吱呀的身影
它比沧桑迅疾它掠过谁生锈的怀念?
那只篝火铸就的鸟翻越山峦
让天穹弯曲的湛蓝不断延续
陌生之鸟仍将唤醒谁熟悉年年的苦乐?
风声压碎缄默群鸟
消失——在我们虚构的骄傲中
鸟影坚硬鸟影
正刺透灵魂无力背弃的最初警觉……
忏悔者
被一片落叶遮掩也是值得的
——风忘记风声 忏悔者
躲闪着 那片落叶凛冽的痕迹——
活过的所有昼夜成为利刃
悬在张望上你错过了命定的暮色
就必须再次错过 那叶逼你醒来的启示
水势推远唯一的航线
谁寻找不可能出现的远方?谁吹灭火焰
让一颗星 在无尽的黑暗中
反复疼痛 追悔莫及?
被一片风声代替也是幸运的
落叶知道苦痛的份量 风剜碎祈求
忏悔者背对的花束 再次
卷过 一无所有的大地……
野山之幻
夕照颤动了七次 岩石
猝然忆及烟尘之远 夕照有微红的光焰
比鸟翅华丽 璀璨的岩石
让野山沉入春天内部旖旎的预感
野山跃动 这麻雀般的顽童
用黑泥 捏制霞彩与悠悠企盼一一
野山袒露麦苗招展的疼痛:山色锈蚀
但一个人坚守的挚爱宛若花束
幻梦状的花束 随起伏的故乡
代替与生俱来的种种眷念
野山记得祖辈吱呀的名字 记得
雨滴中的灯影 肋骨弯曲的绚烂
野山记得窸窣作响的苦痛 风声黝黑
野山记不住似曾相识的诺言
谁在飞翔的冈峦上剜刻宁静的琐事?
野山蜿蜒如诉 在典籍倾泻的遐想里
野山 擎着灵魂摇曳不息的湛蓝
野山翔舞 卷过夕照珍惜多年的祈愿……
神
在土粒之上 神 有着青草广阔的色泽
神用三种草茎做成姓氏最早的偏旁
神写出自己的乳名 然后 神
用一抹黄昏 锻造乳名上黄金的记忆
神有土粒多变的脸色 较大的风声属于怀念
神用风声遮掩膜拜者伛偻的身影 神
在一粒稻谷上 雕刻艰难者闪耀的祈愿
神说出千种曲折的未来 在伤痛与瞩望间
神的沉默高过星河——神让天穹沉睡
让最弱的星光散开 覆盖尘世最远的宁静
神经历了我们扔弃过千百次的苦乐
神的灵肉上刻满伤痕 恨 爱与启迪
神是阴影的寄居者 是花朵枯落的最初症结
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最为尖利的遗忘
神被神反复忽视 在土粒之上
神的独语失去回音——神是神自己的启示录
神高举的骸骨走过远方
神 找不到自己燃烧的足迹
神藏在木纹深处
在一滴水和其他水交错的忆念中 神
向一堆虚假的背影投掷石头 神有些困乏
神 背弃着自己无端的宿命——
神在风霜的尽头转过身来 神越过我们
——在阴影铸就的沧桑中 神成为神话
进入 我们难以闪避的所有歧途……
城市之夜
许多人在尘埃与欲望间走着
——赤裸之城 多少匆忙的骨头
在人缝中 划出大片交错的暗影
谁将向自己挑战?用一把纸币作借口
深入千种陌生的姓名——
谁弄丢灵魂的重量?面对烛焰
谁 喷溅的狂热没有回音?
城市改变历史
历史改变伤痕
许多人在灯盏与曲折间走着
少女的衣襟上
花朵起伏
许多人 已习惯了最美的沉沦
这城市之夜涂旧面具
我回转身来 看着远方
我将在不朽的苦乐里
抠出 青砖与霓虹黝黑的呼声
感激
——少女擦干了绯红的泪水
像花朵栓系的千种苦乐 少女
成为花瓣深处吟唱的记忆
大雨代替怀念 星辰的力量鼓荡花香
这些执着的芬芳 让文字之外的季候
随道路漫长 弯曲……
懂得感激的人可以成为启示
灯盏般剔透的启示 倾诉般
传递姹紫嫣红的颤栗
也许 一朵花就是一处伤口
疼痛穿越沧桑 也许
一朵花 带来醒目的寄寓
——如果只能感激
我们重叠的身影将点缀漫漫荣光
生涯漫长 我们有孤帆闪烁的旖旎
手
三十年前 我看见一只手从空中划过
遍布毛羽的手 用五种方式啼叫
黄昏像一个记号:三十年前
父亲踏着苦痛归来 所有田野
都换不回 那把金黄的稻草
我看见一只手 从风中划过
墙壁在族谱上 烟熏的日子
可以被风车额际的星星 照耀
土 从眼中吐出!掌纹经过的春天
静静翻开——唯一的手
显得比历史苍老
而我看见手从文字上划过
三十年前 我还没能学会哭泣
一只手 躺下 像一柄悸动的弯刀
父亲被写在手上 三十年前
指骨分散了风声 所有眺望
都比被反复眺望的时辰 更为重要
打铁的人
提着废铁前来的女人提着一弯弦月离去。
只需要一炉赤红的吆喝 你就逼近了尖锐
但请你记住我古铜的汗水 记住
叮当作响的手势 请记住我身影上
纷纷坠落的金色尘屑
记住 耻骨以及最远的风俗
我锻造过怎样弯曲的晨昏与追缅?炉火明灭
我把鸦啼打制成一枚黄菊状的灯盏
我将它悬在胸前 然后
我打制山岚不懈卷动的辽阔
打制水势将至时呼啸不息的那次追忆
歧路可以淬上最好的钢火 让它接近诺言
接近卡在骨缝中的痛与事实
而更多的苦乐在铁砧上翻转
我打制谎言可能拥有的第一千种形状
打制沉默的暗影 打制总也无法出现的唯一惊喜
我打制过太多的欲念——
诱惑与警示常常具有相同的陡峭与硬度
我打制坚硬的软弱 打制淬毒的善意
提着弦月前来的女人提着一块黑铁独自远去。
鸟
——为一只鸟的死亡而作
或许 已没有人能再次目睹那些消失的飞翔
在冬天结束之前 星盏高悬
或许 已没有一种疼痛
能代替飞翔消失前的那片光芒
已过去多少年了:彩翎上的风声
卷动空前的凝望——
我 以及更多的人 为一页油画的天空骄傲
我甚至是幸福而孤寂的 一只鸟
——飘飞的岁月充满了叽喳不绝的声响
但或许幸福也注定了苦痛 就像一个字
——翅翼经历的沧桑 难以虚构
就像一次许诺 呵 密云代替典籍
一句古老的颂辞
变得道理般坎坷 漫长
我甚至是忧伤而坚韧的
冬夜漫漫 一只鸟
一只消失的鸟 以骨肉 概括着
生与死鲜艳的方向……
谈论
“向昼夜学习的事 我已思考过了”
翻动书卷的声音现在变得十分响亮
——声音从眉际划过:“……很多年前
书卷依次摊开:那些劝喻始终是灰暗的
我们刻苦练习的晨昏渐渐蜷曲
劝喻者 成为鸣叫的黑猫 站在墙角”
谁的身影跃上了现在的天空——?
“至于幸福 可以从骨肉谈起……”
如果指点的手势疼痛
证明世界开始变了 而世界也将疼痛
——“如果灵魂已堆满华丽的词句
灵魂有可能代替碑石?”
有人在书卷的最后一页上翻查出未来的天色
“呵这是苦晴 这是别无选择的阴
这是擦亮梦境的雨……虚假之雨”
“我也想褒扬城乡间纷杂的梦想 锄声 酒
在市街上反复碰撞的名字……”
“一个人代表时代。一个人
代表了怎样的时代?”
“而向美与丑学习的人交替出现”
谁这样说?让他站起来说。
让他走到高处去说。看透时事的目光渐渐浑浊
“没有谁 愿意用争辩者涨红的脸
拼贴 某种有益的日历。”
傍晚的河
我和谁都说不上话了——河边
空无一人 只留下 满地
浅绛的人影……
我和谁都说不上话了。鸟翅高悬
太阳将斑纹刻写在史册中
——谁的史册?疼痛的人影
压碎 疼痛的其他人影
大河凿下人影毕剥燃烧的声音。
——我和谁都说不上话了
傍晚的河 颤动 盘旋
它说出了我们试图隐忍的一切
夜
从一片弯曲的墨渍中穿过
我听见 许多疾驰而至的往事
我听见诺言。灯盏渐次挂满骨头
秋天已经倦了 它的身影
让空旷的日子变得缓慢
守候在远处的人此刻能否幸福?
隔着灰暗的雨 谁反复回忆?
谁回忆的手
攥痛 花事与璀璨?
家园打碎凝望
而我已无法简单慨叹了——
我不是可以随意骄傲的人
当夜雾升起
虫蛾之梦斑痕闪烁
一个足迹 就是一页新颖的火焰
那些熟悉的道路正在夜色中走远……
梦游者和他的第三种暗影
那时 兄弟还是一把燃烧的骨肉
他从门槛顶端迈出 如吱嘎的烛光
他经历的坎坷 有着梦境般模糊的弯曲
他被生涯碰软了膝盖。弦月比追忆遥远
窗花开始拥有芳香 岁末的风
吹彻 兄弟守候已久的奇迹
他还经历了变幻的草色:此刻是枯萎与焦黄
但它有过翠绿的远方 那时
兄弟像一声踉跄的叮嘱 像一次呓语
门外 巨杉静默 歧路越过警示
一百种寄寓成为险峻的苦乐
——兄弟消失 带着
天穹压斜的最初疑虑
而兄弟随火焰重现 从门槛左侧
兄弟嵌入荒芜之痛——
他只记得两种暗影 在消失之前
第三种暗影湛蓝 从星盏内部
暗影上升——这样的暗影
依旧泥泞 锐利
歌
像一片暗夜。尘土之唇被轻轻翻开
喏那是什么?
——星星的躯体。
而一转身你便打听寒冷
现在诺言滚动
谁将放弃爱与骄傲
谁将携着叶影远去?
敲打花朵:让我为你抖露芬芳
荆棘的喊叫转瞬即逝
让我学会忘记
谁在血滴中剜出女人与风暴?
她们曾经疼痛她们
还将不断地站起
一片暗夜。丁香裸露
手藏在火中
火在歌里……
请举起星星的骨头
日子坚硬苦痛
正在最初的祈愿里延续
向日葵
把头颅扭过去 你看见风向偏转
——歌者坚守的苦痛 带来
黄金般凝重的灿烂……
一代代人回溯的晨昏不懈旋舞
谁骄傲?缄默的歌者 醒在风中
他的期盼 让阴影开始震颤
炎凉深入千种灵肉
骨殖在鸟翅上 那是翻飞的骨殖
经历春夏之交的眺望
正成为 击碎生涯的痛与习惯
而有人依旧艰难的活着
端坐在追忆之巅的人 忍受幸福
像葵影高扬的警策 有人
沉入无边的挚爱 或者厌倦
向日葵被一滴雨意覆盖
它有些冰凉
一个时代垂下炽烈的羽翼
葵影燃烧 仿佛种种球状闪电
向日葵放弃的天色比遗忘更为遥远。
候鸟
丢弃一些季节 在天堂的路途上
我们的跋涉 高过了星光
冷暖之间 艰难的飞翔是一次照耀
往昔的风吹乱典籍
我们的道路 也是自己的梦想
雪霰惊醒过多少名字?
山川蜿蜒 我们的骄傲
带动了远方……
我们常常只能属于怀念
市街上 黯淡的身影渐渐生锈
我们目睹的一切
都可以被叫作沧桑
孩子啊 你这即将衰老的骨头
孩子啊 你是否还准备着另外的歌唱?
回到一些季节。在你的翠绿里
那片匆忙的毛羽
正闪射出 安慰般辽远的光芒
家
一千条路通向同一抔滚烫的黑土。
通向同一阵雨声。旧檐下的天色深入骨髓
谁忘记过山峦疼痛的季候?在一阵雨中
谁成为黑土反复咀嚼的坚韧祝福?
一千条路通向同一坏飞翔的黑土。
通向一次咏唱:孩童被祖先的牌位砸伤
这样的伤痕如何成为骄傲?孩童在泪滴中
奔走像一片粘满黑土腥味的季风
孩童闪耀种种映照生涯的光束……
一千条路通向同一抔梦呓的黑土。
稻禾拭去太阳之影 在我们回溯的黄昏
一个时代褪下燃烧的微记!脊梁之上
有我们坚持不懈的爱憎——我们
蘸着星光写下曾被无端遗弃的所有叮嘱
一千条路,通向同一抔醒着的黑土……
窗外
叶子带走了部分天空。窗外
在倾斜的枝节与琐事间
一个孩子温习着
阳光之舞
五月是藏不住许诺的唇齿
把青果递给天空——五月俯身
谛听大地奔跑的脚步
而鸟儿已绝不仅只是一阕染翠的吟唱
通过苍穹 我们临近的往昔正绽露霞光
在窗外一个孩子
说出了五月最初的幸福
季节搁在窗外
一个孩子 为何懂得了
那次命定的恸哭?
——窗外 布满了父母的手势
一个孩子 舞动
人影 渐渐淹没了所有弯曲的道路
船
这一刻 你说出星星璀璨的追忆
在砾石挪动的空旷中 你说出祝愿
说出一片激流暗黑的执着与爱
你把桨声搁在暮色上 现在
你有疼痛的潮汐
你注视过多少隐没的雨意?
那时 砾石还有一片翠绿的羽翼
它们飞翔 用身影覆盖你的忧伤
那时 水还没有放弃燃烧
你拾起被阳光穿透的诺言
你在粼粼波光中接近世界最远的安慰
你让水势随期盼 弯曲
这一刻 你说出疾风铸就的缄默
在锈迹斑斑的波澜上 你
说出白帆之痛 说出
我们守候多年的恨与祈求……
早晨
谁目睹了星光艰难的消失?
当参差的梦境 晾晒在锁链之上 谁
避开嘈杂的祝福 为白银的天穹
找到了 一次最好的开始
一个长夜在沉沉的麻木里无助地结束!
一个世纪。谁收拾好了锈蚀的身影?
当承袭千年的呓语改变沧桑
一个长夜 正退出碑铭般坚硬的盟誓
凭借不同的警觉 人群醒了过来
人群:树桠上遍布鸟鸣
那滴易碎的霞光
是谁横亘荒野的坚持?
谁在古老的雕像上读出了迟疑?
踏遍晨光 谁
说不出念叨过千载的往昔?
而一个早晨常常只能倾向失败
我这样想着 我不知道
该把什么 正确地推迟
石榴树之忆
旧檐下的石榴树 让四季飞旋
——当风雨上升 祖先的身影
在布满苔痕的晨昏中 再次浮现——
我在榴花呼啸的夕光里 捡拾
鹰翅掠响的隐秘
种植石榴的人成为云霓
他有刀刃的光泽 他与石榴树以及怀想
保持着火焰般迢遥的距离……
而远去的歌者为某种骄傲活着
生涯是艰难的 石榴树以扭曲的疵痕
代替缅怀——石榴树的疼痛
随苍茫剥落
我在暗黑的鸟羽上铭刻石榴树摇曳的宁静
风声坚硬 压碎 星月之忆
石榴树跃上云朵
像一片 燃烧的鹰影
一千种花 朵倏然绽 开触动
歌者赤红的遗忘
雪
被遗忘的一切重新出现。人影呼啸
泥泞淹没了所有的起点及追忆
雪卷过。苍老的失忆者正在醒来
他有铁质的缄默——哦 六角形的缄默
比火焰占据的梦境 更为遥远
他无法说出此刻的雪色还将隐藏是什么
苍穹有过太多的警示 他无法见证
雪粒转瞬即逝的全部凛冽
或许他还记得某个说谎者尖利的暗影
仿佛星辰深处的疼痛 谎言
超越难以掩饰的美 刀刃般的谎言
剜过 我们共同的祈愿
雪就这样下着 尘世值得被反复遮蔽
你还将忘却什么?
寒意来自灵魂之外 骨肉
值得被反复撕扯 遗弃
一个骄傲的失忆者说出苦难
而烛焰找不到燃烧的理由 它
退回到巨大的黑暗中 人影呼啸
——被沧桑捶击的人影 带来
大片飘飞的预感
掘墓人
掘墓者从黄土深处翻挖出一块嗥叫的白骨——
他喘一口气 细心地嚼一口黄土
他尝出了酸辛的某种滋味——“它为什么嗥叫?
狼养的白骨!你嗥叫什么?”
他必须再次举起锄头 他必须挖掘
新亡故的人需要迅速埋葬 但白骨仍在嗥叫
那些彤红的声音 旋转 像大把倾斜的星空
“你为什么嗥叫?”黄土一层层摞着
姓氏上堆满姓氏 死亡覆盖死亡
而枯萎的花香中正不断跃起新颖的花影
哦 死亡抬高了生存——“它嗥叫什么?”
但黄土的滋味有些锐利 它割痛了谁的麻木?
掘墓者眼中涌出泪水 白骨倏忽无声
躺在黄土中的白骨 孤单 坚硬
它 似乎丧失了嗥叫的勇气
又一层黄土被铁锄掀开
——我是被落日隔开的歌者 我凝望什么?
掘墓者将白骨揣在怀中 静静睡去
二月
道路悬挂在冰凌之上
风翻越树梢 紧紧按住
死亡抖动的暗影——
大雪经历的晨昏依旧凌乱
山峦上 巨树雕琢灰褐的空旷
一条路 即将通过
我们遗忘多年的天色……
我在一粒尘土上找寻岁月的回音
在冰凌锻打的道路上 我想找回
尘世可以反复忽略的种种印迹
也许 二月只是一份忠告
属于黑色羽翅和不断皲裂的手势
一滴水回到典籍中 成为
苦痛凝结的最初启迪
而我在二月的肩胛处开始了苍老
——像太阳颤栗的光芒 我
在二月无边的警觉里
枯卉般 学会了诉说与承受
——风成为千种道路
谁 找不到爱憎的方向?
在二月与遐想间
那个缄默的人 正消失在
我们试图握紧的风声里
与水车有关的人
我是在水车的阴影里死过一次的人
那时 我是鸟 是一片吱呀燃烧的泥渍
第二次死亡来得更快 冰凌封住了赞美
泥鳅从水声中探出头来 喊出我的名字
水车缓缓转动 我只能死在
水车以赤红的方式转动的那一刻
我也呼喊泥鳅的名字 那时
泥鳅用西风冻红唇印 热泪即将沾巾
但哭声被夕光卡住 泥鳅灰暗
谁能让水车停驻?我 只能再次死去
被反复虚构的死亡渐渐有力!
大水带来季节与怀念 这一次
黑蛇随水势摆动
像一缕吐着赤信的星光 黑蛇消失
我死在最为漫长的千种凝望深处
然后是水车与黎明的死亡。吁声。
碎裂的波光 再次涌动
东边的云霓成为姓氏上闪烁的夙愿
我醒来——水车畔的黎明
带着巨大的暗影 旋转
我是注定要反复醒来的人
我拾捡晨光 喊出
你们易碎的种种隐秘……
挽歌
——拜谒明十八先生墓
第一颗头颅属于刀刃般嘶叫的罡风
第二颗头颅反复跃动 它只能碎裂
而第三颗头颅被乌鸦占领——谁的乌鸦
卷动 大地疼痛年年的忘却?
第四颗头颅上的天色苔痕遍布
第五颗头颅留住了唯一坚硬的骨气
哦火焰的骨头!一个时代
正陷入千种漫无边际的苦痛警觉
第六颗头颅比山势险峻。雨季旋转。
第七颗头颅闪光 它比梦想更为高远
然后 它坠落 留下
道路般弯曲的痕迹……
第八颗头颅业已苍老 风霜覆盖旧事
谁被剑戟逼到苦难尽头?
第九颗头颅 成为 苦难最初的结局
从第十颗到第十七颗头颅
炎凉转瞬即逝但灵肉间锋利的爱憎依旧
那些不变的襟怀 又一次
触动 我们理当固守的所有夙愿
第十八颗头颅是曾被遗忘千次的头颅么?
山川自梦境中醒来 它有彤红的翅翼
映透生涯的红 让头颅之光 闪烁
或许,所有头颅都在让如画的江山恒久升腾。
虎
用白纸剪一只老虎可能是安全的
用绢帛则未必。绢帛与魂灵相关
——当老虎跃出绢帛 你会打碎
那片时光磨砺已久的迟疑
绢帛与典籍及血脉相关。老虎
有斑斓的寄寓 它属于文字压不垮的
晨昏的一部分——你膜拜过的星空
猝然变黑 但虎脊上的风声
依旧晶莹 迷离……
虎的眺望触及更多的伤痕或者梦想
苦乐转瞬即逝 你刻写过的眷念铮然有声
而你无法用一张纸 剪裁出
老虎迅疾如风的启迪
老虎即将消失 如一则寓言
老虎留一痕爪印在天穹中 谁张望?
你的身影 铸就 老虎燃烧的追忆
半山亭
——张之洞读书处遐思
只需要一半的山势 就可以进入漫漫历史了
重要的山势 是谁坚持已久的企盼?
童稚的春天 瓢虫拧转凝望
典籍上 传来 另一种澄澈的天色
在岩石上刻镂星空的人渐渐进入穹庐
看 蓝色星光 挂满藤蔓与记忆
另一半山势是否可以再次陡峭?
另一半山势 呼啸 那是值得被反复虚构的璀璨
——山势斑斓 一个人回到典籍中
呵 典籍中的人 让昼夜 不断闪烁
唢呐之夜
最好让它就这样在空旷里 静着
不吭一声 像油灯的第二种身影——
就这样静着 铜铸的怀想有些冰凉
它在稚嫩的春天曾扶起过天穹 那时
它有诺言与骄傲 有天穹蔚蓝的声息
静着。让它在祖先微暗的足迹中找寻未来
它记得旧时的腔调:山峦与水的腔调
虫豸酡红的腔调——梦境被星光传递
它记得少女苍翠的笑 一滴露水
经历了 生命可以承载的所有际遇
它静着。远处有被淡雾遮掩的歌谣
——火的歌谣 带着雪白的羽翅
翔舞——它静着 月色已刻满风声
最好让它找不到倾述或遗忘的理由
让它贴近自己的辽远 像一次瞩望
让它随那片灼热的杜鹃 远去
慢慢越过 我们不懈的企盼
让它忘记曾经有过的吟诵 忘记
痛与痛应有的间隔 忘记挚爱与恨
让它静着 不说出暗夜最初的隐痛
不随意幸福——让它高举退想
成为 唢呐自己艰难的夜色
——让它学会燃烧
学会在黄铜碎裂的咏唱中
一遍遍 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