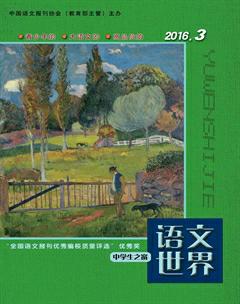一杯清茶话梅花
唐雅冰
秋日午后,就着暖暖的太阳,泡一杯腊梅茶,看阳光在舒展开的腊梅上浮起又沉下,惬意而优雅。顺手翻开诗页,梅绝对是诗行中的活跃分子,一直备受文人墨客青睐。我不敢附庸风雅,却也喜欢“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恬静;喜欢“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的豪迈;喜欢“一声羌管无人见,无数梅花落野桥”的清幽;喜欢“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的孤傲;喜欢“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悲凉;喜欢……
对梅的认识,不是来自诗中,而是来自爱梅如爱诗的幺爷爷。
幺爷爷从私塾先生坚守到人民教师,受过弟子的三跪九拜,也有过被贴大字报的痛楚。他不谈政治,与世无争,只是一个天天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栽种花草的慈祥老人。幺爷爷爱花,门前街沿上摆满了各种花草,兰花、棋盘花、紫罗兰、夜来香、胭脂花……那么多花,四季飘香,他却最喜欢那盆含笑梅。幺爷爷常常置之案头,墨香就着花香,吟诵一首首诗词,给孙辈们亲笔书写一本本字帖。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含笑梅,在我稚嫩的心头,含笑梅成为梅花的代言,脑海中所有有关梅花的诗词都打上了含笑梅的烙印。
在一个含笑梅含苞的日子,我站上了讲台。初上讲台,面对一群野性十足的农家小子,我有些手足无措,不到一周,我便光荣“失声”,金嗓子喉宝成了包里的必备品。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掐来金钱草、过路香、薄荷等给我泡水喝。也是那个冬天,母亲专门回了她的娘家一趟,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一大包黄色的花。她一打开纸包,我小小的办公室立即弥漫开一股淡雅的香味,沁人心脾。从那天起,我才知道原来梅中还有这样的仙子——腊梅。母亲告诉我,腊梅花泡茶可以消炎。我每天进教室前都会泡上一杯腊梅水,看那薄若蝉翼的花瓣在水中慢慢舒展,直到染黄一杯清水,把白开水变成氤氲袅袅香气的花茶。就这样一天一杯,窗台的新鲜腊梅慢慢被风干,慢慢减少;当一包梅花都成为我的杯中之物后,我的嗓子竟然慢慢好起来。母亲却依然每年都会回她的娘家,给我摘回一包腊梅,晒干后装起来放在我的书桌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环境的变化,我又认识了用一片红艳报春的春梅。梅花,一如岁月的雨滴,就那样浸润进我的血液,我与梅算是结下了一份不解之缘。
一日,我偶然在学校花园里发现一丛非常艳丽的花,开得灿灿烂烂、热热闹闹,娇艳的玫瑰红煞是惹人眼,遗憾的是一夜风起便满地残红。诧异间问花工,得知其名——三角梅。我心中梅花的形象瞬间被颠覆。一直以来,我心中的梅花无论是春梅、腊梅还是含笑梅,都淡雅、洁净,脱俗清高。可这三角梅在我眼里却少了几分傲气,多了几分媚俗。风贪恋三角梅的妩媚,总想挟之私奔,却转眼就无情地把离开枝头、不再生机勃勃的花瓣抛弃一地;三角梅迷恋风的甜言蜜语,不顾自己立足的土地,轻佻随风而去,殊不知等来的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也没有留下香味的宿命。我是爱花之人,偏偏对许多人钟情的三角梅不屑一顾,是不喜欢她那份轻佻,还是不喜欢她那份媚俗,也许二者兼有。
梅意,茶意,爱意,诗意,禅意!
时间如茶,总有由浓变淡的一天,而梅花,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都会在属于她的空间孜孜矻矻地绽放,又优优雅雅地凋零。无论怎样,有自己的一隅并且坚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