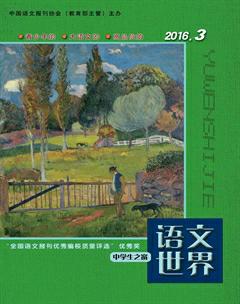唯有西风旧相识
林林
初秋,微凉。
办公桌上的卡片,有一张这样写着:“高二分班后,一切都还陌生。但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那几篇经您修改后的作文。说实话,我觉得那不就是一点暑假作业吗?我并没有认真对待,只是为了作业而作业,却不曾想,您竟如此认真,修改每篇作文还给了评语。想起自己的偷懒,不禁觉得有些羞愧……”
教师节,这个还不熟悉的学生,以检讨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师的问候,那点天真与诚恳,令我莞尔。是的,我喜欢写评语,在那些或欢喜或惆怅或振奋或消沉或敷衍各具神情的文字后面,写下短短长长的感想。
其实,与职业道德无关,我想我只是记得,年少敏感的我,曾经怎样期盼老师的评语,为一两行红墨水勾勒的文字欢呼雀跃,为一个孤单潦草的“阅”字而失落。我只是,不想错过孩子们的心情,如此而已。
谁不是从少年时光走来?
我所在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只是浙中一座朴素的小城,一道江水贯穿东西,将城市隔为南北两岸。我家就在河边。从家到学校,如果往东走,可以闻到木材厂的清香、皮革厂的焦臭;若时间有余,还可以拐到隔壁街上听听打铁师傅将烧红的铁块放入冷水中淬火时“哧”的一声;经过菜场,在地摊之间腾挪跨越,会有大叔在后面生气地喊:“细囡,不要从我的菜上走,会卖不掉的!”
有时候,我也会选择往西走,走过阀门厂的隆隆车间,拐个弯,沿着另一条小溪逆流而行。我走得很安静,因为要听水声潺潺,要听芦苇在秋风里萧索的声音。倘若不小心看见水蛇,又不小心用手指朝它点了点,一定要将手指围成圈圈放在身后,让同学往里面吐口唾沫,不然手上会长出蛇头来!
而后,便到了学校。学校依山而建,行政楼在右,教学楼在左,红砖灰瓦,盘旋而上;最高处的科学馆,也不过四层。科学馆侧面的陡坡下,有一个很大的黄泥操场,烈日下尘土飞扬,雨天里泥泞难行,却是我们热爱我们奔跑的土地。学校的围墙一例是红砖,高高低低的,翻过去,便是乡村野地。傍晚时候,我们偷溜出去,有时候会遇上被碾过的蛇尸,有时候会不小心蹲在某人的坟头上,有时候也会摘到红红的小果子吃。记忆里,暮春时节一群女生曾大把大把地摘牛爱花(栀子花),而后,在晚自习的铃响前坐回教室,一朵朵串起来并排挂在窗棂上,在月光下,随风摇曳,仿佛花开有声。
那年,我初三。
我们的英语课上,同学还是笨拙地用“古德毛宁”来记录读音;像妈妈一样的班主任钱老师,总是会揪出那些头上长虱子的男生哗哗地给他们洗头;每天六点半的电视机里,我们等待的是那个在困境中高举宝剑,大喊“赐予我力量吧”的希瑞,还有《恐龙特急克赛号》里一个又一个打不完的史前怪兽。那时候的我,穿着绿毛衣,红裤子,蓬松的童发不过耳根。妈妈说过:“考上大学之前,不可以留长发。”
没有悬念地,我考进本校高中——市一中。就像罗大佑在歌里唱的,忽然之间,就有了“高年级同学那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最先想起的,是校园五点半的天空。我“哼哧哼哧”用力蹬着那辆玫红斑驳的二十四寸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冲上水泥山坡。天空是灰紫色的,又好像泛着鱼肚白,又好像有一抹红霞,许多个清晨的记忆都糅杂在一个画面里了。但是我记得广播的旋律,克莱德曼的《绿袖子》、贝多芬的《月光曲》、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时候我不知曲名,只是这些声响混同着秋日大片流云在苍茫高空中摇漾悠游,我的心怀也慢慢舒展开来。黄泥操场上,住校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跑步,并没有老师组织。教室的灯还没有亮,但有两三烛火,已经有人啃着馒头读书了,也并不需要老师督促。
校园里自有一种如朝阳初起般的兴发之气。
一直觉得70年代出生的人很幸运,相比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有一张更安静的书桌,贫寒的子弟可以依靠自己的才智与努力考上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相比于80后90后,当时社会公平,学费低廉,贫富差距并不明显,求学之路单纯,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我们很少想过可以依靠谁。在那个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代,学校之间关于升学率的竞争并没有那么激烈。我们生活在相对宽松安宁的氛围里,有更多时间欢喜,忧伤,思考,畅想……
我并不是很用功的人,但爱看书,看得杂,不辨良莠。
家中爷爷奶奶外婆都是教书先生。外婆去世前,床头放的还是唐诗选,日读一首。记得小时,她会用毛笔写成娟秀小楷,一个一个教我认字。或许,是在这样耳濡目染之下,读书成为我最大的乐趣。只是小时读得多是《三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的野史杂谈,《红楼梦》也喜欢,小学毕业时在奶奶家阁楼里翻到繁体竖版的,也是颠三倒四囫囵吞枣地看得欢喜。
高一的时候,认识了梁羽生、金庸与古龙,认识了三毛、琼瑶与席慕蓉。我不记得第一本金庸小说是什么时候摆上爸爸书架的,但是我的确记得自己偷了他的《白发魔女传》,套上书皮,在眼保健操的时候偷偷放在座位底下看;我也不记得,班里是谁第一个开始读席慕蓉的诗,“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啊,原来句子可以这样写,心里曾这样悄悄地感叹过。
90年代初,大学里的西方文艺思潮正在渐渐退去,但却如涟漪般,一圈圈一荡荡。小城感其余绪,在细雨微风中悄然变化。
那时候新华书店里的书,依然如陈列室般摆放,售货员阿姨高傲而淡漠地坐在玻璃柜台后面,我只能用目光触摸纸质,猜想它的内容。语文课里刚刚学过《项链》,老师描述的法国文学勾起我许多向往。我的口袋里有这一个月不吃早饭积攒下的25元钱,只是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和《莫泊桑文集》之间踌躇不定。胆怯的我不敢让售货员同时摆上两套书供我翻看。当我鼓起勇气,从毫无表情的售货员手中接过《莫泊桑文集》时,内心狂喜;可是当我翻过几十页书,看过莫泊桑那浮华暗淡的世界及喋喋不休的说教之后又无比懊悔,当初我应该选择另外一套。十六岁的我也许还不懂欣赏大师的叙述,不过即使二十年时光流逝,也没有改变我对莫泊桑的观感。那套书依然在父母的书架上蒙尘,那浅紫色的素雅封面,“人民出版社”的庄严小字,曾让一个少年满怀期待,心生敬畏。
那是我记忆中,一次重大的买书事件。
再后来,老街的十字路口,寒暑假时开始有年轻人摆起了书摊。那时没有城管,年轻人席地而坐,我在那些小小的书摊周围踱步,有人告诉我这本书讲了什么,怎样生动。我还记得当我翻开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时,塞尔维特事件是怎样刺激着我的头脑,使我内心充满愤怒。少年时候的阅读,会长久影响着一个人,以至我后来几乎买齐了茨威格的著作,甚至毫无必要地一买再买。就这样,我的阅读世界慢慢扩大延伸,《基督山伯爵》《雾都孤儿》《简·爱》……也许现在看来,这些不过是一些通俗小说,但我无法形容那时候的欢喜与痴迷。而我的视力,很快地一降再降,已然接近八百度。
我也还记得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述的外国文学史,虽然这与考试根本无关。冬日微冷的空气,白炽的灯光,激情的表述,闪亮的眼神,张扬的手势……然后是雪莱、拜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只是听着这些名字,就已使我内心闪烁、觉得光彩纷纭了。还有父亲订的《收获》《九月》《世界文学》中那些篇章,都以断章碎片的形式冲击着我的头脑,却完全在我的人生知识与经验之外,超乎我的理解。
当代先锋文学或西方文学,到底与旧中国的不同,全是不同的调子。读时觉得波澜壮阔或尖锐深刻,读罢又觉得躁郁愤懑。高中岁月,似乎渐晓人世,实则懵懂未开。耳观眼听,在大人三言两语中慢慢形成自己对这个社会时代的认识,却又片面不周,于是心里常有困惑怀疑,带一点畏惧与叛逆。许多年后我开始意识到读书应从中国古典文学开始,立根在传统儒学之中,而后伸展枝叶去触摸西方或现代文学,才不至觉得茫然无所依傍,终日言不及义。但那是大学以后的事情了。
站在四十岁的秋天里,踮起脚回看过去,那天真无忧的岁月已无可追回,诗里说“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在地域的故乡之外,追怀时间的故乡,望极天涯,心情也无非如是。
和谁一起折过纸飞机,看它斜斜地飞过三楼?和谁一起在荒野的坟地里漫步?和谁一起抢着冰糖葫芦、拎着小吃穿过大街小巷?坐在谁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起看夕阳,谁的背影是我曾经惆怅的张望,崎岖山路上谁为我搭建人梯,突兀峰顶谁与我一起迎风呼啸……
想起我那个从来不去食堂买菜吃的同桌,他每星期从家里带来一搪瓷杯梅干菜,和着食堂蒸的盒饭津津有味地度日。他的数学成绩是我三辈子也无法企及的。高中时,我在所有会做数学题的理科生面前感到自卑。但他从来不曾笑话我,一次一次又一次给我讲解题目,我好像还能记得他叹口气换个姿势,一边斟酌用词、思考怎么使我开窍的那样子。
想起五音不全的我出任文娱委员时的尴尬。每周二周四晚自习前的20分钟,就成为我最发愁的时间。有一次,学校布置教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久,团委的高年级干部来检查我们班的唱歌情况。当全班一起满怀激情地唱响走调歌曲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学长错愕的表情,还有我那还没变厚的脸皮是怎样涨红的。同学们在哄笑中跟着教唱员一句一句地纠正,我的眼泪却止不住落下来。但也是在那个晚上,我收到许多安慰与鼓励的小纸条,还有同学悄悄对我说:“其实,我还是觉得你教的那调子听起来更好。”
想起班主任怎样一次一次找我谈话,在教室的走廊外,轻轻低语。总是让我放下各种课外书籍埋头于题山题海之中。她的那份诚恳与殷切,我当时少年傲气并没有领会,如今身为人师,细细想来倍觉惭愧与感激。而她在退休后依然以那样温和与谅解的姿态拥抱我。
想起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声情并茂朗诵郭沫若的《屈原》,那声音如飞湍瀑流。历史老师在讲台上大声说:“要纲举目张,要有大时间观念。”手指重重地点在黑板上,笃笃有声。地理老师告诉我们怎样在夏夜观察大小熊星座,怎样不顾怨声载道一次次要求我们画各种省会地图直到滚瓜烂熟,浪漫而又严谨。这些,都令我受益终身。
……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此刻我多想跨越时光,站在过去,但耳畔只有西风浩荡。
年少时种种,可感可叹者有,可笑可怪者有,可恨可悔者亦有,但终究,一句“思无邪”大略可以抵过。如今走在校园,桂香浓郁,看那些在晨曦黄昏间奋力读书的孩子,内心便思振作。即使我的人生是这样平淡与微小,也想要长长久久守着这方寸土地,安顿身心。这辈子,有书可以读,有学生可以教,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