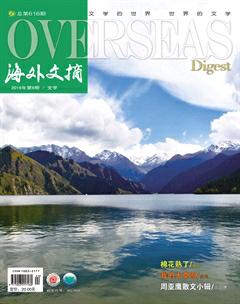杀牛柴
樊冬柏
杀牛柴是大集体时赚取工分的一样农活。
那时候,村里养了几十头牛。牛是农家的半边家屋。村子不仅为牛建了栋生活起居的牛屋,而且还安排了一名牛饲养员。农忙季节,牛们要吃过早餐才去忙农活,而一旦进入寒冬,地面没了牧草,同样要为牛喂食暖身子。所有的牛食,都是由柴火煮成的熟食,故此就派生出了杀牛柴的活计。
大人们是不杀牛柴的,大人是干田地里重活大活的。自然,杀牛柴这些轻巧活儿便落到我们小伙伴稚嫩的肩膀上。那时候,我还刚发蒙,在靠工分“分红”过日子的年代,起初,我占了1分5厘的底分。早晨、上午要上学没时间杀柴,只有等到下午放学后,我才和村里的小伙伴进山杀牛柴。杀回的牛柴,担到牛屋里,叫牛饲养员验收,然后叫他在劳动手册上记上工分。这样才算是向大人们交了差。
杀牛柴既是一件轻巧的活计,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行当。村子后面有的是山,山里有的是密密麻麻的老树,有的老树老得我们一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上有鸟窝。趁着杀牛柴,我们可以爬上树,掏鸟窝,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做这种造孽的事情。每每弄回些鸟蛋,或者幼鸟,父母都会数落我们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寻上那种叫“栗树”的树,因为这种树不结什么果子,但满是疙瘩的树身,常常流出一些清香的液质,引得“打锣蜂”、“天牛”等昆虫吮吃。我们偷偷爬上去,捉了它们,或用绳系住它们的脚,或扯根小竹签扎住它们的后颈,让它们嗡嗡地飞着。这嗡嗡的声音不啻是一曲撩人心房的天籁之音,而让它的振翅对着我们的头脸,却深感有凉凉的风的流动,这又不啻是一把天然的环保小风扇呢。
除了古树,山里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柴。对我们来说,我们杀牛柴一般喜欢杀洋粒米柴、雷公柴、桎木柴,这样的柴烧起来发出像放鞭炮样噼里啪啦的响声,且少烟,接火快,火力旺。我们还喜欢杀一种叫鸟壳的荆条柴,这种柴,虽然它们身上长满了锋利无比的刺,但我们把这种柴砍下来后,如果发现它们身上留有洞,那么循着洞洞,然后把柴劈开,在洞里可寻出一条条白白胖胖的虫儿。然后用柴火把虫儿烤了吃,特香特脆。大人们还说吃了这种虫儿,晚上睡觉不会尿床呢。
杀的虽然是牛柴,但也有见了柴不开杀戒的。我们不杀“鸭子柴”、“老虎柴”、“箭不离柴”。这些柴们,杀起来奇臭无比,烧起来更臭。我常常对着这些臭柴不可思议,同一片天地,长出了那么多的柴不臭,为什么独独它们要臭?还有一种叫“漆丰”的柴,叶子长得极像香椿,却没有香椿的香气,无论谁一碰上它,皮肤准会过敏,这种柴自然也无人敢碰。村里曾有一个小伙伴,逞英雄说他不怕这种柴,后我们提一把“漆丰”往他脸一搔一撩,结果当晚他的脸肿得像瓜瓢,害得我们暗喜好几个时辰。其他呢,凡长有毛镰把儿大的柴,我们也都不杀。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祈祷,祈祷它们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因为有树,我们就可以拥有浓荫;有树,就可以引来飞鸟与各种昆虫,也就引来了小伙伴们没完没了的快乐。
杀了牛柴后,我们担着牛柴不会立马回去,而是和小伙伴在途中寻上陡陡的山脊然后歇下来,再折几根树枝贴在屁股下,从山脊上滑下来,玩上这种叫“刷马”的游戏。一个接一个,一轮接一轮,“刷”得山脊溜溜光,“刷”得山坳灰蒙蒙,“刷”得欢声笑语阵阵起。我们不“刷马”,便分成“中国”与“美国”两大阵容,利用山脊作掩体,泥沙作子弹,玩起“打仗”游戏来。天昏地暗的,天不黑尽,我们断然不会担回牛柴的。
多年后,我与父母一起为长眠在大山里的祖母送去一点祭祀。但我路过杀牛柴的山头,让人惊愕的是已无牛柴可杀,到处是发霉、生菌的树蔸、树枝,到处是连成一片的荆条刺蓬,以及一条条没有规划的土路。山头矮了,“刷马”的山脊平坦了,密密麻麻的古树、毛柴也没有了。曾是熟悉的山头,我一下又全然陌生了。父母说,所有的青山被村里卖给树老板了,树老板除了动用挖土机在一个山头连一个山头修了一条条土路,然后拉走了一车又一车连老带少的古树,便再也没做点什么。
傻傻的,我的心头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