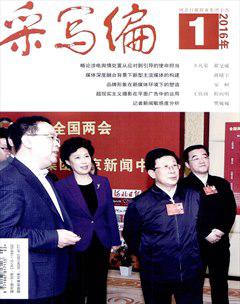味
邢雯芝 周克敏
评弹前辈陆瑞庭老人说:“味者,耐思也。”什么叫“耐思”,即经得起思考、思索,耐得住咀嚼、体味。
评弹首先要说理说清,只有立足于理,符合于情,听众们才会认可。但单单有“理”不行,干巴巴地说教,谁会买票进书场去听?这就要把“理”化在“情”中,曲径通幽,引人入胜。这种动人又撩人的“味”,会使听众欲罢不能。
由于艺术的独创性,甚至面对同一个题材,艺术家们也完全可以创作出不同的作品来。在蒋月泉存世的一系列经典弹词开篇中,《剑阁闻铃》正是一杯浓酽沁人的香茗,一盏甘醇诱人的美酒,一曲肺腑动人的绝唱,耐人寻味,余音悠长。同唱这一曲《剑阁闻铃》,与他同时代齐享盛名的苏州评弹艺术大师杨振雄的《剑阁闻铃》相比,蒋月泉没有那种华彩绮丽、响弹响唱的声势,但是,惟以摒却浪漫、只顾慕求笃实,才打造出了一曲现实主义的佳作。同一首开篇《剑阁闻铃》,蒋月泉先生和杨振雄先生的演唱风格可谓迥异。
评话《三国》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周瑜为了加害孔明,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狼牙箭,否则按违反军令处罚。岂知诸葛亮说“只需三天”,惊呆了周瑜,吓坏了鲁肃。十万支箭,不说造,就是准备齐全原材料,都得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三天怎能造好?鲁肃为朋友孔明着急,怎么这么糊涂?十天造箭时间够紧的了,好在有我帮忙,可以勉强完成。这三天是你自己提出的,我怎么在旁帮忙呢?周瑜暗自高兴:诸葛亮,这次你是死定了。我给你十天造箭,你完不成时,我羞辱你一番,也就算了。你现在自己“狠霸霸”,只需三天!好啊,军中无戏言,到那时你不用头颅来交令,看你如何下台?诸葛亮呢,大家知道的,他一向是胸有成竹的。但听众的好奇心被他这“三天造十万支狼牙箭”的“大话”吊了起来,要看他究竟怎样个造法?又怎样去曹操那儿“借”?曹操会上当么?曹操发觉上当会不会采取措施派人追赶?万一追上了又怎么办?诸葛亮呀,你太冒险了。嘿,多么有味!
我们曾在戏剧舞台上看到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谭富美等表演的《草船借箭》,感到很有味儿。但当你听了评话《三国·草船借箭》后,你就会被评弹艺人的高超说功折服,咀嚼出的味道够浓。它充分显示了诸葛亮足智多谋、料事如神的非凡才干。因为有才干而遭妒忌,又因为有才干才击败了妒忌者的计谋。诸葛亮谈笑风生,镇定自若,他充分分析和运用当时的自然条件,巧制曹兵,圆满完成了任务,可谓料事如神,胆略过人。最后连十分妒忌他的周瑜也不得不哀叹:“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不如他!”作者通过周瑜叹服的话语来反衬诸葛亮的才干,使诸葛亮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另外,评弹艺人把鲁肃的忠厚老实,周瑜的妒贤嫉能,曹操的刚愎自用,徐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在品味的过程中,也让我们感到,“味”与“理”是密不可分的。
书情不同,书味也各不相同。
喜悦的情节,给人们传递的是欢乐愉快。以长篇弹词《三笑》为例。一榜解元唐伯虎因为秋香在虎丘山上烧香及回无锡途中,无意中对他笑了三笑,误以为有情,买舟追赶,一路上叫船家唱山歌,企图以此来打动和吸引官船上的秋香出舱探望。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唐伯虎听的是如痴如醉,以至于被大船上的秋香银盆泼水也没感觉。两人讲明唱一首山歌是一两银子,以船家的蓑衣须为凭,唱一首摘一根须。当船家唱到“秋香”与人结识私情逃走时,唐伯虎高兴得把整件蓑衣抛给了船家,却无意中打翻了水碗里的“银子”(蓑衣须),碗也掉到了河里……这是唐伯虎从内心生发出的欢快,引得书场里笑声不绝。
风趣的情节,必然是让听众感到妙趣横生。许仙和白素贞在西湖一见钟情,临分别时,白娘娘赠送许仙两只元宝,每只五十两。后来发现是钱塘库银,累许仙吃官司。许仙到苏州投奔师叔王永昌大生堂店里,目的是请他保举离开徙罪衙门。王永昌与许仙交谈时,请许仙吃馄饨。但他是个刻薄鬼,做生意时经常要克扣人家,怕别人也短斤缺两,所以一面吃馄饨一面敷衍时,心里还在暗自盘算着馄饨店的老板是否揩油少给他馄饨,又不好明数,于是,把自己吃的与许仙吃的凑成数字“五”,便于计算。许仙吃三只,他吃两只……许仙一汤匙舀起五只,他为了弄清数字,只能喝点汤。许仙边吃边与王永昌攀谈,“请问叔父大人,婶母今年几岁了?”王永昌正在数馄饨呀,正巧数到十五,脱口而出“十五!”许仙惊呆了!婶娘年纪这么轻?王永昌发觉失言,马上改正“五十”。寥寥一小节,风趣幽默地拿王永昌为人刻薄小气的性格描绘得惟妙惟肖。
而哀怨的情景,带给听众的则是沉郁、凄凉的感受。《玉蜻蜓》中《贵升临终》一折就是如此。金贵升过早谢世,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他在临终前充满了凄凉哀怨。他在法华庵堂病体沉重,如果这种状况在南濠自己家中,只要请好郎中诊治,各种药材应有尽有,也许可以治好。可是在庵堂就没有办法了,缺医少药。金贵升这只“船”一日沉一日,几次通过老佛婆和三师太向当家师太提出要回南濠,当家岂肯答应。一回去,师姑不规矩必然暴露,一庵性命难保。而且当家对金贵升与三师太相好有着强烈的吃醋心理,因此拒绝得很彻底,毫无回旋余地。嘴上说“待大爷身子略爽后再回不迟”,其实潜台词就是“要死就死在此地法华庵里,要出去,休想!”金贵升仅有的一点希望破灭。他是个聪明人,言外之音怎么听不出来?无奈之下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之事,再三嘱咐智贞保牢金家一脉香烟。这一段书,听来凄惨。这就是“味”,凄凉哀怨的味。当智贞生下男宝宝,由老佛婆连夜送到南濠金家去,说书艺人来了个黑色幽默:“还好,南濠金家倒朆损失,出来一个(指金贵升),回转去倒匣是一个(徐元宰),不过长短大小是大推板勒嗨。”书场内听众禁不住发出哄堂大笑,悲哀的心情由此也轻松了一些。
评弹书中的“味”,是因人而异的。一方面是听众的感觉认同,一方面是艺人的艺术差异。同一部书,同一内容,从不同艺人的口中说出,感觉和味道大不一样。
以落回来说,艺人有各种各样的落回方法,不尽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明日请早”,而是五花八门。据前辈艺人说,《珍珠塔》中方卿二进花园,陈翠娥下楼“姐弟会”,亦名“小夫妻相会”,下胡(扶)梯十八级,说了十八回书,回回书的落回都各不相同。有些听众听得“骂娘”,但又无可奈何,第二天老时间又到了,再听。这就是评弹的魅力,评弹的“味”。
还有一种冷落回,非要艺人很有本领才能做到。在长篇弹词《文武香球》里,女扮男装的张桂英寻小官人龙官保到京城,借住“王家老店”,月台上透空气时,遇到店主的小姐王芸英,发生一段颇有趣味的摩擦:张桂英忘记了自己是假男人的身份,想着自己是女的,对方也是女的,女碰女,调调情也不妨。可王小姐却想,你是一个英俊青年,怎能与我说些出格的话?很不快,两方面一时都缄默。这时,说书艺人就来了个冷落回:“张桂英呒不闲话,芸姑娘匣呒不闲话,俚笃呒不闲话,伲(指上下手两位艺人)匣呒不闲话哉啰,那就让别人来讲闲话哉啰,下去吧。”两人下书坛,场内听众掌声不绝,为艺人高超的技艺而叹服。
总之,一方面,评弹的“味”体现在艺术欣赏中。另一方面,评弹的“味”体现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面对大千世界浩瀚的生活素材,必须进行选择、提炼、加工、改造,并且将自己强烈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等主观因素“物化”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之中。
参考文献:
1.吴宗锡.评弹文化词典 [M].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6.
2.刘大巍.论苏州评弹表演技艺的艺术传承[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3.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书坛口述历史[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