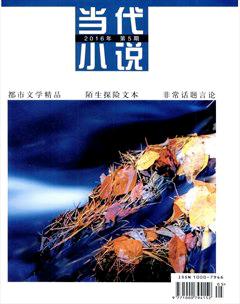夏天
玉荷
公社电影队要来放电影的消息,上午我们就知道了。还知道是打仗的,《南征北战》。
平常,村里能让人乐呵一下的事情,还真是不多啊,说起来,除了谁家嫁闺女,谁家娶媳妇,年轻人搞场篮球赛,再还就是放场电影了,都直勾勾地伸着脖子盼着。太阳才歪过晌午,我们一帮小屁孩就撅勾撅勾地跑到村北的大路,候着了。电影队来,这里是必经之地。打这儿朝东北走,穿过两个村子,一个果园,两条水渠,四棵大白杨树,是公社,毛主席的巨幅水泥塑像,挥手站在进院门不远的地方。大衣被吹开一角。塑像后是影壁墙,写着为人民服务。老大,鲜红。电影队就在公社大院最后边的那间房子里,门口一棵合欢,枝子曲曲拐拐,树下一块长条水泥桌,桌上放着盆茉莉。放电影的是刘福村和马继生。刘福村高个子,说话很和气,俩酒窝。马继生梳分头,爱唱酸不啦叽的小曲,哪个漂亮点的姑娘看电影,他都没话找话,讨好,献殷勤,跟人家瞎掰掰。他们用一头毛驴,拉着辆地排车。地排车上放着两个灰色的木箱,一个盛着放映机,一个盛着发电机。驴是头叫驴,动不动呲起牙花子,昂昂着头,啊啊地叫几声,然后噗噜噜,喷一下大黑嘴。后蹄子扒扒土,咕噜咕噜,撅起尾巴,拉几个黄不溜秋的粪蛋蛋。肚皮底下那个黑不啦叽的东西,时不时伸出来,翻翻着,东里一下,西里一下,甩搭。姑娘们一不留神看着了,赶紧别过头,慌慌着,躲了。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二存对三当当说,这头驴,老不要脸了,火家村一队那个骡驹子,就是它弄的,他们瞅一眼旁边的我,头凑近些,声小了,但还是被我听见了。他们比我大好几岁,知道得多。
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不弹了,用狗尾巴草逗蚂蚁的不逗了,头唰地冲路那头望去。
一辆地排车出现在那里。小毛驴,灰木箱。还用说吗!我们呼啦站起来,朝地排车跑去。十五六个人,高高矮矮,稀里哗啦,一会儿距离拉开。嫌鞋不跟趟的,扒下来,提溜着;怕裤衩朝下溜的,攥着松紧带。前边的,大都十二三岁,也有稍大点的;中间的,七八岁;后边光屁股的,五六岁。哎哟,谁的脚扎蒺藜了,叫一声,蹲下拔出来。噗通,前面倒一个,鲜柳枝编的帽圈甩出老远,捡上爬起来。大汗淋漓地迎上地排车,呼哧呼哧地跟在后面,拥在四周。这个摸下地排车,那个摸下灰箱子。马继生坐箱子上,刘福村坐左车辕上,很风光的样子。挥下手里的鞭子,不真抽,驾!驴蹄子细碎着倒腾,踢踢踏踏。车轮嚓嚓转动。
进村,大队保管早提着把带眼的绿铁皮暖壶,拿俩白茶杯子站在村街上。公社来检查,拖拉机来耕地,公安来破偷盗案,都这么接待。
来啦,保管问。
啊!刘福村、马继生从车上下来。
听说《南征北战》?
还有《阿夏河的秘密》。
好!两个多月没看了,都快忘电影是个啥鸡巴样了。这回可过过瘾了。
一递一句,地排车咯咚咯咚中,领着上了麦场。一群小屁孩又从一条条胡同里加入进来,浩浩荡荡。麦场上已无黄灿灿的麦子,俩月前垛的麦穰垛还在,七七八八的,耸在周围,再就七个碌碡,两张破犁,三根抽水机铁管子。村里放电影都在麦场上,这里宽敞。最早曾在村小学校,有一回放《卖花姑娘》,朝鲜的,人乌乌洋洋,来了十里八村的一大片,还没开演,呼腾,土院墙倒了,差点闹出人命,后来就改了。春节唱戏也在这,喊亲戚的,叫朋友的,田间小道上涌了来。《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汽灯呼呼照着。花被面做的幕布哗哗拉开,呛呛呛呛,开始了。有些台词小屁孩们都能背。有时台上一紧张,忘了,还在下边给提醒。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啦?
防……防……
防冷涂的蜡,防冷涂的蜡啊。手放在嘴前,圈成小喇叭。
保管打开麦场上的一间门,帮着卸下驴,一缠一绕,翻手一系,拴在门口的杨树上,让着刘福村、马继生。进屋,迎面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很慈祥,下巴上有个痦子。母亲说,那是吃嘴痦,有福。左侧墙上挂着副牛套;右侧墙上竖写着几个人名,白粉笔的,下边画着一些正字,有多有少。靠里边右墙角那一张床,吱吱嘎嘎,对面一把竹联椅,椅子下,放着一串秤砣,散落着些尿素——能闻出来,跟别的化肥不一样,呛鼻子。窗户那对着两张桌子,放着马提灯、墨水瓶,缺几个珠子的算盘。刘福村、马继生接过保管递过来的烟卷,点上,嘶地抽一口。保管倒上两杯水,放桌子上,我去买点菜,叫人做饭,出去了。
刘福村、马继生坐了阵子,出去忙活。
发电机搬出来,抬到后边的马厩那里,柿子树底下安好,电线一拐一拐,拉到麦场中央,固定好保管室里搬来的一张桌子,架上放映机,刨坑埋上两根柱子,电影幕拉上去,拴上喇叭。麦场,一下就很像个放电影的样子了。
这当儿,屁孩们有的围着刘福村、马继生,看鼓捣放映机,刨坑埋柱子,甩绳子扯幕布,倒腾片子,更多的,在放映机前的空地上,忙着占地方,粉笔划,找来砖头圈,扛来板凳摆。爹的,娘的,姐的,姑的,姨的。一个个不规整的方框,高高矮矮的凳子,还有滚来的碌碡,西边废弃短墙上掀来的土坯。来了些妮子,扎着羊角辫,穿着花衣服,这里那里,玩沙包,比玻璃糖纸,跳绳,互相撑着一根线,翻棉条,你指头一撑,翻过来,我指头一撑,翻过去,长条形,菱形、三角形……变幻莫测。麦场上闹哄哄,狗儿、麦香、四蛋、腊月、小芹地叫。二存和三当当为占地方,动手了,也不言语,脱下背心,甩到地上,手心里吐口唾沫,啪!呼地掐在一起,你两只胳膊撑着我肩膀,我两只胳膊撑着你肩膀,头几乎顶着,跐溜跐溜进进,跐溜跐溜退退,调过来,转过去,吭吭哧哧,脸通红,都想摔倒对方,可都摔不倒。二存的妹妹拉二存,哥,哥。三当当的弟弟拉三当当,撕三当当的手,二人松开了,哼!哼!你瞪瞪我,我瞪瞪你,走了。看的,也散了,回到一个个凳子前,方框内。
我们没心思占地方,我们的心思在保管室旁边的草棚子。我们都是四五岁五六岁的小屁孩。那里在给放电影的做饭。保管,大队书记的老婆,大队会计的老婆。逢到这样的事,基本就这几个人,可以趁机吃一顿,解解馋,剩下的,又可以剔着牙,揣怀里,塞裤腰中,悄没声地带回家。别人一般捞不着。偶尔也有林子他娘。林子他爹后山上修大寨田,塌土砸伤了,炕上吃,炕上拉,家里就指望林子他娘,林子他娘就出出进进,风风火火,成为娘儿们中数得着的人物。不过,也不全为这,有回我在槐树底下玩,听几个大人悄悄嘀咕,书记吃林子他娘的大妈妈,林子他娘在南边的废机井屋子里,让书记骑马。
草棚子里香气扑鼻,油香、菜香、葱花香,混成一片。钢精锅里嘎啦啦翻着浪花,酱色的猪蹄,浪花中时隐时现。保管从保管室里出来,左耳朵上夹根烟卷,拿筷子叉起个,嘘嘘,咬一口,嗯,差不多了,行了,端下来吧。大队会计老婆把钢精锅端进了屋里,保管刷刷炒菜锅,放到煮猪蹄的火上,倒进豆油,搅搅花瓷盆里的面糊,撒进一块块切成条的鱼,挑一挑,挂上均匀的面糊,看油差不多了,夹一块,放进锅里,刺啦——咕嘟嘟,锅里滚起来。炸鱼一下把其他香气盖住了,从草棚子里纷纷扬扬钻出来,冲老远里跑。
我们七八个屁孩,光着腚的,穿着裤衩的,光着脚的,嘴角含着食指,流着口水,高高矮矮,挺着肚皮,站在草棚子口,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油锅,炸鱼一条一条,黄鲜鲜,油亮亮,不停滚动,寻思,这条该熟了,那条也差不多了。保管夹进些后,不夹了,一条一条,不停翻动。火小点,保管说,旺了容易煳。大队书记老婆抽出两块板子,插进下边的灰中,冒烟,保管眯眯着眼,歪歪着头。不多会儿,夹出一块看看,差不多了,端过一个盘子,一块一块,夹进盘子里,再朝锅里夹,咕嘟咕嘟。大队会计老婆端着切好的黄瓜过来,对堵在门口的我们说,不占地方,在这干嘛,咹?快去占地方,要不好地方都叫别人占了,电影就看不到了!我们朝后退退,她一进棚子,又围回来。
咔咔,两声咳嗽。嗯——噗啊!一口痰。甭看,是大队书记。
保管赶紧把炸鱼的花瓷盆递给会计老婆,从草棚子出来,书记。
咋样了?
差不多了。
在学校那就闻着炸鱼味了。
书记有口福啊。
保管这就进草棚子,端出刚炸出来的那半盘炸鱼,再去捞上两个猪蹄,递给书记,你尝尝,看咸淡。
书记蹲在保管室门口,出啦出啦地吃,吧唧吧唧地啃,也不用筷子,直接抓,满手的油。一会儿猪蹄,一会儿炸鱼。碎骨头、鱼刺,吐在两个膝盖间的空地上,舌头一拱,出来了,边吃边说,行,还行!
书记说行,那就行。
买酒没?
买了,买了。保管麻溜从床底下摸出瓶酒,你看。
书记接过来,转了转瓶子,醉八仙。
保管说,五瓶。
够了。
你看劲道咋样?
书记抹抹瓶盖,咔呗,咬开,呗儿吣儿喝了两口,嘴一张,哈!吧嗒吧嗒,啊——够劲!把盖摁瓶子上,交给保管,放好,演完好好喝喝,上回演《闪闪的红星》,马继生小子开头不喝,差不多了,来劲了,跟我平端,喝了个农家节气大满贯,二十四盅,直接把我整趴下了,睡了一天都。这回完了,得拾掇拾掇他。
他能比得过你吗,要不耍赖?
主要他开头没喝,要不我还能喝多?
就是。
麻溜哈!
嗳,嗳嗳!
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嗯。
不能慢待了,要不,好片子来不了咱张家营子,尽拿别村不爱看的来糊弄。手一倒背,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音调拐拐拉拉。
保管看书记走了,扭回身子,咬开酒瓶子,我馋虫子也上来了,也整口,仰脖一竖,抹抹嘴,哈!会计老婆说,不是煤油吧?保管说,哪壶不开提哪壶,还老煤油吗?有回民兵连长的闺女生孩子送米,保管在柳村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到村办公室里,会计刚打了瓶煤油,一个新酒瓶子里,桌上放着,保管以为是酒,磕开盖,咕嘟咕嘟两口,可进肚子了才知道,是煤油,吐了个稀里哗啦,恶心好几天都,一遍遍清水漱口,成了村里的笑话。后来,不知谁一加工,竟成了一个歇后语,谁要找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又没在,别人问咋样?就会回说,保管喝的那酒——没有(煤油),很响,四邻八庄都知道。
会计的老婆夹块鱼,给书记老婆,自己也拿一块。
保管走过来,扒拉扒拉我们,别挡这里,去,去去。我们朝一边闪了闪。
油锅里咕嘟咕嘟,旁边摞起的土坯上,已炸了满满两盘子。
三五只芦花鸡围过来,东一下,西一下,刨腾。一头猪吸吸着鼻子,哼楞哼楞,一下一下,冲这里拱。几只花猫,塌身猫腰,蹑手蹑脚,过来,过去。
几个胆大点的屁孩,直接进了棚子口,可又怕高,目标明显,被扒拉出来,就蹲在地上,两手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他们哧地吸溜下口水,哧地吸溜下口水。外面的,有一个一下一下,慢慢蹭悠到保管室门旁,趁人不注意,一根一根,捡起书记吐在地上的鱼刺,背到身后,站起来,装作若无其事,走了,离开刚两步,就把一根鱼刺放进嘴里,吱儿吱儿地漱啦。有一个一看鱼刺没了,噌地过去,捡起书记吐在地上的碎骨头,走了。我们再看地上,啥也没了,一下子后悔了,咋不早捡呢?其实我已瞅了好多遍了,也想去捡来着,可没好意思。回头看那俩小孩,羡慕,嫉妒。有一个大些的屁孩,跑过去截住捡鱼刺的,伸出手,捡鱼刺的给他一根,看他还不收手,又给了一根。我也想去要一根,可他比我大,估计要不来,讨没趣,只好作罢。寻思,要是书记再来吃,我一定去捡,可书记一直没来,在放映机那,粗门大嗓。
去去去,保管又轰我们,一盘盘朝桌子上端菜。保管室里的那张桌子,已抬到中间,四周高高矮矮的凳子。
趁会计老婆不注意,保管在她腚上摸了一把,会计老婆一扭身子,盘子还占不住你的手,摸你老婆那的。保管嘿嘿一笑,她那哪有你这好啊,早摸够了都。二存春上说过,保管很流氓。马厩西边的草料棚里,晚上有很多麻雀。上年冬里有回晚饭后,他和三当当他们去照。三当当那时自制了个手电筒,旧电池后腚上,用锥子钻了些眼,放进盐,很亮。他们从草料棚的破窗户爬进去,听到草料顶上唰啦一响,吓了一慌,以为是鬼,赶紧把手电筒唰照过去,是光着腚的保管,抱着也光着腚的麦香的姐,慌张地趴在草料上。二存他们呼啦爬出来,嗖嗖跑了。以后,再看见麦香她姐,他们就在背后吐唾沫,挤眉弄眼。看见保管,就在后边把手握成枪,偷偷瞄着放,巴勾,巴勾,说枪毙不要脸的大流氓。
啪叽,土坯上炸好的鱼盘子里,一只芦花鸡啄了一块,我们反应过来时,芦花鸡已钻过草棚子上的一个破洞,跑了,我们赶紧苕苕地边喊边追,可芦花鸡却没有放弃的意思——偷块鱼不容易,拼上力气逃,我们就紧跟着撵,围着麦穰垛转了一圈,到了水渠上,朝东跑了一阵子,又折回来,以为要过水渠,却没有,打水渠上冲下来,到了西边的破土墙,北跑了十几米,过土墙,进了玉米地,沿着玉米沟左拐右拐,到张家坟地那儿,拐个弯,又窜回来。我们伸着两只胳膊,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朝那边,哈哈喘气。到底芦花鸡受不了了,见实在逃不掉,不朝前跑了,脖子一缩,闪过追在前面的,往后走回来,到我跟前,把鱼一丢,溜溜着,夹悠夹悠走了,我一下捡起鱼,吹吹上面的草屑,在其他屁孩的簇拥中,回来,两手捧举,对端菜的保管说,追回来了,给。保管看了看我,你要吧。我以为没听清,眨眨眼,望着保管,保管说,鸡啄了,给你了,抚顺。我眼睛一亮,啊?真的吗?赶紧攥在手里,跑了。似乎晚了保管会反悔,再要过去,捞不着了一样。
兴冲冲地进家,母亲正顶着毛蓝头巾,呱嗒呱嗒做饭,一看,哪来的炸鱼?
大队保管给的。麦场上不是在给放电影的做饭吗?
那咋会给你呢?
一只鸡不是啄了吗,没看好,我追上,捡着了,保管就说不要了,给我了。不信你去问问。
噢,是这样。
嗯。
那先放橱子里,等你哥你姐他们回来再吃,让他们也尝尝。
嗯。
去啊!
我闻闻香。
过了会儿,母亲问,闻完了吗?
闻完了,就放。我到上房,拉开橱子,把鱼小心地放进一个空盘子里,舔舔手,回到灶房,伸过去,让母亲也闻,母亲说,我是大人,又不是小孩子。你闻闻嘛,可香了。母亲就俯近我的手,吸吸鼻子,嗯,还真是很香(口来)!啥鱼?
我姨家大姐结婚时,我们在酒席上吃的那种。
吃的哪种?
啊!你忘了就挨着粉皮蘑菇汤、芹菜炒猪耳朵,这边是炖豆腐、芫荽、土豆丝,你还让我慢点吃,怕我卡着。我一下吃了三块。手上全是油。
噢,鲅鱼!母亲说,咕噜噜咽了口唾沫。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