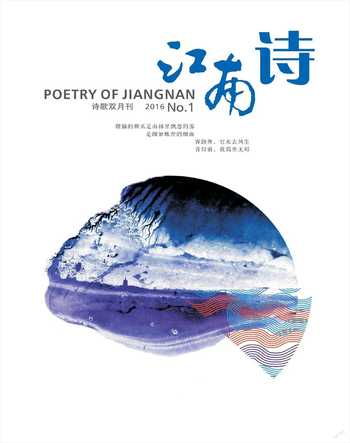深情而执着的歌者
人邻 高平
主持人语:
诗人的想象不仅不排斥实实在在的生活积累,而且想象力丰富的诗歌都是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底蕴。我十分欣赏生活在祖国西部甘肃的诗人高平的纯粹性,他像许多杰出的前辈诗人一样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他的诗歌的品质是饱满的,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保留了他们那一代诗人所处的时代的真实声音。(雨田)
人 邻:学者张明廉在《高平小传》里写道:“在乡间小学上学时,高平已开始接触民间的歌谣和说唱,他每每为民谣那明快、朴实、生动的语言,丰富、优美、跳荡的想象和民间艺人们说唱的那些长长的绘形绘声的有韵故事所倾倒”。您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些民谣还有那些说唱么?
高 平:在我幼小心灵中埋下的诗歌种子,和故乡的农村一起,我是不会忘记的。那些歌谣在今天的城市中大概很难听到。比如极具童趣的“光明奶奶,爱吃韭菜,韭菜不烂,爱吃鸡蛋。”关于游戏的“蜻蜓蜻蜓来,我给你绣个大花鞋。”同情妇女的“多年的大道踩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记忆时令的“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反映抗日战争中流离生活的“左手拿着个瓢啊,右手把婴儿抱,举家逃难就把那饭来要。”等等,都使我开始领会到了汉语言中美的因素。在我听过的那些说唱中,我记忆最深的是《薛仁贵征东》,它在叙事处就说,抒情处就唱,对我启发很大。
人 邻:也许您的作品受到那些民谣或者是说唱在音乐上的影响,也许还有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经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剧社戏剧队演过戏剧,我注意到您的诗歌大多都适宜于朗诵,您觉得是这样么?诗歌的音乐感对你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什么?
高 平:我在战斗剧社戏剧队的时间极短就转入了文学队,所以没演过戏。我倒是在别处客串过话剧和京剧。我的诗大多适合朗诵是因为写得比较明朗,接近口语。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诗都是可以用来朗诵的,因为诗人为了高雅,难免使用一些书面语言,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字,是难以知其义、品其味的。另外,有些谐音字词,如果只听不看,也容易产生歧义和理解错误。同时,诗人为了精炼,难免省略一些主语、副词、连接词,语句之间跳荡的空隙较大,听起来要比读起来吃力得多。所以朗诵诗应当是诗的特殊类型之一,即专门用来朗诵的诗,它属于时间的艺术,在语言的逻辑和词汇的选择上要关照人们的听觉。不论什么诗都是语言的艺术,读起来都应当具有语言的音乐感,所以我对自己的诗总是一边造句一边默念,觉得哪个字磕磕绊绊就坚决删掉重来。
人 邻:1950年初,您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天下穷人一条心》在刚刚解放的成都出版的《川西日报》连载。那时您才18岁,您现在对自己这首长篇叙事诗还有印象么?您的父亲高恩传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母亲李孝娴出生在清末秀才之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即便时局动荡,也应该大致是衣食无忧,年轻的您如何在这首诗中理解、切入“穷人”的心理,并将这样的叙事上升为诗?
高 平:这首长诗我至今还保留有剪报。我家虽然衣食无忧,但村里的穷人生活我是熟知的,我童年的小伙伴中就有几个穷人家的孩子。这首诗是不成熟的,并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且含有不少图解政治概念的成分。所以我没有将它收入过任何一本诗集。
人 邻:因为诸多原因,您在建国之初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多少书可读的。您能谈谈,您在那个时候有什么可读的书吗?尤其是诗集?那些书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高 平:上世纪五十年代可读的书并不少,可以说是我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最多的时期,抓紧一切时间地、废寝忘餐地读,甚至经常夜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诗歌方面,除了我国诗人的作品以外,翻译出版的外国诗集也相当多,我读过的有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舍甫琴科、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雪莱、拜伦、雨果、阿拉贡、洛尔迦、惠特曼、聂鲁达、瓦普察洛夫、泰戈尔、赵基天、素友等。他们对我的影响总起来说就是切入生活,爱憎分明,视野开阔,形式多样。
人 邻:1951年,您作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创作室的创作员进藏,生活是艰苦的,环境是陌生而新鲜的。但是,您在那一阶段的诗歌却是充满了生活的活力。您能简单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么?
高 平:我第一次进藏的半年经历,无疑是我生命中新生活的开始。我写了一本书叫《步行入藏记实》,已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我领略了横断山脉的壮美,展现了濒临死亡的豪迈,我爱上了藏族人民善良淳朴的性格,汲取了进藏部队坚韧无私的精神营养。它厚重了我的爱心,强化了我的豁达,使我的作品永远同灰色与晦涩绝缘。
人 邻:短暂的进藏生活结束后,您正式对组织提出了去西藏工作的要求?是因为西藏的地理地貌、文化风俗和热情的人们给您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您在西藏的生活对您长达六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几乎是起到了决定性、根源性的影响。
高 平:如上所述,我愿意去西藏工作,只是因为我爱上了西藏的山川和那里的军民。如果说还有其他原因的话,就是我认为要想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必须不怕艰苦,自讨辛劳,到无人开采的“矿”区去,而不能拥挤在舒舒服服的地方。而西藏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正合我意。这样做,与临时去完成写一点什么的任务大不相同。您说的很准确,几十年来,我对西藏的爱在延续,西藏对我的影响在延续,它是我永不断流的创作源泉之一。
人 邻:您二次进藏之后,写作了大量的抒情短诗。有评论说:“尽管其中某些篇章还显得粗糙,艺术上的提炼和概括不足,但写得真挚、热情、朴实。”我们知道,现在的许多诗人,抒情短诗语言上很是讲究,但是诗歌里面缺乏的却正是真挚、热情和朴实。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高 平:我们那时相对缺乏诗的艺术素养,但不缺乏真诚和激情。您所指出的现在诗歌里缺乏的东西,正是找准了诗歌界的软肋。一无激情二不真诚的诗,不论想象力多么丰富,语言多么精致、俏皮,词汇的积木搭得多么怪险,都是一道流星,留不下恒定的光芒。
人 邻:1957年,您在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抒情短诗集《拉萨的黎明》,在艺术上有了进一步的成长。其中的抒情短诗《致田野》、《写在花圈上》(后一首尚未收入,请删去,可加个等字),在语言的提炼和意境的概括上,已经显示出诗人自己的艺术个性。但是,似乎真正引起诗坛瞩目的是您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收入诗集《大雪纷飞》里面的三首叙事诗。洪子诚先生在评论中指出:“(《大雪纷飞》)它表现了高平对他所表现的生活所达到的认识的深度,也较突出地反映了他艺术个性的某些重要特征”,认为“五十年代初涌现的青年诗人,他们踏上诗坛时,引人注目的主要不是他们艺术上的成熟,他们的长处,在于对新的生活的敏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大雪纷飞》这首长诗的创作过程吗?也许,您能否自我重新在2015年这个时间点上客观地回顾评价一下这首诗对您创作的意义。
高 平:在西藏,我心中总有一种强烈的痛楚无法排除,那就是我所目睹的西藏农奴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的生活。他们世世代代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应各种差役,流尽了血汗,却换不来人身的自由。积压在我心底的愤慨,炽热地熰着浓烟。1957年元旦刚过,我偶而听到了一首流传在羊卓雍湖畔的民歌,是诉说农奴的苦难的,特别凄凉婉转。其中有一句:“我是人家的仆人,不能随自己呀!”它像是从农奴的心尖上滴下的血,一下子点燃了我心中对奴隶制的怒火。我很快构思出了一首长诗,写一个支差远行的藏族姑娘的路途艰辛、美好向往和最后毁灭。我的笔紧随着女主人公央瑾的行程往前走,边走,边诉说着心里话。最后,在冰天雪地中,她死了。我含着热泪在稿纸上重重地划了个惊叹号,“啊,大雪纷飞!”诗也就写完了。长诗《大雪纷飞》的出版奠定了我在中国诗坛的地位,被认为是百年新诗中的经典。它揭示的是野蛮的社会制度对人的自由的剥夺,恶对美的摧残;深层的含义则是制度的变化固然不易,而精神枷锁的解脱更难。这是它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我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标志着我从执着理想的美好转向正视现实的严酷,从单纯地赞美新生活转向关注人类的命运,从单纯地歌颂英雄业绩转向挖掘人性的复杂。
人 邻:1958年6月,您被打成右派,是因为诗歌创作还是因为某些言论?另外,我注意到张明廉在《高平小传》里写道您的父亲曾经苦劝过您“不要做文人”。您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曾经想起过父亲的这句话吗?还有,我看过许多右派的回忆录,他们对右派下放劳动有许多描写,有顺从的,颓丧的,也有对抗的,您对那种压迫是采用何种态度呢?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说的事情吗?
高 平:我被打成右派,与创作无关,因为我没有一篇被认为是毒草的作品;也与言论无关,因为我没有参加大鸣大放,没有在什么会上发言。我的“罪行”来自我的日常闲谈以及“向党交心”的检查,材料的拼写采用了当时普遍惯用的手法,可谓集捕风捉影、断章取义、颠倒黑白、张冠李戴、捏造陷害、无限上纲之大成。父亲当年告诫我的关于文字狱的话不幸言中,那时他已病逝,我已无言以告。我被“撤销一切职务,取消一切待遇,送农场监督劳动”以后,是顺从的,也是乐观的,有位领导告诉我说“劳动个一年半载,摘了帽子,还跟原来一样。”因为划定和处理“右派分子”是个新发明,谁也不清楚以后怎样。我在农场劳动的两年半中,那里的农工、下放干部和场领导,都不把我当敌人看待,对我的同情、友善、爱护、照顾令我感激难忘。至于后来挨饿、浮肿,那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人 邻:1958年6月您被打成右派,到1959年12月您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快就“解放”了您?
高 平:劳动表现好,不怕苦和累。放冬水就下到带冰的水里,扛麻包能扛200斤,割麦子还得过四分钱的奖金。
人 邻:您1961年调入甘肃省歌剧团工作,是您的选择?还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您后来的诗歌创作是否受到您在歌剧团写歌剧剧本音乐感需要的影响?您早期的诗歌曾经受到过民谣、说唱的音乐影响,加之歌剧剧本的撰写,是否决定了您的诗歌比其他诗人的创作在语言上更多地受到音乐的影响?现代诗人在很多时候是不大注意诗歌的音乐性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 平:1961年初,为了解决饿死人的问题,中共西北局开会决定“抢救人命”,把我们用闷罐火车运回到兰州。重新分配工作时,去歌剧团做编剧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爱诗,也爱歌,歌剧的唱词也必须是能唱的诗。现代的诗人之所以不大注意音乐性,我想,一面是受汉语古典诗词和民歌民谣的熏陶不够,另一面又受翻译体的影响较深,丢弃了方块字独有的节奏感,也丢弃了语言的音乐性,大大降低了诗美,令人惋惜。
人 邻:1978年以后,您虽然不断有抒情短诗面世,但长诗似乎依旧是您从不愿意舍弃的创作形式。那之后您出版了长诗集《川藏公路之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78年)、《古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2年,您又出版了长诗《帅星初生》(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国除了一些少数民族有史诗,汉族没有长篇叙事诗的传统,诗人更为看重的是抒情诗,而你却为何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创作长篇叙事诗?是因为反观到抒情有其“狭隘”之处,还是您遇到的那些题材的“倒逼”?抑或是当时政治任务的需要?
高 平:写诗写惯了,什么题材都想用诗表现,同时也不无写作史诗的奢望。后来,我停止了长篇叙事诗的创作,甚至放弃了《西藏三部曲》的续成。因为我发现诗的读者本来不多,而用诗叙事远远逊色于小说,如果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故事曲折,用诗来写无疑是扬短避长,自讨苦吃,费力不讨好。什么题材适合用什么体裁来表现,是应当慎重选择的。在文学史上,同样的题材失败于这种体裁而成功于那种体裁的例证很多。
人 邻:也许,我们还可以专门谈谈你的叙事长诗《古堡》。林家英教授指出您这首长诗“在锤炼语言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藏族民歌风格、韵味”。林家英在评论中还特别谈及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益喜拉姆的《祈祷歌》。另外,我们知道您在《大雪纷飞》(请改为《紫丁香》)中,藏布和巴珍的对唱中的想象方式都带有藏族民间传说和藏族民歌意象的运用的浓重痕迹,带有藏族民歌常用的比喻方式和叙述方式。您能谈谈藏族民歌风格、韵味的这种吸收对您长诗创作的影响吗?我不知道您懂不懂藏语,但是我想即便是不懂,长时期的接触,那种风习、语调、气息的吸收,也一定在你的诗歌里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 平:我只会一点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藏语,我吸收藏族诗歌的营养主要还是依靠汉语文的翻译。它们简短精炼,语言明快,比喻贴切,形象平实,表现形式也不复杂。和我原有的诗歌主张基本合拍,会被我借鉴、融会、孵化到某首诗中,它像是藏族民歌,但在藏族民歌中你找不到它。
人 邻:似乎1984年之后,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您又着重于抒情诗的写作,连续出版了多部抒情短诗集。这些抒情诗的创作,对你中晚期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什么?相较于您早期的抒情诗创作,您自己认为这些诗歌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高 平: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文革”浩劫的结束,冤假错案的平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施,又开始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我作为被文学史家称为“归来者”中的一员,也进入了创作的第二青春期。我在发表于《诗刊》的题为《心迹》的诗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冬天对不起我,我要对得起春天。”诗歌评论家吕进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说它“写出的也许是归来者的共同心迹。”在这之后,我将许多不适合写诗而又想写的题材搬进了电脑,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当然还有不少抒情诗。这些作品与以往相比,最大的变化一是自觉摆脱人云亦云的旧式牢笼。二是努力向审美回归。
人 邻:我知道您也是写了大量的诗论的。您的诗论的核心,也许您可以为我们简略介绍一下。或者说,在您的诗论里,已经表述了您的诗歌创作的美学倾向。
高 平:在诗歌领域,古今中外对两个问题见解纷繁,各种答案难以数计,即诗是什么和什么是好诗?我对前者的界定是:诗是诗人对于高层次的事物通过高档语言所作的高度个性化的展示。我对后者的界定更简单,六个字:揪心情,惊人语。我的作品都是我的见解的体现。
人 邻:您的抒情诗歌创作,常文昌先生在他的《一代诗人的足迹——高平抒情诗的哲理性》里指出,也“经历了一个由单纯天真到复杂深沉的变化过程”。诗歌的哲理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巧妙地将之浸入诗歌,得其深沉的力量,而又不显踪露迹。抑或,干脆也有些诗人直接就排斥诗歌的哲理性。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高 平:不必有哲理诗的提法,也不可刻意去创作哲理诗,但是要肯定诗中的哲理性,绝对不能排斥。好的诗,耐人寻味的诗都是含有哲理性的,它是由诗人的丰富经历与深沉思考搅拌生成的必然产物,会增加诗的思想厚度,增强诗的可读性,增添诗的经典性。诗的哲理性和所谓的哲理诗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人 邻:您还曾出版过一本《了然斋诗词选》,能介绍一下您的旧体诗词创作情况吗?也请介绍一下这本诗词集的创作对您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新诗史以来许多诗人在延续了一段的新诗创作之后,又转向了旧体诗词的创作,这意味着无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新诗对于古诗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承继,还是无奈的现代性的断代?
高 平:《了然斋诗词选》是个仅有几十页的子小册子,选收的是我1996年以前的旧体诗作。自那以后,我的旧体诗的产量大有逐年递增之势,我也可以算作是两栖诗人了。所以,我在最近出版的列为“陇原当代诗歌典藏·诗歌卷”的诗集《赶在冬季之前》中,特意选入了48首旧体诗词。我写旧体诗既是出于一贯的爱好,也是要表明作为中国诗人不应忘本,对于古典诗词要不断地学习和继承。旧体诗在当代,功能并未消失。中国诗歌的大鹏鸟应当用自由的新诗与格律的旧体两扇翅膀飞翔。
人 邻:您还曾经创作了有关仓央嘉措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引起您的兴趣?他的诗歌,他的传说?也许还可以这么说,有关仓央嘉措的小说是您对西藏生活的继续的更为深入的关注?是您的无法割舍的西藏情结?
高 平:是的,小说《仓央嘉措》的确渗透着我“对西藏生活的继续的更为深入的关注”和“无法割舍的西藏情结”。进藏初期,我就接触到了仓央嘉措的诗歌,感觉感情真挚,富有人性。我开始在各种历史记载当中寻找这个人的踪迹,积累有关他的材料达30年之久。逐步加深了对他的理解、同情与敬爱。我写《仓央嘉措》,是为了替这位伟大的藏族诗人立传,也是为了通过惋惜天才的毁灭,昭示人间的善恶。值得欣慰的是,我成功地了却多年的心愿。
人 邻:我注意到,您还出版过一本《易经诗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本《易经诗解》是您哲理诗的一种具有较大外延的探索?是您八十几年人生的自我观照?
高 平:我只是对《易经》系辞原文的含意作了诗体的表述,目的是破除千百年来人们对于《易经》内容的误解。它具有哲学、社会学的价值,而不是算卦的工具,更不是供人妄测什么具体事物的巫书。它显示的是大自然和的人世间的关系与规律,对于正确认识与对待人生是有帮助的。
人 邻:对您来说,成名甚早;而且在成名之后,一往直前地写下去,延续了六十多年之久。这在诗坛是很少见的。对您的创作,学术界、文学界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仅仅是近些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新诗发展史》、《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史》、《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史》,甚至像(美)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的史学巨著也注意到:“50年代早期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开发西部疆域中一大批年轻诗人从云南和西藏高原,从新疆和内蒙的草原和沙漠中涌现出来……高平(1932——)有一首关于一个藏族女孩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对话简洁,俨然是田间10年前写的叙事诗《赶车人传》的风格。”对某些人来说,这些成绩是求之不得的,对您来说也算是功成名就。但是,我看到的是——您还在一直写下去。您这么多年的创作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高 平:写作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已经无关名利了。它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我不敢美化自己具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我只是执着地认为,只要活着总得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我能够做得来、比较善于做的只有文学创作。
人 邻:谢谢您接受这漫长的访谈,让我读着您早期诗集《珠穆朗玛》里《甘孜草原的夜里》这首诗来结束我们的访谈吧:
白鸟收起了翅膀,/雪山沉睡在远方;/蓝天衬着星星,/像我爱人的衣裳。//夜晚的甘孜草原,/像一块深绿的水晶。/熟睡的羊群,像草丛的白花,/围着新织的帐篷。
这首诗真是不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的,直到今天,它依旧是那么新鲜、感人。
高 平:谢谢您的慧眼与卓识,提出了这么多值得让我重新思考的问题,对我是很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