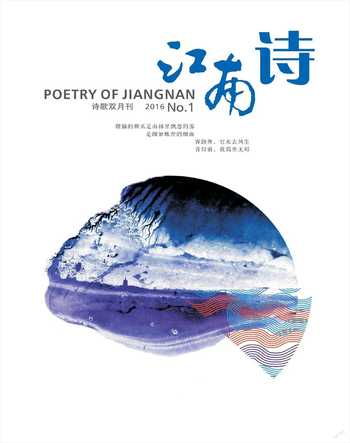首届江南诗歌论坛研讨会纪要
主题:江南风格在当代新诗中的独特性
时 间:2015年11月28日下午
地 点:浙江省仙居县皇嘉国际大酒店国际厅
主 持 人:钟求是
学术主持人:汪剑钊
钟求是:各位同仁,今天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集聚在仙居,在此参加首届江南诗歌论坛,一起探讨江南风格在当代新诗中的独特性,这非常有意义。我是写小说的,有时与诗人打交道,发现江南诗人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江南诗风在诗坛上呈现也是很明显的。江南诗风怎么归纳?是细腻?是温雅?还是有人文关怀、讲究修辞?这是一个特别的话题,希望今天讨论能对江南诗歌这一概念有个较好的定性,对江南诗风这一写作有所推动,我的感谢方式就是用耳朵来静听,下面会议交给剑钊主持。
汪剑钊:今天就江南风格在当代新诗中的确立,它的概念和写作风格,以及它对当代诗歌能起什么作用,在写作中江南诗歌在整个诗歌中的格局是什么位置这些话题进行讨论,希望各位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
耿占春:江南诗歌沉静、优雅,非常注重修辞,一般不用粗犷的语言。直观的特点是,一到江南就感觉这里的植被是这么丰富,空气中的水气充足,水墨江南,感觉的丰富性在江南。植被的丰富性在江南作品中是不是会体现出来?这种感觉要依赖于环境,江南诗歌比较讲究修辞方式,可能这些与江南的环境有关。感性的东西肯定是很容易受到空间、地域影响,视觉的、听觉的、感性的事物构成的是写作的下层,一般不构成主题;社会、历史、制度构成写作的上层问题。在一首诗歌中,下层的问题往往比上层的问题有意思,如果文学和诗歌仅仅是由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问题所构成的,那么它会很枯燥,如果没有渗入到一个地方的地理、地貌等地方性风格的感知上,这个作品是很枯燥的,缺乏不具体性和不深入的。下层世界是对微观的事物进行描写,越是到了21世纪,作家越是不厌其烦地去写各种感知,像沃尔夫的《海浪》就是这样。江南诗歌最主要的就是关注细节,构成一个非常浓郁温润的下层世界,它的底部有一个地域性的、具有江南感知的世界。地方性风格不可能构成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主题,但它是检验一个思想真实性的修辞方面的显现。
唐晓渡:关于江南诗歌,我们以前没有专门的讨论,我想到最早的好像是93、94年,钟鸣曾经倡导过南方诗歌,当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主要是从地域角度讲,对北方诗歌霸权的反抗。朦胧诗全是北方的,大家讨论话题主要是顺着朦胧诗的思路在展开,所以他当时提出来南方诗歌和北方诗歌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北方诗歌更多的是被政治、历史或者皇权意识所渗透,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地方色彩比较强烈,而南方歌更多的是生活化、虚拟化的。从语言角度,北方诗歌很多时候是普通话,修辞和句式比较标准。而南方诗歌比较多是方言,被方言所渗透。从大的来说,像占春说的把诗歌分成一个上层的、下层的,而北方的更多的是骨骼的、头脑的、政治的、历史的,这种区分其实也很有意思。在历史上比如说海派和京派的讨论,其实是一种差异,无论是南派、北派、海派、京派等各派存在着封闭性,主要还是一个地域的区别。随着媒体社会的发达,交流的无限展开,这种差异,通过交流、网络、阅读的便利和创作的借鉴等形式,随之一个地域的界限被打破。以前就个人而言有北人南相、南人北相,风格有时完全是分裂的。我认识一个写诗的,整个人长得与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很不一样,他人长得梁山好汉似的,一看就觉得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但他诗歌写得非常精细,这种很矛盾的现象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两极化,好像使一个地域概念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风格概念都会渗透到血脉里面,体现在一个人的文本当中。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风格概念,与其说是风格概念,不如说是美学维度。江南风格的独特性是在比较当中产生的,一般地域的比较是比较抽象的,这种比较,阅读也好,批评也好,都是针对文本的。所以我赞成占春所说的江南的感受性,江南诗歌的修辞特点,整个作品的质地。说到江南,我们会联想到雾雨烟霞、江南三月草长莺飞啊,都是比较细腻、温润、潮湿的,南方比较多的是沼泽、植被茂密的。但不管是哪个地域,比如被移植,会与本地的会有很大区别。像沈苇,一个江南诗人到新疆,可能会吸收西北的广阔,但是他的作品还是有江南质地的,但你不能简单说他是一个江南诗人,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域性,从更广泛的美学意义来说,他超过风格了。一个作品比较有更广泛的意义的话,他肯定是超过他的风格的,讲究更多的是诗歌的品味、质地。一般从一个风格性的学术上来表述的话,强调江南风格,可能是诗歌自身的要求,避免作品的同质化。诗歌是生命最底层、最原始的东西,是不断地在涌动、在变化,水汽朦朦的看不太清楚,但是需要你赋予它比较清晰的、精确的声音。如果说江南风格则更是对诗歌自身的感受。我认为江南诗歌应该从好几个层面上来讲,而不是说只是从一个地域上来讨论所谓江南风格。
沈 苇:我对江南的感情非常复杂,二十几年前逃离江南,现在年过半百却频频返回江南。对我来说,最喜欢读的还是江南诗歌,作品当中细腻的、优雅的、灵感的、考究的,尤其是水性的东西,从中我学到很多。西北的写作普遍比较粗糙,也有很多大而无当的东西。但在这种江南的特征中,是不是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江南诗风?约定俗成的江南诗风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方面这个从地域概念来谈的话是不存在的。江南这个词一直也在发生变化,最早是在先秦产生的,指的是湖南、湖北和江西的一部分,演变到现在大江南的范围已经很大了,浙江可能是全部,还有上海啊,包括苏南、皖南、江西、湖南、福建,甚至包括贵州一部分。大江南是吴语区和徽语区,小江南就是吴侬软语的江南水乡,太湖流域的浙北和苏南这么一个概念。同在江南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写作之间的丰富性和差异性非常大。浙江文学占了半部现代文学史,其中鲁迅和丰子恺,我很喜欢,都是浙北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写作风格包括性情相差太大了,鲁迅写作中的勇猛锋利和丰子恺身上的温暖慈悲完全是两极。还有前面晓渡说到的南人北相和北人南相问题,在座的晓明和剑钊就是南人北相,飞廉是北人南迁、北人南相。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很重要,我的家乡、出生无法选择,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的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认为人性大于其他,我的观点是诗歌写作既是地域的又是不地域的,既是江南的又是不江南的,既是风格化的又是不风格化的,就是个人的独创性和地域性与普遍性的一种结合、一种创意。
王家新:对江南我没什么发言权,我出生在湖北偏北,生活在北京,从个人的气质上来讲也是冷一些、硬一些、广阔一些。我对江南是很向往的,中华文明之精华后来集中在南方。中国人对江南也是寄予了文化乡愁,一两千年来在诗歌中呈现和创造。关于江南风格问题,有没有江南风格?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江南风格,在古代经典中主要由哪些诗人体现的,对于这一块我缺少发言权,也缺少研究。但从直观意义上来讲,江南充满水气,水气又带来灵气,这影响诗歌的风格、创作灵感等等。江南植被物产丰富,江南诗歌中有丰饶性、细腻性、感观性,还有一个修辞性。我记得布罗茨基写的《给明朝的一封信》有一句:“稻米匮乏,宣纸却源源不断”,说明了对江南文化的一种推崇。另一方面江南过于发达,也有可能形成一种颓废,对于江南我只是从直观上来发言。在坐中有晓明、飞廉、江离等我比较喜欢的几位,比较具有江南的特色,有一种喜悦之情,修正、刷新、扩展江南。泉子写的诗歌,许多是他围着西湖散步写出来的,另外他更注重一个内在的修炼,他也从他自己方式对江南和江南风格作了一个刷新。在坐的飞廉带来了北方的因素、中原大地的因素,但他肯定也是受惠于江南,带着江南的灵气,诗歌简约灵动,也富有功力。结合他们的创作来考查江南的风格在今天的时代可能性等等,如果空谈是很难来谈的。最后我觉得江南比我们想像的是更丰饶、更丰富。像河南省是中原大地,似乎比较单调;浙江比较丰富,比如宁波、温州人的方言,这种丰富性需要我们深入考察。我们需要打破这种习惯性的认知,需要亲身的体验、考察,在这些前提下来谈今天的江南性。另外,在这个时代江南也在变化。再补充一下,江南有一种古典性,文明高度发展,风格优雅,江南与古典密切相联,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东西。
何言宏:昨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论坛会议,因为今天要参加这个江南会议,我特别注意了昨天会议上的四位江南作家:苏童、余华、格非、艾伟。四个作家都是我们江南的作家,他们一方面出生在江南,在创作上体现了江南性。特别是苏童,他就说喜欢南京的颓废,甚至死亡的气息。南京有很多的坟墓。江南风格在小说界有许多体现,甚至得到了很多人喜爱。在我们诗歌上也应该被更多人所熟知,我对江南诗歌充满期待和信心。关于江南诗歌的讨论,钟鸣用北峻和南糜来概括南北诗歌的巨大差异。关于南方的诗歌,很多学者都有谈论过,古代就有上海的董其昌,在艺术界和文化界,南北的差异和对峙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很必要的。2008年我还在南京工作,当时第一次讨论的主题叫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四川的柏桦写了一篇文章。再过几年,在广东佛山也开了一个会议,他们成立了一个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但都没有进一步去深入。我们今天叫首届江南诗歌论坛,最经典的福地就是江南。另外,谈到江南的诗歌,实际上地域性的问题一旦把它本质化,就会成为一个囚笼,一个诗人就很难超越。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待,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辩证性的地方性。不管怎么说,江南是存在的,它的地域,它的文化,它所培育的人的精神气质和品味是很难改变的。江南存在着一个广大的、松散的诗歌群体,只是让诗歌界知道有江南这么一个诗歌群体。当时在考虑,江南到底以什么地方为区域呢?我觉得在明清时期,江南存在着一个可靠的概念,官方确定为八府一州地域。我认为每个地方存在着自己的一个独特风格,但也不能够局限于八府一州,因为交通发达,独特风格可以互通,可以扩大八府一州地带。大家对江南诗歌的活跃这一认知度很高,但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江南诗歌的活跃和复兴,而应该放到更广阔的背景当中。整个世界文学的地方性和本土性都在复苏,在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地方性本土性,现在都特别强调。我们可以专注于我们的认同,但我们的精神空间、文化空间应该更广,应该是一个全球的空间。刚才谈到文明、传统,江南诗歌与传统文明的对接十分明显,江南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最经典、最精彩、最灿烂辉煌精致优雅的地区。江南诗歌对古代文明的一种眷恋之情,是江南诗人、江南的作家对我们本土文明的一种把玩。这些年江南大地上到处有诗歌活动、诗歌研讨,有很多文人雅集,都有诗、有酒、有茶、有古琴,这是对文明的沉醉。
梁晓明:江南风格到底存不存在?江南风格如果存在,到底该怎样去界定?首先有一点需要确定的就是晓渡提出来江南首先不应该是一个地域概念,如果是地域概念是很荒唐的。去年我去了一趟金华,金华有一座楼叫八咏楼,李清照曾写过一首诗《题八咏楼》。李清照算不算江南的?因为李清照她虽然是个女的,但是她的文章有一种尖锐性、攻击性和战斗性。就像刚才讲到的扬州一样,一讲扬州就肯定是江南,那么李清照诗歌到底算不算江南风格?这个怎么来论,确实是比较难的。第二,当年钟鸣办南方诗刊是有一个构想的,他是一个搞策划的人,搞南方诗刊就是与北方对着干,当时诗坛上北方的势力太大了,南方被压得没话说,因此要寻找一种传统来拓展南方自身的空间。中国文学古典也好,都是一个天然的传承性,江南有一种文学传承的骄傲感,天然的诗歌就应该是在南方,而不应该是在北方。北方的政治性和概念性的东西,确实在我们的写作中是不屑为之的,是比较空泛的,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南方概念最起码在写作上应该还原到个人写作,诗歌写作的正道应该是个人性,李白是李白,杜甫是杜甫。很久以来我们的文学是事件性,小靳庄也好,甚至四人帮粉碎之后,一首诗能够全国上上下下共鸣,这是中国十年文革背景下事件性的,我们应该拨乱反正。85还是86年我在杭州,朋友问我在西湖边怎么从来没有写过关于西湖的东西,才突然发现我真从来没有写过西湖的诗,我自己都一愣,而我也特别讨厌说自己是杭州人,因为杭州的文化是小富即安,当时还年轻,认为这没有什么理想,所以我不愿意认可这种。到89年底90年初,我到小书店里买书,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文学和诗歌语言全部都要重新来过,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当时还有圣琼佩斯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在有的一切基础上都是错的”,突然觉得天灵盖都打开了。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写了《开篇》一诗。我虽然人在杭州,但我在这里找不到我的家乡,我感觉这里不是我家乡,谁讲到可能以后的家乡会找到月亮上去,很凑巧,我在88年写了一首诗,叫《月亮,我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很凄凉,大地上找不到家乡,我认为在这里我没有家乡。我既怀疑江南,又喜欢江南,因为一个写作的人就是这样比较纠结。
嵇亦工:江南风格,我认为江南风格肯定是有的,北方的诗,比较粗犷豪放,而江南的诗就是比较精致细腻。不讲地域的时候,回到人,个人差异总是很明显的,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因其自身的因素写的东西肯定还是比较有内涵、比较细腻的。诗是人写的,应该归到人去,环境虽然是有影响,人的身上他的经历、阅历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总体来说诗是诗人写的,好诗就是各种不同的风味,地域会影响一个诗人,北人到南方也会吸收到南方的好文化,同样南方人到北方也会吸收到不同的文化。
胡 弦:江南风格以前在我脑子里没怎么出现过。我反顾自身,算不算江南诗人?这不是一个江南风格确认的问题,而是身份寻找的问题。我老家徐州,我以前写诗是用徐州话打腹稿,但现在都用普通话,而普通话并不是江南的。我到南京十年了,实际上我祖籍倒是南京的。南京的一些诗人,像朱朱、韩东,好像南方特征都不是很明显。南京这个城市纸上江南的感觉远远多于现实,虽然南方和北方以长江来划分,但长江黄河这种大江河是代表国家象征的,南方真正的感觉应该是秦淮河,但是一去秦淮河你会发现只是个商场,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现实的江南不如纸上的江南。我觉得江南正在消亡,在城市中正在消失,特别在大城市里找不到,城市一模一样,河流污染,诗情画意的乡村消逝。还有移民频繁,像看江苏昆山一年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很多,基本上当地没什么人写,你说这些人是不是江南诗人?江南概念的形成在历史上是有渊源的,北方的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衰微构成了南方的兴起,南方的强必然是北方的弱。现在随着工业化的发达,城市整齐划一,地域性在消失,这个从美学的传承上可能就是画龙画虎。从过去无论是人在江南写的还是什么,写诗刚开始可能是一种经验,后来带有一个江南的风格。现在许多江南诗人经常以诗唱和,是不是有一个江南文化的自觉性。在历史上许多时期,所谓江南文学,就是中国文学。江南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巨大宝库,还是应该去保护,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危急,现在的小孩很多不会说方言,因为学校里讲普通话,家里也讲普通话,如果地方性语言在一个地方消亡了,那么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划一。江南风格的形成可能还是需要依靠个案,一些人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高标性的人物,这些人会有什么共性。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仙居,如果土生土长,接受了地方性文化的,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更纯粹些。
雨 田:什么是江南诗歌精神,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比较重要的话题。刚才大家在谈论江南诗歌的时候,我想到江南诗歌就是一种唯美,他这个唯美是与江南的山水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或者是优秀的诗歌,除了唯美之外,更多是诗歌的品质,诗歌的品质还与诗人的涵养、体验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前面谈到沈苇,即使沈苇比较粗犷,但他骨子里还是有江南的特征,我觉得沈苇过去的风格就是有他很柔的一面,我想江南诗歌除了有柔的一面还有阳刚的一面。我赞成胡弦的看法,诗歌是需要一批人来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在我们提出江南诗歌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有下面这种写作的本身,呈现给我们和读者一个大背景,包括江苏、上海、安徽、贵州,这样一个大江南的概念。在这个中间有一批人,包括他们的作品,像力虹的、潘维的、江离的,我们在聊的时候更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作品,就是不说他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谁的作品,我担心大家在讨论江南诗歌和江南诗歌风格,会不会将这批人误导进去,我就是担心这点。
飞 廉:从中国古典诗歌来看,我认为南北诗歌还是有差异的,随着南北的融合,差异变得越来越小。最早《诗经》和《楚辞》的差异,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南朝北朝的诗歌差异还是很大的,南朝的民歌和北朝的民歌差别是很大的。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对南北朝诗歌的评价太低,我个人可能对南北朝诗歌比盛唐更看重,南方文人写的诗歌也是被大大低估了,大家关注的几乎都是陶渊明等人,对北朝后面一批诗人几乎关注不够。后来文化大融合,南北政权对峙,南北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很多人身上南北兼具,像老杜,像李白的宣城诗等,都是很江南化的诗歌。到了晚唐前期特别明显,像李商隐、杜牧,南北风格融合非常明显。到了宋朝之后,北宋词和南宋词差别也是很大的,到南宋这批诗人写的就是繁复到了不能繁复的地步,而北宋苏东坡等人写得大开大阖。可能到了明清之后,我们南方商业文明的兴起之后,南北诗歌可能在更小市民化上还是有些差异。
朱岳峦:这个论坛非常好,这个命题也非常好。我感觉风格就是品牌,谈江南风格在当代新诗中的独特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深化下去的话,我感觉是非常具有促进作用的。
金岳清:我是写小说的,也搞书法,对于这个风格的问题是否趋向单一化的问题,我就联想到书法,江南的书法与北方的书法,江南的诗歌与北方的诗歌,南方的书法都是杏花春雨江南的风格,北方书法都是金戈铁马气势磅礴的风格。浙江、江苏书法家的江南风格,无论怎么演变,在江南风格的总体的风格下里面还是千变万化的。比如江苏的林散之和浙江的沙孟海,同是江南人,但风格却差很远,说明这种东西在总的江南文化积淀的滋养下,风格不是绝对的直接反映,肯定是人文积淀的厚积薄发的综合的结果。现在书法界都说,单一的江南的书法,和单一的北方书法都会走向狭窄,如果想走向一个高峰,必须南北糅合,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不知这一点用到诗歌上会如何,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柯健君: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江南风格是比较模糊的概念。我自己在写作中也确实没有想到过我写的诗是江南诗,我要往江南的方向写,可能是平时的地域不知不觉对自己产生了影响,让你有了江南风格或是北方风格的定位。江南风格的一个定位究竟对一个诗人是好还是坏?可能是从一个风格上来讲是一个封闭,可能对于一个江南风格来讲,江南诗人以后的出路到底是好还是坏?从台州诗人来讲有些像北方,有些很南方,这样不同性格的人,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是往江南风格去写,或者说我了解了江南风格之后再跳出江南风格来写,我是不是完全忽略这个风格,我就写身边的地域的东西,北方人到江南可以写江南的东西,江南人到北方可以写北方的东西。
钱利娜:关于地域性我也在我的诗歌创作中思考过,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于地域性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于女性作家,激发她创作中的内在潜能应该是女儿性和母性,我也是将女性作家分为女儿性较强和母性较强的作家。男性作家对地域性关注一开始就比较强烈,而女性作家就比较弱。毕竟江南是我们的生命河流,流到我们的生命血脉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江南的女诗人与大西北的女诗人风格肯定是有区别的。
汪剑钊:前面各位从不同的角度对江南风格的特点、在新诗中的定位作了探讨,内容很丰富。占春提出了诗歌写作的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它的上层由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部分构成,而它的下层则由感受的丰富性、具体性来体现,江南风格以其沉静、优雅、注重修辞以及敏锐丰富的感受力对诗歌写作的下层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晓渡则进一步建议将江南风格与提升到美学维度来看待。地域性的本身是一种很好的起点,但如果只局限在这里是不行的,这意味着必须要超越,我认为沈苇是做到了这一点。但只有风格化也是不行的,因为有可能会封闭。家新这几十年的写作是比较成功的,甚至在国际上也是有所建树的,家新讲到的实际上是指江南本身不是一个静止的,而是有一个流动性,有演变的,甚至外延也是有扩张的概念。江南风格我们姑且不作价值判断,我们不将它的好坏来作一个判断,比如江南的颓废,但实际上江南在文学上是有一种很重要的特征。言宏把江南的概念从历史的渊源,以及当代诗人如何向经典文化致敬上来考量,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应该从辩证地看待地方性角度来看待江南文化,我认为大家需要如何将劣势变化成一个诗歌的正能量来思考。晓明提到江南诗歌是对80年代中国化语言的一个颠覆,特别是对北方语言的皇权颠覆。我认为咱们谈论诗歌,离开语言是很不实际的,很不明智的,前面晓明也提到一个语言重建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看法。嵇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地域性,在一个大的江南风格下,作者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风格,自己对语言的建设等等,还说到对地域的超越,可能一个非江南人也写出江南的好诗,这也涉及到写作上的距离感问题。过多地禁锢在自己的地域性问题上,可能屏蔽了自己的视野。胡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我们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江南文化是否还有持续的发展,提出了江南文化危机感问题,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危机,重树江南诗歌,他提出一个观点,需要个案写作,成为重要人物、国家标杆之后发现有什么共性。从飞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七零后诗人的希望和对中国诗歌的关注。中国的古典诗歌七言、五言都是在汉朝奠定的,这为中国后来的诗歌起到了很好的归纳作用。我觉得江南诗歌柔情、女性的一面是很重的。另外金岳清老师从书法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觉得可能小说现在诗化也是一种风格。来自书法上的启迪以后无论是对诗歌还是小说都会有一种帮助。利娜从一个女性诗人在地域性写作中提出她的看法。雨田和健君则担心过多考虑江南风格会导致大家千人一面,这引发了我的思考,每个人即便在这个大环境下,都还是会有自己的特点。江南诗歌自有其丰富的一面,既有似水柔情的一面,也有坚硬如冰的地方。我们将江南风格这面旗帜树起来,但在这场战争中,每个诗人“作战”方式和“武器”也会有不同,这是不用担心的。江南风格的诗歌内涵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江南风格是具有流动性的,有巨大的吸纳性,包括对北方文化的吸纳和重新转换。我认为今天受益最大的应该是我,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大家能够对整个江南诗歌的地域性、个性化,以及在大江南的背景下如何追求自己的诗歌语言,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