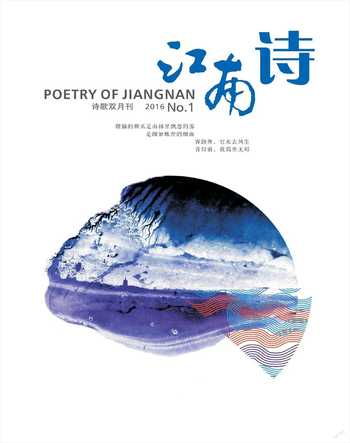甲壳虫诗学:平庸的敌人
江雪
荒谬是世界的本质。当你试图深入荒谬或欲解释荒谬之时,你就进入更为荒谬的境地。
——育邦
列夫·托尔斯泰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着只有他自己理解的东西,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又说,理解绝对是养育一切“友谊之果”的土壤。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真正地理解一位诗人或一位艺术家的精神世界,理解他的作品,是多么困难而又奢侈的一件事。育邦在《如何瞬间消灭耗子民族?》一文中同样谈到“理解”:“我相信我自己也是一名理解毁灭者。我们无法清晰地解释,理解障碍来自我们自身”,我亦深信此话。育邦理解了卡夫卡、博尔赫斯、佩索阿、普鲁斯特、策兰等大师,可是又有多少他的“读者”真正理解他文学精神的隐秘与深远呢。理解一个诗人,必须努力回溯到他的历史与记忆中去,进入到他的诗意言词与人文思想中去,去探究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当你真正理解了一个人,你同样也会成为一个智识上的受益者——你同样也会被“他者”理解。正如培根所言,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谏言中所获得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得到的光明更加干净纯粹。
育邦,无疑是我们同代诗人中的又一位杰出代表。他在文艺领域里,有着多重身份的转换。他的写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和随笔,呈现出一种博学而豁达的大家风度,一种融现代性与古典性于一身的文学范例,并且他的写作已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肉身最隐痛的部位,“进入到更深的黑暗之中”(木朵评语);他就像一个太极高手,在一种漫不经心的套路中,气定神闲地通过一些实验文本、隐秘高妙的技艺以及天真质朴、大智若愚的人生超然态度,治服文学名利场上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与游荡者,这是育邦为何能够赢得不同时代的诗人与作家持久关注与尊重的重要原因。正如诗人、作家韩东评价育邦时说:“育邦是一个独自写诗的人,读书、写作构成了他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秘密的生活。他的诗因此也与流行相异,而与书本暗合,在文雅、唯美的修辞中内心的激情穿越而过,有时甚为动人。育邦的写作告诉我们,诗歌对于人心的抚慰效用,一颗孤独谦卑之心对于诗歌的重要。”诗人朵渔甚至洞察到育邦诗歌写作的一些秘密之处:“他对诗歌史上的大师序列有深刻的洞悉,对形式感有儿童玩具般的不满和沉溺的热情。他的探索通常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条通往个人主义的牛角尖,一条通往艺术史上的死胡同。他乐此不疲。一旦他开始书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事物,一种温润的书卷气又扑面而来。”
大学时代,育邦在几位作家老师的引导下,他在对东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有了较多的涉足与了解的同时,同时也在深入学习东西方文学大师的写作技巧,其中有一种让他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写作技艺,即“仿写”,而“仿写”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早已存在于东西文化传统之中。还有一种比“仿写”更为高超的技艺,是“伪托”。这种技艺的真传与奥妙,同样被育邦掌握得炉火纯青。这种伪托的写作技法,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写作者故意在文本中设置的“障眼法”,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设置智力与辨识障碍的同时,而有力地增强文本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淡化或遮蔽原作者的身份与隐秘。育邦在大学时代掌握的这种“独门绝技”促使他在未来的写作中,经常使用这种“伪托”的写作手法,比如他的组诗《名人传》、《抄古逸诗三首》、《仓央嘉措遗逸之作》、《薄伽梵说》、《特隆世界诗选》等。育邦在组诗《特隆世界诗选》(八首)中有一段“伪托”的注释:“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在20世纪中期通过秘密文献发现了特隆世界,并撰写了《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通过深入研究,我发现特隆世界也存在一些诗歌,姑且抄录之,时为2010年8月至12月”。这一段注释,即是读者阅读这一组诗歌的关键所在与秘密通道,同时也是诗人通过“伪托”的技艺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诗人的思想与情怀。育邦这种写作技艺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的现象,在当代诗人中间是极为罕见的,同时应该引起诗歌批评家的重视与关注。什么是“特隆世界”?“乌克巴尔”在哪里?要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必须了解博尔赫斯写于1940年的短篇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描述的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博尔赫斯在此小说中高超地使用了“伪托”技巧,他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叫“特隆”的幻景新世界,并且“靠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发现了”乌克巴尔,而想真正找到“乌克巴尔”,又是如此曲折迷离,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特隆的文化只包含一种科学:心理学;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前“乌托邦”世界,它却是存在的,真实的,到处可以挖掘到关于语言与智慧的化石与废墟,并且这些化石与废墟不断地被人类再毁灭,再复制。可以肯定地说,育邦这一类使用“伪托”的诗歌作品,正是他乐于进行语言与心理实验的心血之作,诗歌先锋性极强的智识之作,如果没有一定现代文学基础的读者是无法进入到育邦的“诗歌之核”,或者说,“伪托”的写作,其实是一种难度写作,智识写作。我们可以想象,育邦在真诚地通过这种难度写作的方式,在向他喜爱的诗人、作家博尔赫斯致敬,从而也让进入到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特隆世界”。这或许,也是诗人最纯粹的诗歌精神表达。
论及育邦的写作,不能不提及他2004年12月出版的小说集《再见,甲壳虫》(。育邦在序言中有一段奇特的回忆,回忆他与一个叫“甲壳虫”的女孩的邂逅经历,这是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我的爱情只有一天。等我第二天再到溪边的时候,再也没有见到甲壳虫。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十天,我总在那个我们相逢的傍晚时分站在我们见面的地方等她,但她再也没有出现。我还清晰地记得八年前的那个黄昏,我记得她的泪水像花一样绽开在水面上……我记得我对她的承诺:“我要为你写一本书,我知道未来的书将是我们惟一的纽带。
“这本书”就是《再见,甲壳虫》。五年后,这本书变成了《体内的战争》。七年后,这本书变成了《忆故人》。十年后,这本书又成了《潜行者》。仿佛这些书名,潜意识里都与那个“甲壳虫姑娘”的深度意象有着神秘关联。作为诗人的育邦,在其小说集的序言中讲述了一个邂逅一位叫“甲壳虫”的女孩的“故事”,并且这个关涉“文学”与“爱情”的隐喻故事如此深远地影响他的写作与文学记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忖与猜想。我们再看诗集《忆故人》中的一首同题诗《忆故人——在宋朝,送一无名诗人乘舟沿江入蜀》(2006)。在我想来,这个“故人”可以是一位逝世的诗人,也可以是一位离别的友人,同样还可以大胆地想象这个“故人”也许是诗人曾经比较亲密的异性,或者是诗人记忆中的一位精神知己的混合而成“隐喻载体”。而在此文,我是愿意把这个“故人”想象成育邦文学记忆与人生记忆中的“甲壳虫”。“故人”离去之后,“她”变成了“他”,少女变成了男人,溪流变成了山河;或者说,甲壳虫变成了诗人,诗人重新回到岸上,诗人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宽广,并且开始了一场有关“自由”与“黑暗”的战争,甲壳虫少女自此给诗人引上了一条语言的、诗意的“迷津之路”(“天际之外”),“暗黑之路”。
通读诗人育邦的诗歌作品,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这个词就是:“黑暗”。这个词,在诗人第一部诗集《体内的战争》的第一首诗《夜有多深》即已出现(那是十三年前,育邦时年26岁),这个词在长诗《薄伽梵说》中甚至出现五次之多,足以看出诗人对“黑暗”这个修辞意象的迷恋程度。正如诗人在诗中埋下的深度隐喻:“一种‘黑洞理论,也许可以解释”它。这个词,在育邦看来,它既不是具体隐喻时代的社会性符号,又不是遁入人类精神绝对虚空的黑洞,它在诗人的诗歌中真实地存在着,它是诗人个体精神的深度体验与哲学探险,所以它可以在愉悦中穿行,可以在快感中挣扎,可以像银河一样诗意地广袤地流淌,我把育邦的这种极富忧郁气息的“暗黑诗学”特征,我把这种诗学称之为仅仅属于他个人的“甲壳虫诗学”。
是什么构成与支撑育邦的“甲壳虫诗学”呢?首先必须让读者了解本文赋予“甲壳虫”的语义与寓意。甲壳虫,是鞘翅目昆虫的俗称,它们的体色多呈红褐色至深黑褐。甲壳虫天性只产一个卵,然后从粪堆里把它滚到阴凉处。古代埃及人把甲壳虫的这种习性比喻为上帝在天空中滚着太阳行走,赋予地球以生命。甲壳虫就成了生命繁衍的吉祥物。在古埃及的文化体系中,更是被尊称为“圣甲虫”,在古埃及众神之中,它的地位超然存在。在这里,甲壳虫是一种充满智慧与神性的动物,它既可以在地上行走,又可以在水中游泳,同时还可以在空中飞行。有一种俗称“独角仙”的甲壳虫,威武,霸气。独角仙因为有着雄壮有力的一只独角,角顶端又分叉,故称独角仙。所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总是习惯于把昆虫分为益虫与害虫,甲壳虫也不例外。但是我认为,在自然界中,任何动物均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但是,在此文中,我乐意赋予育邦“甲壳虫诗学”的“有害性”,那就是——它永远是“平庸的敌人”,平庸诗学的敌人。因此,“甲壳虫诗学”在此指代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持有暗黑精神的诗学,它是属于那些独立的“潜行者”所倡导的诗学,它既持有幽深广博的诗学以外的文化基因,又持有强大的诗歌语言造血机能;它既强调呈现诗歌的纯正技艺与古今贯通,同时又强调诗人诗意栖居的“幽暗传统”与现实世界的“荒谬性”,从而在人性的诗学中倡导怀疑精神;因此,这种诗学暗藏着“自我觉醒,自我颠覆”的不断渐进的诗学理想。
纵观育邦的全部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诗歌涉及“夜晚”(“黑夜”)场景,甚至有一部分诗歌可以看出诗人就是在夜间创作的,事实上很多诗人都习惯于在暗黑的混沌的世界中思考一切。对于诗人来说,“他离不开黑暗”,他的“夜晚”是“不可亵渎的夜晚”,甚至他像诗人曼杰什坦姆一样,不忍心翻开这世界残酷的秘密,也不愿看到自己在黑夜中淬火的劳碌,诗人“总是在夜晚/寻找一些轻佻的事实/和黑暗带来的镇静剂/作为入睡前的安慰/落雨声并未停止/于我而言,则像静默的电台/持续着揪心的等待……”(《生意人》[2008]),这足以说明,这些诗,像诗人自身的忧郁气质一样,早已浸染上了暗黑气质。诗人的内心与现实一直有一种对抗,他不想做一个文抄公,一个刀笔吏,可是现实却又让诗人不得不在终极理想与现实命运之间进行回旋与妥协,抑或一个俗世的玩笑,就算是告别“体制研究所”,诗人仍然不能摆脱“暗黑”的命运,而诗人真正的独立情怀,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言:“拒绝平庸之恶”。事实上,这种暗黑的命运,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命运,动物的命运,甚至是宇宙的命运,诗人于是写道:“沿着黑夜的隧道持续奔跑/ 直到陷入梦的沼泽/ 他拼命用双手扒开一条壕沟/ 也许是砌出一条堤岸吧”(《沿着黑夜的隧道持续奔跑》(2008),亦如诗人里尔克的吟唱:“我喜欢这夜。不,不是夜,而是这夜的开端,夜的这句长长的起始句……”。
从写作时段来看,“2008—2010”,无疑是育邦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诗人相继出版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这三年期间,育邦写出了《名人传》、《西塘纪事》、《杂诗》、《福音书断章》、《特隆世界诗选》、《秒兴八首》、《薄伽梵说》、《春天通信》等一大批优秀长诗和组诗,另外像《忆故人》、《夜有多深》、《八字山上》、《体内的战争》、《像阿莱夫在品尝孤独》等经典短诗在朋友中间广为传诵。从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他的读者会有一个明显感受,就是可以读出他诗歌内在的孤独感与语言洁癖,而且一以惯之地坚持他的抒写特征,他的暗黑诗学——甲壳虫诗学。在随着诗人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大气的同时,他对世界的质疑,对语言的敏感度,也在不断提升。诗人不再一味地俯首,他开始关注到,一个诗人的“孤独”不能仅仅建立在情感渲泻与才华泛滥上,而更多的是体现诗人对客观世界的切入、反刍与转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再思考,不再盲从和满足于先驱者们的时代性思想及其个体精神的诱惑力,从而让自己学会质疑和废黜,让诗意的言词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育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批评》一文中,借怀念苏珊·桑塔格之际,质疑了她对加缪的批评与误读,这种在敬畏大师的同时却又敢于质疑大师的勇气与自信,足见育邦日常阅读的深度与广度,或者说,他已经在自己的诗学理念中,开始学会理性辨识“他者”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哪些声音是可靠的,哪些声音是可疑的,哪些声音将变为他的常识与养分。
“2014—2015”,则是育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在此期间,诗人除了创作出大量的诗作之外,还出版了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纵观育邦创作的所有诗歌,包括他唱和友人的赠诗与游记诗,均很少采用叙事的手法来记述诗人的人生轨迹,而是十分巧妙地把自己的人生记忆,抑或“体内的战争”,融化于诗行之中。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言说:“文学的历史不应当只是作家的历史,不应当写成作家或作品的历史,而应当是精神的历史,既包括生活者,也包括消费者”,而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生产消费者”。如果说在第一个创作高峰期,诗人的作品中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可让读者挑剔的瑕疵,那么从诗人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其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中来整体观察,诗艺日益成熟精湛,谦卑有余,霸气十足,甚至也可以读出诗人淡定阅世的现代性与古典从容,可以读出诗人精神上的“还乡意识”(育邦:《中年》)。
育邦近年的诗歌创作,有着浓郁的还乡意识,这种“还乡”,尤其体现在他与诗人之间应酬与唱和的大量诗作中,比如《雨中过华不注,访赵孟頫不遇——兼致风华、夫刚、散皮》、《秋风辞——追和苏野诗,在扫叶楼遥想龚贤》、《富春山居图——过黄公望隐居地,兼致立波、陈铿兄》、《不知迷路为花开——谒李义山墓园》、《鉴山堂记——与德武李晖同游鉴山堂有感,并呈小海、臧北》等。育邦的“还乡”不仅仅是回到溃败的自然中去,回到历史的寂静与深远中去,他还在努力回到“自我”中去,试图回到“古典山水”的怀抱里,诗人们常常雅集于人文山水与古典记忆中,其实就是试图以一种现代人的谦卑与无知向先贤致敬、追怀与学习,这种姿态就是诗人的另一种精神还乡:“向后眺望”;甚至,我愿意把育邦这种游记诗称为“访古诗”或“还乡诗”。育邦近年来在这种“还乡诗”诗中呈现的“精神还乡”意识在我看来,仍然是“甲壳虫诗学”的锐意进取,这种意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育邦诗学观念与独立姿态日趋成熟。透过诗人在“还乡诗”中设置的诗意迷障(借古喻今),可以读出诗人“精神还乡”的孤独、高洁与清远(育邦:《与商略访王阳明故居》)。
育邦是一个习惯于“向后眺望”的诗人。“向后眺望”,既意味着向古代先贤学习,向西方文学大师致敬,同时也意味着对时代记忆的追溯与沉思;“向后眺望”,又是诗人创作中潜在的精神脉落,它不是直线,它是曲折迂回的,终点可以回到起点,唯有不停地向后眺望,诗人更容易找到自我,找到尘世间遗落的诗意与美德。诗人因此在创作中不断对自己的写作经验与诗学理念进行反省、巩固与倔升,同时又在未来的抒写生涯中清醒地树立个体的诗学辩识度与路碑。育邦2015年11月创作的《危险的中年》中有这样的句子:“夜深时/ 琴自鸣/ 叶自落/ 中年的面影从茶水中浮现出来”,这样的句子在他八年前创作的《潜的样子》中得到回应:“空荡荡的大厅里没有偶像/ 看不到他/ 却隐约听到他的琴声”,甚至我们还可以在《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一诗中得到更深层的呼应。
育邦是一位具有多重忧郁气质的诗人,在他的身上既有着夏加尔与爱·伦坡式的忧郁,又有着策兰式的忧郁,陶渊明式的忧郁。育邦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流露出一种忧伤氛围,这种忧伤不是消极的,但它可以是暗黑的;这种忧伤不是个体的伤怀,而是时代赋予诗人的一种特质,一种诗性的存在物,它关涉到一代人的精神信仰与诗人之间的隐秘汇合,关涉到汉语诗人在时代碎片中坚守和创造的精神特质与时间简史,或者说,忧郁特质本就是纯正诗人后天无意识继承的传统,育邦持有并焕发这种特质与传统。
育邦是一位有着古典情怀与隐逸情怀的诗人。在谈论育邦汉诗写作的“古典情怀”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他的诗写中同时还存在着“现代性”;在谈论他的“隐逸情怀”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他的诗歌中同时又存在着“入世情怀”。所以,我常常在阅读育邦的诗歌时,会产生一种来自阅读与修辞的悖论与困惑,这种困惑不仅仅是读者的困惑,也是诗人的困惑,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困惑。诗人总是尽可能地把最痛苦、最困惑的、最迷茫的情绪深深地隐藏在诗歌的内核中。如果读者不用心地阅读它,如果读者不以拥抱尘世的心态去开启诗意的窄门,那么读者最终将获得一堆固态的修辞与言词,甚至一无所获。所以,阅读和理解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读者需要足够的智识与真诚,每一位诗歌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诗人一样,也是一位“潜行者”,他可以在阅读中游泳,阅读中徜徉,随着诗人的心绪而波动,随着诗意而潜行,诗歌真正的读者,其实也就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当我们阅读育邦的诗歌时,总会在不经意中在他的诗歌中,发现一些来自精神意志的世界的秘密,亦如“特隆世界”的秘密。诗人在《感谢光阴》一诗中写道:“我的时刻一到,你们立即滚蛋”,诗人还写道:“我是来自太空的风/ 我并不存在”。风是什么,风是时间的影子,时间是永恒的,永恒之物。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作品,针对于平庸时代而言,就是恒常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