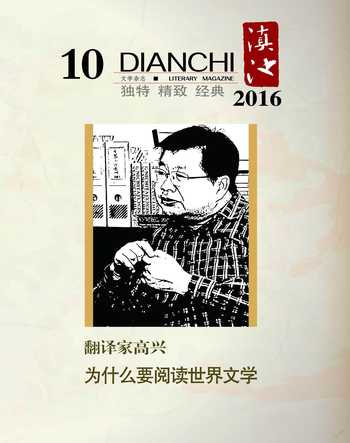河水流过村庄上空
陆荣斌
锦绣幻想着,时间就此停止,就像她坐着的这条小船,她不摇动船桨以后,它是静静的,泊在坡落湾的水面上。然而,红水河在流动,天上本就寥寥的星辰在渐次退隐,眼看天就要亮了。
锦绣看看跟前的塑料水桶里,大大小小的鲤鱼、草鱼、罗非鱼在欢腾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动。她把网又撒向水面,因为力气小的缘故,那张网并没能撒开成她想要的范围。她不想再重来了。她深知,即使再重复千万次,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能把网撒开得像一张晒玉米用的大竹席那么大而已。她拿起搁在船头的木桨,往深水里划去,小船便缓缓地向离岸更远的水面驶去。远处的那片水域之下,就是她的村庄。不,准确的说应该是她男人的村庄。她的村庄在山弄里,是一个窄窄的弄场,没几块好地,一年四季的口粮大多是从石缝里抠出来的,更不用说能种出大米来的水田了。嫁给男人的那个春天,她和男人足足种了一个春天,才把他家的田地都种完。那是她这辈子种田种地最多最欢畅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个春天过后,河水就开始一寸一寸地漫上来了。河水漫过田地,漫过村庄,漫上山坡。河水停止漫上来的时候,锦绣的眼前已是万顷碧波,村庄后面的山坡只有顶端露在水面上,像一艘永远停泊靠岸的轮船,汹涌奔腾的红水河也似乎停止了流动。男人告诉她,下游建起了水电站,从此,他们就是库区移民了。锦绣看着平静的水面,茫然问道,那我们的田地呢,我们的田地全被淹了,以后我们靠什么过活?男人安慰她,有政府,有这宽阔的水面,你怕我们还饿死不成?锦绣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说,可是,可是我要种田种地,我嫁给你就是为了种田种地来的。男人就笑她是个傻瓜。
有时候想想,自己真是个傻瓜呢。锦绣自嘲地笑了。小船在木桨划开水面发出的嗦嗦声里缓缓地前行,比起男人开动的那艘柴油机动船来,真是没法比。要是男人不出事,她也用不着开这小船半夜三更地到这水面上来。她划行了一段,觉得该是收网的时候了,就又把木桨搁在船头,才一点又一点地把网往船上收拢起来。网兜底快露出水面的时候,锦绣只看到水面有小小的翻动,心里顿时就涌起些微微的怅然。果然,锦绣把整张网收到船里后,三只不足一斤的鱼活蹦乱跳着,那刚才还灰蒙蒙的天空,就不可遏制地亮了。
锦绣的目光越过水面上浮着的一层薄雾,看见了远处山脚下的坡落镇。今天是圩日,坡落镇上那些卖肉卖菜的,卖鞋卖袜的,卖衣卖布的,已经开始忙碌着摆摊了。就是那山弄里来赶圩赶得早的,也都挑着几只土鸡或是一些诸如竹鼠、野生淮山芋之类的山货来到坡落街头了。
锦绣赶到坡落镇街头的时候,卖鱼的大头覃早已在自己的摊位前忙开了。锦绣把肩上挑着的两个连水带鱼的塑料桶放在大头覃的摊位前,说,覃哥,好生意哈,给你送钱来啦!
每次拿鱼来给大头覃帮卖,为了图吉利,锦绣都这么跟大头覃说。
大头覃卖的是人工养殖的鱼,锦绣拿给他帮卖的是野生的河鱼,这与他的生意并不冲突。当然,大头覃也是完全可以从中捞个差价的,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很乐意帮锦绣的忙,他觉得锦绣一个弱女子,真够不容易,也真够命苦的。移民搬迁到坡落镇上没几年,丈夫就因为在建新房子的时候不慎从房顶上摔了下来。她男人这一摔,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她八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地照顾着丈夫,直到他断气的那一天。坡落镇上的人们都说,这山弄里来的女子,真是个好女子呢,要不是他男人又因为身患重病治不好,她能把他照顾到老死呢。这不,男人去了都有三年了,她也没想过要改嫁。去上门替那些光棍提亲的媒婆都快踩烂她家的门槛了,她也没答应。后来媒婆也不耐烦了,有光棍或是和锦绣年龄相当的鳏夫叫媒婆去提亲,也懒得去了。坡落镇的人们也因此纳闷起来,好端端的一个女人,四十都还没到,咋就不想再嫁人了呢?这可倒好,家公中风偏瘫,也像他儿子一样躺床上了,看你想走也不好意思走了吧。其实,外人不知道锦绣心里的想法,大头覃也不知道。大头覃只是很钦佩她这样的女人。
大头覃直起腰来,垂着两只水淋淋的手,往她的两只塑料桶里看了看,说,好,我这就给你过称,等街圩散了你再过来要钱。你今天的收获不多,会卖得很快的。
呀,覃哥,我还不相信你嘛?锦绣说着,把一只塑料桶里的水和鱼倒进另一只桶里,把空着的那只桶放在身旁,呆呆地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鱼儿挨挨挤挤地在桶里窜动着。
大头覃说,那行,你忙你的去吧!
锦绣却还不动身,大头覃只顾忙着,也没空跟锦绣闲聊了。当回头看见锦绣还在,就有些纳闷:怎么?还不回去?我帮你看就行了嘛。
被大头覃这样一说,锦绣才犹犹豫豫地拿起刚才挑鱼来的扁担,把扁担一头撩过空塑料桶拴着的绳子回家去了。
锦绣家在离坡落街有三十分钟路程远的红水河边的移民安置点,房子还是刚移民过来男人建造时的样子,是两间还算宽敞的平顶房,楼梯口还是用油毛毡盖着,唯一变化的是,房子还没来得及涂抹石灰的墙面已在时光的流逝中蒙上了陈旧的色泽。当初,她和男人是打算盖上两层的,可人算不如天算,这生活一垮,就像当初村庄那些泥瓦房被河水浸泡后轰然倒塌的样子,再也没法阻挡。
锦绣来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动静。她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她,她不想去面对,就像她想让时间瞬间停止一样。既然时间不能停止,需要面对的,必定如汹涌的洪水一样迅速向她涌来。她推开门,看见卜民躺在地上。地上,有被水濡湿的痕迹和卜民挣扎的痕迹。锦绣知道,卜民一定是想上厕所,可是他应该清楚,他是没办法做到的。卜民看见锦绣进门来,脸上便不知是尴尬、困窘还是生气的表情,嘴里叨叨着:天啊,我家祖上可都做了些什么啊,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罪孽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如果可以,为什么不让我替阿民去死?
阿民是他儿子,是锦绣的男人。卜民想,如果他能代替儿子去死,今天需要照顾的,就是阿民,而不是他了。躺在床上三个月了,两个女儿轮流着来照顾他,每当锦绣也跟着到两个姐姐旁边帮忙的时候,卜民就叨叨着那句话。锦绣知道,卜民说那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两个姐姐有自己的家庭,不可能一直呆在这个家里照顾他。这不,二姐也和大姐一样,照顾卜民不到两个月,就回家忙自己的去了,空闲的时候才过来帮着照看一两天。
这可为难了锦绣。她总不能跟两个姐姐说,你们的父亲你们来照顾,我可不能照顾。她觉得这样的话自己怎么也说不出口,就算是没有阿民临终时的那番话,她也万万说不出口。谁叫她在卜民还好好的时候不把自己另外嫁了呢?那样,卜民遇到这一天,她作为他曾经的儿媳,最多也还不是偶尔回来看看。这可倒好,她娘家的姐姐肯定又在背地里说她是个傻瓜了。
锦绣在阿民过世后也都没想过把自己再嫁出去,并不是没有缘由。阿民临终时含泪嘱托锦绣,务必要她把儿子养育成人,并给他父亲养老送终。锦绣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她从没有过改嫁的念头。她想,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都熬没了,哪还有什么想法呢?不如好好带儿子,不让他受半点儿委屈的长大成人,到那时再由他替卜民养老送终,那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锦绣等不到那时,卜民却已躺在床上了。这是远在天上的阿民让她快点兑现她的诺言吗?他是怕日子久了她会忘却吗?
锦绣把扁担和塑料桶丢在门背后的角落里,走到卜民的跟前。卜民还在絮絮叨叨着,锦绣就制止他道,别说了!要是天随人愿,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来,我扶你上床去。卜民果真不再絮絮叨叨了,却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满怀歉意地解释自己为什么此时身在床下。卜民说,我是想去茅房,我努力着动了动,以为自己能行的。锦绣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已经没法动了。锦绣边说边使劲,却是使不上劲。她又把两只手臂穿过卜民的两边腋下,再尝试着提他起来,却只是能提到有床铺半高的样子。卜民说,你自己怎么能抬得动我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去叫阿松来帮忙吧。阿松是卜民的堂侄子,卜民瘫痪后刚从医院回来的那些日子,锦绣和两个姐姐没少叫他来帮忙做她们女人不方便做的事。叫了几次,她们也不好意思再叫了,两个姐姐便横着心做起了让她们羞赧的事情。虽然他们不叫,可是阿松空闲的时候也还是主动过来帮忙照顾一下的。
锦绣说,阿松出门干活去了。阿松到底有没有出门去干活,锦绣回到门外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她只是想,叫得了别人帮忙一两回,却不能总是叫别人帮忙,最终还得自己去做。
锦绣把卜民放下,到堂屋里搬来两个凳子放在床边。她重又把两只手臂穿过卜民的腋下,把他架起来,使他坐到了板凳上,自己随后也站到了板凳上。锦绣再一用力把卜民往上提,卜民的屁股终于稳稳地坐到了床沿上。卜民的嘴里随即也吐出了一串长长的气息。在这股气息的末端,卜民的骂娘声牵引出了他的感慨:这是死掉了才舒服咧。
锦绣边轻轻地托着卜民躺下,边埋怨道,别整天说死啊死的,你再忍受一会儿,我去烧热水来帮你擦洗身子。
卜民说,你不用理我,随便我什么时候死都行,越早越好。
卜民不仅尿裤子了,还把排泄物拉在裤裆里了。
锦绣没理他,快步走进厨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刚才憋在身体里让她一点也不好受,现在终于可以换上一口新鲜的了。
灶塘里的火苗在呼啦啦地欢腾着,锦绣的眼泪也在呼啦啦地奔腾着,掉落在灶塘口那摊被火苗焐暖的草灰上。锦绣盯着草灰上被两行眼泪滴出的湿点,脑子瞬间就被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这是什么命?侍候完儿子又要侍候老子?这个问题缠绕她已不止一次两次了。自从卜民瘫痪在床后,她几乎天天被它缠绕着。每次被缠绕上,她都绞尽脑汁为自己求解,却总是无果。现在,她不想被这个问题缠绕了,她决绝地把它抛到了脑后。眼下最要紧的是,她要好好想想,该如何去帮卜民擦洗身子?她不是怕脏怕臭。照顾阿民八年,她已习惯了,甚至可以说得心应手了。她害怕面对的是,卜民裸露的身体。之前,都是两个姐姐帮卜民擦洗身子,她们都走后,她就不得不做了。想到这里,锦绣闭起眼睛,烦躁地用双手胡乱地搓弄着自己的头发。她似乎想借此把一切都摆脱掉。但怎么可能,也就在她再次睁开眼的刹那间,一个想法闪过了她的脑际,让她有了一丝小小的兴奋。兴奋之余,她把眼睛闭上,伸出手去摸灶塘上的锅盖头,准确地摸到了锅盖的把手。她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把眼睛睁开,锅盖和锅头的结合处,沁出了几滴滚烫的水珠,一如她刚才的眼泪。她知道,锅里的水已经足够热了。
锦绣把一桶热水提到卜民的床边,说,爸,热水来了,我帮你擦洗身子。
卜民不领她的情,吼道,我不要你管,走开!任由我死活。我死后你叫人把我抬去埋就好了。
锦绣没理他,回头要挂在墙上的卜民的脸巾和自己的脸巾。
锦绣面对着躺在床上的卜民站好,把卜民的那张脸巾扔进脚边那桶温热的水里,接着用自己的那张脸巾蒙住了自己的双眼,并在后脑勺紧紧地打了一个结。卜民知道锦绣要干什么,就绝望地使劲摇头,不耐烦地嚷嚷道,我不要你管,你走开!任由我死活。我死后你叫人把我抬去埋就好了。
锦绣显得很淡定,说,你就别乱嚷嚷了,让我快点帮你擦干净。
卜民还是执拗地叫嚷着,想扭动自己的身躯,试图往床里头挪去,但徒劳无功。锦绣不理他,往前伸出双手,落在他的肚子上。她的双手开始游移,像一只初次爬出洞口的小兔,显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她摸索了一会儿,才摸到卜民裤头的那只纽扣。她窃喜,解开那只纽扣,双手又顺着卜民靠床沿的那条腿往下摸,很快就摸到了裤脚。她的一只手往平行方向移动,也摸到了另一只裤脚。她扯住两条裤腿,慢慢地往下褪去。当卜民的裤子完全被她扯下来后,那股刚才还隐隐约约的异样气味开始变得突兀、直接、令人猝不及防。锦绣不由得蹙紧了鼻翼。虽然也曾一次次地帮阿民端屎端尿,但面对卜民身上散发的异样气味,她还是不习惯,非常想作呕。她把那件裤子丢到一边,强忍着不让自己呕吐出来。她定了定神,双手又顺着卜民的一只腿沿路返回。她的手触碰到了卜民大腿的肌肤,她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像被烧灼了似的。她的手同时也触碰到了一些黏稠的东西,她知道那是什么。她依旧蹙紧了鼻翼,在心里想象那就是一些烂泥巴,以给自己增添一些坚持下去的勇气。她又褪掉了卜民的短裤,那股异样气味变得更强烈,自己的脸颊变得更灼热。她知道,有某些东西裸露在阳光之下,甚至在肆无忌惮地看着她。
她转过身摸索着去寻找锑桶里的脸巾,并不是很用力拧紧,就摊开来朝着想象中卜民的身体部位抹下去。锦绣觉得这样还不错,可她不能确定,她是否把那些粘在卜民屁股底下乃至大腿根部的排泄物都抹干净了。这种不确定感让她很抓狂。她照顾了阿民八年,每次都把他拾掇得干干净净的,她已经不能容忍自己有半点马虎潦草。她一把扯掉了蒙在自己脸上的毛巾,看到了卜民裸露的下半身还没完全被蒙住了眼睛的她抹干净,也看到了卜民的那个物件软绵绵地匍匐着,像躺在草丛里的一只大虫子。她立刻下意识地别过脸去,把自己从脸上扯下的毛巾覆盖住了它。这一回,她看到了卜民侧往床里头的脸庞已是泪雨滂沱。
锦绣没理他,准确地说她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干脆就不说,继续擦拭他的下半身。锦绣又提来一桶热水终于把卜民的下半身擦拭干净后,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卜民的一件裤子准备给他穿上。她抬起卜民的一条腿,套进一只裤腿,又抬起另一条腿,套进另一只裤腿。正当她抓着卜民的裤头往上拉的时候,看见她的那张毛巾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她愣怔了一下。等她回过神来,拔腿就冲出了门外,差一点就撞上了进门来的阿松。
怎么了?锦绣。阿松看着锦绣的背影愕然问道。锦绣却头也不回地向坡下跑去。阿松进门去,看到卜民光着下身躺在床上,似乎有硬物在顶着那张遮羞的毛巾。看见阿松进来,卜民更加羞愧难当,忍不住骂了一句:都怪这该死的东西不听话,让我死了算了。
阿松似乎明白了什么,也急忙跑出门外,冲着自个儿的屋子喊自家的女人,叫她快点也跑下坡去看看,锦绣怕是跑到河边去了呢,可千万别出什么事。阿松的女人听到阿松火急火燎的叫喊,就嘟嘟嚷嚷地叫着从屋里走了出来:你叫嚷个什么啊,火烧房子啦?阿松说,比火烧房子还严重。阿松简单把事情跟女人说后,女人似乎还在回味着什么,阿松就猛推了她一把,快去!阿松女人被这一推,也顺着锦绣的方向去了。
阿松回到卜民的床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帮他把裤子穿上。阿松知道,此时此刻,他说什么或者问什么都是不合时宜的。一个鳏居多年的老男人,还不到六十,突然之间被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女人触碰到,难免会有所反应。阿松在心里不怀好意地偷乐着,如果卜民不是自己的长辈,而是自己的同辈或是晚辈,此刻他准会拿他开玩笑,准会揶揄他:行啊你,半边身子中风偏瘫,老二没偏瘫啊?
卜民像是赌气似地,说,松,你把我掐死了吧?
阿松说,开玩笑,我把你掐死了我能活吗?再说了,你是我叔,又不是我仇人。
卜民问阿松,你说,锦绣还会管我吗?
阿松说,我看会。
卜民似乎不相信,问,真会?
阿松含糊地应道,嗯。
阿松到底还是忍不住了,说,叔,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对锦绣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卜民说,你个野崽,我要不是动不了,非狠狠地踢你一脚不可。你看叔不像个人了,是不?锦绣她一个儿媳妇,能拉下脸面来帮我换洗,我除了羞愧与感动,还能有别的什么想法?只是该死的本能反应了嘛。
阿松听到这里,吃吃地笑了。
锦绣坐在水边,望向远处的平静水域。她有些恍惚起来,像是晕船了。她站在船上,阿民驾驶着柴油机动船在前行。不知怎的,那柴油机动船就慢慢地往水面下潜行,独留她在水面上拼命地扑腾。她既没有沉下去,也没有向前游移。她想到了呼喊救命,却怎么也喊不出来,因此也就没有人来救她。她就那样扑腾在水中,眼睁睁看着阿民开着那艘柴油机动船潜行到淹没前的村庄。他把船泊在村口的池塘里,下船来,叫她进屋去拿锄头,跟他去地里种玉米。父亲在地里赶着老牛在开垄呢。她欢快地答应着,扛着锄头就和他肩并肩下地去。中午收工回来,吃过午饭,两个人不管不顾地躲进屋里一阵子,才意犹未尽地又扛着锄头肩并肩下地去。到地里,卜民已差不多又开好垄了。
锦绣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没想到那口口水把她给呛住了,她不得不没命地咳嗽起来。十一年了,自从阿民从房顶坠落,瘫痪在床,她每次替阿民换洗,看到他的宝贝都是沉睡的模样。她一次次地祈求,像曾经一次次祈求阿民能站起来一样,祈求他的宝贝会在某个夜里醒来。可是,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它也不曾醒来过。她的心便像寒冬深夜的火塘里渐渐冷却的灰。而今,被风一吹,那灰里,竟还有一星炭火,一丝微热。
怎么可以这样?锦绣在埋怨自己。
不可以这样!锦绣在心里告诫自己。
可是,她怎么再去面对卜民?不面对卜民,她又怎能代替阿民去照顾他,去给他擦洗身子?那样又免不了面对他的裸体,身体里的那一星炭火,免不了又会被风吹热。
怎么办?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阿民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刹那间,锦绣只觉得好像有人拿着一根根锥子,刺着他的脑壳,似要刺出无数个窟窿才肯罢休;又像一条条绳索,被人紧紧地缠绕在她的脑壳上,愈缠愈紧,似要把脑壳挤瘪了才肯停手。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感觉这世界似乎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唯有她自己一个人在这世间承受着那么多问题的折磨和蹂躏。她用力捂着自己的脑袋,想制止那些纠缠。她甚至躺倒在地上,像一只被无数只疯狂的马蜂叮咬的牛儿,满地打滚。
嘿,还真管用,她打了几个滚,那些纠缠竟轻而易举就解开了。就在她为自己感到庆幸的时候,她似乎听见了阿松女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声——
快来人啊,锦绣跳水啦,锦绣跳水啦……
也就在这时,锦绣才感觉到自己原来就在水中,水正灌进她的嘴巴里和鼻孔里。意识到这里的时候,她松开捂紧脑袋的双手,张开,像一只落进水里的鸡,扑扇着翅膀。那一刻,她多么希望自己是一只鸭子,扑棱扑棱地张开翅膀划着两只爪子就能游起来。可是,她仍像一只落水的鸡那样扑腾着,她仍能听见阿松女人撕心裂肺的无助的呼救声。
她继续像一只落水鸡那样扑腾着。同时她告诫自己,她不能死!她也不想死!卜民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呢,她还没煮饭呢,煮好饭喂饱卜民后她还要上街去看大头覃帮卖鱼完了没有呢,更重要的是她的儿子还没长大成人呢!
锦绣继续像一只落水鸡那样扑腾着,阿松的女人仍撕心裂肺地呼喊着……
虽然河水还在不停地灌进锦绣的嘴巴里和鼻腔里,但她似乎还能听到有杂乱、急促的脚步声离她越来越近了。她看见世界不是一片白茫茫的了,而是看见明晃晃的太阳光正照着她的眼睛,以及这流过村庄上空的河流。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