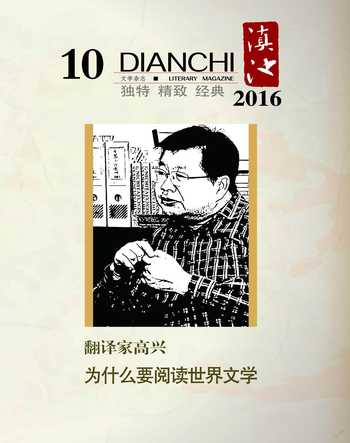芦苇岸的诗
春来帖
广步于庭,春气生发
舌尖上的蝴蝶,回眸杜鹃的羞赧
生而勿戕,除草的浪漫,免了
是故有秋后问斩
等我饱满的时候,想怎样随便吧
眼下忙于扑杀活禽
在遥远的戈兰
幽深的小径,风吹过
两旁高大的常绿阔叶木一直哗哗响动
似鼓掌通过了什么
阳光洒下来
一对暮年的伴侣蹒跚着走过
一辆婴儿手推车呀呀经过
一个孤独的背影缓慢路过
时间像在早晨,在黄昏,又像在正午
这一刻,我流下泪水
疾风从波涛万顷的东海吹来
吹到杭嘉湖平原深处的一片草叶上
突然不动,朝露在辽阔的阳光下
无声消散。夜晚我伏在阳台上
倾听新割的草地生长露水
久违的友人发来短信
说“生命如烟”,一道闪电划过心间
如一场宏大叙事里的强行停顿
时间的盛典
那高远的北方天穹,大雁在无声地飞
队列断断续续,无始无终
仿佛碧蓝的海面留下神的脚印
教堂的钟声响了,一群修女望着远方
这令人冥想的时日,宛如一块白绢
关于存在与消亡,关于短暂与永生
手拿经书的人,对着天空
反复诵唱一句台词:“结束痴迷开始”
而他脸上,鲜花掩隐地平线
慢慢地,慢慢地,半个月亮升上来
在屋檐那边,像长调一样升上来
窗下的瓜子黄杨,已悄悄绿透
立言者的火焰
与自己斗了一辈子
希望明天醒来,世界给我留了一道门缝门牌号还没来得及装上
但写着一笔娟秀的字——
一个给尘世留下刺耳声音的人
他的沉默是永久的,他点燃的
那片光明,曾击伤过人人痛恨的黑暗
我的平静生活
在厨房洗碗,清水冲走暗黄的残渣
剩饭在锅中平复了高温的激动
也不再期待我们的行为
带走,而睁着如我们欲望的细眼儿
给垃圾桶套上褐色套子
这里是归宿,我双手付出的劳动
不甘空寂张嘴嚎叫——填满的期待
飞逝而入:米粒、菜根、鱼刺……
中午河南商丘的张师傅
来修水管,他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离生活很近的人,留下了一只
破旧的鞋套,和一堆水泥的细末
我轻轻拾起,下一刻
一切都将在屋外的黑暗里
安静下来。这会儿,淳朴的修理工
或许已在梦中回到魂牵的故里
我提起一袋滴水的沉重,离开厨房
走下楼梯,从明亮走进夜色
有一种气味开始强行进入我的身体
隐喻
围着酒杯和茶壶
各自坐成光阴中生锈的铁钉
我们不谈偏头痛
只说黑暗里的光影,像散乱的排泄物
撒了一地
清洁工多了一份欢悦,只是略有怨气
有一个位置始终空着
寻找幻境的人手持线装书
里面总有一些句子不按语法出牌
打饱嗝儿的频率加快了,微微出汗
往东山上搬石头的动静
越来越小,但放滚石的声音却出奇地大
“天真是岁月埋下的病根!”
脱掉睡袍穿上麻服,天光明暗交织
前朝旧事,像一块破筛子
舍酒问茶,热气冲淡了现实滋味
长街深巷里,独坐的守夜人
把盏的手越握越紧
只认记忆衰退,不言老眼昏花
他手记
他在时光里的痛苦,欢愉而沉静
像他手里的物件——
有的是在地摊儿上淘来的
有的为朋友相送
也有自己打制的,粗糙、油腻……
他爱之多年,不曾有过厌弃
它们没有固定的形状,幼年到成年
每一天都在变化之中
但是,他发现自己爱坐下来
在公交车站台
在高楼大厦前的台阶
在公园里的水泥墩子上
在蛛网密布的屋檐下在一棵开始落叶的大树的根部
他的话越来越少,像他手里的物件
转动得越来越慢
他不知道转不动的那一天何时来临
他学起了针线活儿
想要缝住偶尔显露的莫名的恐惧
手可摘星辰
理发师不在状态。天高地阔
把喜悦修剪整齐
你转身就到东山顶上
嘿,拄杖走了一程,你数脉搏
我替你独揽繁霜鬓,你予我浊酒杯
落寞为青春盗墓
我记着来生要偷走你的步点
唯有默数可以治病
我抱紧胳膊,像抱着自己的高度
回头我再去找你的鬼脸
在山顶大喊
那个天上人,喊你吃晚饭可以不
对着远处喊一声
不需要太用力,也不需要
有什么讲究,就那么对着远处
平平常常地喊一声
像树摇落了枯叶
像雨终于洗掉了屋檐上的尘灰
像泪,学会了与悲伤再见
下班时,拐向通幽的小路
我看见那个用拐杖点击地面的人
望着黄昏中静默的河流
喉结在上下蠕动
仿佛对岸传来一阵回声,打在我胸口
远处的香樟树上,群鸟惊飞
小年夜
挑一盆马兰头的工夫够不够完成
一首诗?不要因为语速急促而放弃抒怀
日子是用来慢慢过的,但这一次
堵在嗓子眼儿的激动特别强劲
许多年以前预知,如果没有这次相聚
人生就不算完整,像一棵长势不好的野菜
睡梦中被冷落在荒野
意气的筷子夹起水芹、荠菜、青蒿……
是时候了,举起五谷杂粮的佳酿
这大地的精液或泪水
等待享受的人返回森林、草地、田园
做语言的义工,给陌生的事物命名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回到乡间草垛
去和童年的豆娘杂交,生下遍地野花
誓言把河山的菜地裹在飞毯里
带着它和故乡去占领福克纳规划的半径
酒话比身世清醒,唤景德镇的青瓷做儿子
在预谋里产下 7.4斤的诗篇
打捞茶水的意象,忙着将盘里的鱼翻身
油焖的骨架头上瞪圆了超现实的眼睛
但一切都将随酒气消散,只有
特罗斯特罗姆的飞鹰还提着山谷里的阴影
不管你爱与不爱,它已属于精神的奖章
拆解人性,或重塑灵魂的事情
就交给才华横溢的时间去精雕细琢吧
年景的闹热或粗糙,我们都没有理由嫌弃
断头路
走着走着,前途没了
不绝望?算你狠
你不低头,也会叹气:条条大路不通罗马
欲望收住阵脚,仿佛夜盲症患者
不知从哪个方向
将自己带离此刻
你知道滚烫的车轮也无用
除非飞过去
但鸟儿都睡了,没有谁能借出翅膀
事实上借你也无用
属性的不兼容,就如死扭着的两颗心
始终打不通
那就比能耐,扛到底
有种别退下去
迂回包抄,这一招断头路肯定不曾预料到
冬天过后百花开
你闻到的香,不可阻挡
此刻你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站在黄昏的河边
想从河里抽走孤独多么不易
不像青春,水一样流逝
在山中时,我用稻草束腰
如今在异乡,我拴的是结实的皮带
这肉体要守住什么我说不清
麻木地站在黄昏的河边
风吹皱了流水,也吹碎了我落在
水面的脸。我看到的人生
在水面晃动,在夕光中失真
“逝者如斯!”我唇齿翕动
依次穿过一片弱柳、残荷、荒草
多少匆忙的过客,如我一样地走过
天板着脸,黑暗来得正是时候
盲
端坐天堂摘编方言,乐此不疲
变卖铜钱者,胃里香辣翻涌
我们忽然就被扣上一顶文盲的帽子
人间,只配有炊烟
雨是子夜时分落在屋檐上的
月亮收拢它的翅膀
一切交付黑暗的,都在静待黎明
手把一豆青灯
光线指引的方向,从来皆无声息
我在行走,很慢
黑暗里伸出的双手握住了颤栗
寂静在延伸
夜晚,火车追着铁轨的寒光
在空寂的黑暗里疯跑
铁轨的几何学,简练、精深
答案在将要抵达的远方
车厢里的乡愁
被冲了开水的方便面泡软
刺鼻的气息联合喉结的响动
堵塞了充斥着汗味的过道
谈兴弱下来,一直弱到鼾声里
有人冷不丁坐起
木然看着车窗上一晃而过的家国
哐当声撞响的午夜
洒满月光和乡愁的花火
关山恍惚的面容,像过客一样惊慌
大地深处的车厢
灯影晃闪、幽暗而模糊不清
独坐爱晚亭
头顶在呼啸
刮风,下雨;千里之外的友人
说雪在烧……
四下里一片苍茫
这广漠的夜,适合密会
霾
这残败的身体,这迷乱
松鼠们已经失去赞美森林的耐心
你在旅途,你的骨头长满刺
你的羽毛,像发丝一样
是天空失去灵魂,还是灵魂
失去了天空?无人应答
迷恋低音做假。脂粉失血过多
如今,脸面越来越虚幻
光明昂贵
我们都倒退着,去后山掘墓
把黑夜折叠过来
这好玩儿的事
埋葬了又一个灰色的发疯的白昼
我在高原
高原上,连绵的山野仿佛吐露着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燃烧着的骏马
嘶鸣于苍茫的天际
赶着羊群和露水的孩子,在山路上狂奔
钻出栅栏的狐狸偷走了岭上的明月
那个占山狂舞的仙人,啪啪地
甩着水袖;她喊一声我们的乳名
四散的羊群,纷纷如落叶归根
满山花儿开啊,云朵在篝火旁成亲
日子甩动鞭子抽打寂寥的青石路
不吭声的树,盖住了鹰隼的忧伤
夜色守在村口,吹过的山风,叩响柴门
宽恕
小马驹撒开四蹄奔向原野,一棵嫩草
宽恕了它的放肆。闪动的火焰
在阔大的绿地打开羽翼。一粒尘埃
打破了午后的寂静,喧嚣只是游戏的
一场情欲,隐遁于万物的内部
要被宽恕的,端坐如石佛
二郎腿晃颤,一次香艳的走神该不该宽恕
佛没说。毛孔里的汗滴盗走大海的盐粒
我该宽恕大海,还是自己的无边无际
挽留
燕子挽留它的呢喃,雨水细软
翅膀测度的时序,在飞也似的轮转
如果我有羽毛,是不是也会轻盈地带走天空
这该有多么美
我看到西沉的夕阳挽留时光的灰烬
我看到一条走向屠刀的狗眼中的哀怨
那拴在脖子上的绳索和
牵它的手,没能将它健硕的身体挽留
面对这个世界
灵魂究竟有什么用处
可怜的温暖,像打滑的泥土
挽留我们活着,并且极力活得坚实有度
倘使春阳还在挽留它照彻的生灵
像树荫下
那只啄食的母鸡,身外的世界与它有何关系
在它不远处,一队蚂蚁匆匆赶路
更远处的草坪上
一场欲火正在挽留发情的公牛
只要眼睛够使,我的发现就会将我挽留
热情、豁达,有时也执拗
身体的地图
有风,雨也不小,为漫漶的云游导航
国破山河在……有人吟诵,拧断数根须
我多么希望彼人朝我笑一笑,像高枝的喜鹊
把一些无用的抒情丢弃,只埋头啼啾
每一颗落地的果实都有着一个强大的国家
放心吧,我不会走错,路上民生不多艰
如蚁的信男善女,手里攒着亮晃晃的银子
随时随地,我的身体都是一座庙宇
我被时光举着,像有人出行时举着的地图
消费时代的抒情
五月,小区门口的光阴涌动生活的激流
卖酸奶,卖汽车,卖防盗锁,买桑葚……
每一天都在熠熠生辉
玩滑板的小女孩,一个趔趄
打断了进出的人流。只有哭声是最真实的
这一带,年轻人居多,脸上脂粉肥沃
没人在意生儿育女的祖传偏方
古老的手艺,抵不过一口喊定的价格
上门服务,省去了日常的繁琐
政府的民生报告,酷似夏天的隆隆雷声
谁见过和风细雨,汽车飞溅的脏水性子急躁
抬头观景,低头赶路,过客匆匆
进入五月,盛大的集会卷土重来
移动的田野,袒露在一排装桑葚的箩筐里
紫墨的果实,翠绿的叶子
卖桑者小心翼翼,轻轻掀开的薄纱
透露出消费时代的精致,酸酸甜甜
玛瑙、保险箱、联排别墅、高层公寓
灵魂和肉身,像打进堡垒森严里的间谍
出口顺着电梯,速度通天达地
扶摇直上,手可摘白云、星辰,接鸟屎
高处终究不是什么好玩艺儿
那就选择向下,一直向下,一楼、负一楼
尽管走,被汽车尾气带着走
小区门口,卖酸奶的还在,卖防盗锁的还在
只是那卖桑葚的,是不是被卖汽车的送走
玩滑板的小女孩变成了玩轮滑的小男生
但他无心专业,而是吊在附近的一棵树上
摘青果,像一只不谙世事的猴子
阵阵尖叫,印在了本地消费周刊的封面
07省道
从一本书里取走目光
驶入 07省道的大巴车,突然莽撞
窗外的原野,像被公牛尾巴扫荡过
又像书生翻过的册页
记忆迅速滑入盲区。一块块
麦田缝合的大地,开始生长色斑
真快啊,苍老的年华
被抽走的青春,随意丢弃的抹布
历史翻过务虚笔记,飞黄未必腾达
富有只是大地的一块疤痕
凯歌不断,世界夹在玻璃里
我是如此地惦记工资、福利、声名
酸胀的颈椎,在档位之间换来换去
速度始终提不起来,下一刻,车走直道
欲念先一步到达,有人开始诵经
头顶的高架,动车呼啸射来
07省道躬身而过,像一个懦弱的人
以一个意象缩短与生活的距离
还能对自己寄望啥呢,生活不是毛毛虫
惊叫有什么用,孩子的母亲在失控
大地宽厚,不只花红柳绿,还经得起跺脚
以一个意象缩短与生活的距离
真正的诗人,被父亲架在脖子上,招摇过市
而我们,只能跟在身后,猫腰雀步
在猎猎风中,表情腐朽,灵魂被活捉
超市、美容院、干洗店……要经过的太多
端着汤面的小二,长得比一声吆喝清瘦
他油腻的工作服,早已把日子穿旧
一生都在从别人的抬爱里品味口感
那么,盯住这世界的举动,是诗人的义务
初雪
像一声问候,悄悄地将脸贴在窗棂上
玲珑的一生,很短暂
场面可大可小,只要获得足够的尊重
亲人在手机里赶制温暖
爱,比多添一件衣服实在
为什么雪片是白色的
而且透明。这洒在惊喜中的时光
将日子拉长
仅仅为了那激情的一点凉爽
我张大嘴巴,让舌头跑出紧锁的身体
只有冒着热气的舌尖
才有资格接受天宇的馈赠
雪,继续下……
旅程
雨夜,开车行驶在幽暗的省道上
模糊的夜色不时闪过
前方被雨刮器搅碎,乱飞……
低调真是一种冒险
车载音乐自动归零,寂静覆盖的时速
稍纵即逝
车轮扬起的泥星
仿佛散落在身后那破碎的恐惧
这时间,已容不得去细想该想的事情
总有东西会逼着你放下放不下的
一切都在进入遗忘……前方有光
晨省
子不嗣父业,我离草木
很远,不懂伤悲
我的心很小,装不下辽阔的世界
就像这挑剔的胃,喜欢素净
生如草芥,免于缛节
认得寒露、薄霜
每天用警觉的眼神和紧蹙的心指认光阴
爱计较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
深春过眼,我连哀怨一片落花
也不会
窗外,园丁拽动的割草机
正在减去多余的春意
成天耽于琐事,我活得越来越像一个
正常人
心如空山
有路至半山,不平坦
泉水解近渴,林荫里浮动暗香
往左,是悬崖;往右,刚被我走过
索性躺在一块磐石上
看天
鹰的翅膀越来越高,越来越尖
天空,不蓝,也不伟大,但我爱它
远近高低的树,发着芽,开百花
乍暖还寒天气,虫声绝
我本轻狂,对着四下的空寂一阵喊叫
回音惊扰一地落花
存在让一个人假装强大
只想告知天下,很多时候的我
心如空山
体检报告
只有手里的这张纸
才能展示中年的阔绰
给身体的每个部件宣判罪行
精确到小数点
一生的长度
就这样一次次地被裁剪
而我最在意的是
什么时候我的灵魂
也能列入常规体检
激情的胃口
不再了,不再!
路边,一排玉兰的惆怅
被朝露洗去铅华
流着鼻涕的孩子风一样地跑远
没人知道冻僵的光阴
怎样骗过一个人的视线
把发芽的机会让给腐朽的事物
活着,只剩姓氏
我需要喂饱激情的胃口
像喂饱一头咆哮的狮子
高处
炫目的高楼,肃立在上班途中
一声口哨经过我
在我仰望的高度
一群人膏药一样贴在玻璃幕墙上
看不清他们的脸
黄色的安全帽和背上的红吊桶
让更高的高处,温暖、悦目、稳靠
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抬头送上惊讶
而让路人更惊讶的
是他们中间竟然有女人——长长的马尾辫
像划过时空的一道黑色闪电
他们说着黄段子,放浪地大笑
沾满泡沫的污水通过手里的刮器
流进红色的吊桶里
蓝天渐渐直立,离人们越来越近
太阳靠在玻璃上,安静地睡去
她的梦,在反光,干净、清新
那个赶着种猪的人
那个赶着种猪的人
和他的种猪,兴冲冲地走在林荫道上
一辆运化肥的皮卡
呼啸而过,卷起的尘土将他淹没
“狗日的!”他吐掉旱烟,指着前方
拍了一掌大腿,跳着骂道
只有那头周身通红的猪
摆着尾巴“哄哄”地赶路
像一辆加满油的拖拉机
他追上去,手里的烟斗
仿佛一把无声手枪……皮卡眨眼就不见
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
他的话也多起来
喜悦了钻进他的皱纹和牙缝
种猪越走越快,越走越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