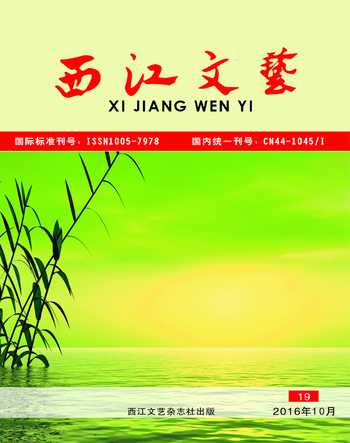浅析《月牙儿》与《日出》的女性悲剧命运
熊念
【摘要】:从古至今,与男性相比,女性这个群体一直都是作家们致力于描写的对象,而在中国现当代中,作家们往往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以此来揭露出暗藏在封建传统和金钱社会中的污垢。笔者通过对老舍《月牙儿》与曹禺《日出》中女性角色的对比分析,从不同方面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及原因,进而转入对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
【关键词】:月牙儿;日出;女性;悲剧;命运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墨客们的创作重心,但她们却往往以悲剧结局。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小雅·谷风》和《卫风·氓》中的弃妇形象。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写妓女霍小玉与书生李益相爱后遭到背叛,最后抑郁而亡。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女主人公秀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被逼与心爱之人双双化为鬼魂。元杂剧中的《窦娥冤》借窦娥这个形象展现出了女子被压迫被损害的悲惨命运。明代描写女性命运的作品丰富多彩,其中熠熠发光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述了杜十娘付出一切之后惨被情郎典卖的悲惨故事。清代的杂剧试图摆脱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长生殿》中将国家的悲剧命运转嫁到一个女子的身上,至此杨贵妃成为红颜祸水的代表人物。
近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问题小说的兴起,许多作家开始关注到女性悲惨的命运,特别是小说和戏剧这两种体裁,女性作家们更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搬上文学的舞台,借以揭露出大千世界中,女性仅仅是依附他人的寄生蟲这一社会现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月牙儿》与《日出》在吸取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教训之后,开始深挖女性这一角色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自我认知,不再将所有悲剧原因仅仅归结于社会等外部因素,这暗示着女性自我意识初步觉醒,也显示了作家们对女性悲剧命运这一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不再与重大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作家们单纯地以一个农村或都市中的普通女性为代表,细致地描写她们的日常生活,从最纯粹最根本的生活本质来剖析女性的悲剧命运。《月牙儿》中的“我”与《日出》中的陈白露,她们在这吃人的社会中苦苦挣扎着,除开社会的压迫,还要经受自己内心的煎熬,精神上的苦痛,即使是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女性形象,无一不是以悲剧告终,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女性无法在离开家庭后在社会上取得真正的独立,任何努力最后都只会加速飞蛾扑火的过程,乃至被黑暗所吞噬。
一、殊途同归的不幸命运
《月牙儿》是一部中篇小说,描写了母女两代沦为暗娼的悲剧命运。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去世以后,剩下的母女二人只能相依为命,母亲只能帮那些工人洗一些又臭又硬的衣服来勉强支撑生计,然而她到底是日渐消沉了。没有办法,她只能再嫁,幸而第二任丈夫是个较为阔绰的好人,这样舒适的日子过了两年之后,丈夫再次出了意外。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女人再也站不起来,万般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做暗娼,直到脸上涂再多的粉都没有几个人原来来光顾后,她再一次嫁给来了一个娶不到老婆的卖包子小贩,生活将她磨砺得没有了人气,她唯一知道的就是本能地活下去。
主人公“我”多少受了一点教育,她知道母亲一半是为了自己才会这样选择,除了替母亲去做这件事才能帮到家里,她想不到别的办法,但是她心里同样也知道,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成为母亲这样的人,终于母女二人的关系日渐疏离了。毕业后,她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只为有一口饭吃,不被饿死,然而竟然连这一点都难以实现。起初,她找到了餐厅服务生的工作,但无法接受招呼客人时还要坐到腿上去忍受那些屈辱,经理最后也劝退了她。从小缺乏关怀的她在遭遇人生困境之时,以为找到了美好的归宿,谁料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被包养的情妇。在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之后,为了生存,她走了母亲的老路子,染上花柳病之后被曾经的客人,现在的警察康先生抓到了监狱。看着窗外的天空,她的人生不再有希望。
《日出》作为曹禺继《雷雨》之后的又一大作,通过描写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揭露出了女性在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中的困境。这里有高傲孤独、爱慕虚荣的陈白露,无力反抗命运的小东西,受不了生活压迫而抛家弃子的黄省三妻子,辛苦照顾四个孩子还被丈夫逼着融入贵妇圈的李石清太太,被损害被压迫的妓女翠喜。这许多的女性形象汇成了半殖民地社会的女性大合唱,宣泄出女性内心的苦痛与悲愤。
陈白露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女性,父亲去世之后,她想要凭借自己的年轻与美貌在大都市里传出一片天地,最后却沦落为红舞女,成为有钱人的玩物。她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构成了整部戏剧的结构。一方面,她憎恶这个虚伪而龌蹉的金钱社会,人心未泯的她甘愿冒风险救下小东西,对街边的乞丐们也十分同情。另一方面,她沉迷于奢侈的金钱生活,“我要玩”、“要舒服”、“出门要穿好衣裳”①。她认识到了自己所处境地对的黑暗,但是又没有办法逃离,难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呆滞地思考。欠下高额债务的她,想要逃跑但却被恶势力金八盯上,只能在日出之前服毒自尽。
无论是《月牙儿》还是《日出》,里面的女性都难以逃脱社会与命运的掌控,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双无形的手拉着她们一起堕落,所有的挣扎都无济于事,所有的反抗只会招来更悲惨的结局。她们所处的空间虽然不同,一个在农村,一个在都市,但她们都在这个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规则下沦为妓女。她们二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思想,懂得基本的礼义廉耻,但在遭遇社残酷的社会现实时,全都束手无策。“我”和陈白露的人生轨迹大致相似,都曾经历过最初童年的美好,享受过父母和家庭的温暖,家庭遭遇危机之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成长起来了,都天真地想要依靠自己和学到的知识闯出一片天,至少获得个人生存的基本。可惜三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繁华的大都市,一样毫不掩饰其吃人的本质,尤其是对独身女子的侵蚀。“我”和陈白露也似乎都有過摆脱悲剧命运的机会,但最后也都以失败告终。《月牙儿》和《日出》都是一首女性的悲歌,它从女性的角度敏感而细致地探索着隐藏在女性悲剧命运背后的深刻内涵,发人深省。
二、女性悲剧命运之根源
两人殊途同归的不幸命运有其症结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形成了一套密不透风的礼制,它用简单的三纲五常就束缚了女性的一生。辛亥革命之后,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始终没有打碎这种吃人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女性,仍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女”字最开始为跪在地上的形象,女性的生理性别是先天的难以改变,但其社会性别是后天形成的,可以通过人为努力改变,但是从传统的性别文化来看,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等都把女性作为社会的次等公民。
社会中残存着不少遗老,他们仍旧坚守着那些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并将之强加到女性这个群体上,甚至是女性自己,也以三纲五常为自己的行事准则,虽然她们对生活的遭遇感到不公,却只是将这归结于官府、老爷、假洋鬼子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未曾深思。而新兴的大都市中,看似中西交融,实际上内里却鱼龙混杂,迂腐的封建主义与西来的拜金主义熔铸一炉,身处其中的女性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整个社会成为吞噬人的巨大机器。
韩月荣和陈白露即是那个时代中被牺牲的被损害的人物,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两人的性格也是造成这一悲剧命运的要素。父亲早逝,母亲成为暗娼,这使“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摆脱家庭的阴影,但受过教育的“我”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忍受餐厅客人的屈辱,面对男人的欺骗也不敢反抗,家庭和经历的社会遭遇让“我”胆小而又卑琐。“我”虽然能够认识到女性离了男人的支撑在这个社会上根本活不下去,但自己最终也能没逃脱。主人公“我”有着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毅力,为了“活着”这一基本的生存要求不遗余力,但同时“我”也是一个纯真的年轻女孩。然而,“我”始终不敢真正去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恶势力,只能在坎坷的人生中起起伏伏。
陈白露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女性形象,她贪图享乐而又同情弱者,崇尚拜金而又性情高傲,勇敢无私而又胆小懦弱。她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想要跳脱出去,却又越陷越深,终于自食恶果。她的悲剧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选择,但实际上仍是“人之道损不足以遗有余”②的社会现实所逼。她在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大胆地独自来到繁华的大上海,在这里谋求人生的出路,最终成为所谓的上流社会中男人们的玩物,她时常在凌晨坐在窗前抽烟,静静地思考着,给人一副落寞的图景。她精神上的痛苦来源于还未泯灭的人性,而身处无望之境的自己对于那些不公的社会现实无能为力,只能任由自己不断地沉沦。
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对社会人生始终不抱有太大希望,消极对待人生,后者则有一个逐渐冷血的过程,在认清自己之后,终于自杀。前者无路可選,后者有方达生,但是她自己却无法摆脱奢侈的生活,终于被自己所欠下的债务逼死。
总体而言,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三个方面,即封建制度与礼教、社会现实与个人的性格因素。“我”和陈白露作为现代中国中的女性代表,传达出的是整个旧社会中女性的基本生活状态,或许真正的现实并不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一致,但女性始终都是社会的最底层。
三、暗示着悲剧的不同意象
《月牙儿》与《日出》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令人扼腕叹息,但她们的悲剧命运在文本中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即作家都用具体的意象来暗示人物的悲剧结局,同时也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
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文中出现最多的意象作为题目,这显然是作者的故意为之。《月牙儿》正在文中不断出现,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被迫成为暗娼等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总会在深夜看天上弯弯的月牙儿,它似乎能给“我”一些安慰,是“我”的伙伴。文中的“月牙儿”总是清冷地挂在空中,它象征着不断被周围黑暗所吞噬的光明,我就是“月牙兒”,“月牙儿”也就是我,“我”也在逐步为这个黑暗社会所吞噬。“我失去了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我和妈妈一样了。”③这句话是作者用含蓄地语言来描述“我”遭受了玷污后,受到了生活的打击。小说中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满月,永远都是那么一个弯弯的月亮斜挂在天边,月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但在这里,美好的事物从来都是有缺憾的,亦如小说这种的女主人公,偏偏遇见了这个不公平的世道,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好的事物注定会被毁灭。
日出,本是希望的诞生,而讽刺的是,陈白露却选择在这个时候自杀,她的人生没有了希望,这个社会同样如此。在她死前,只说了一句话,那是一位临终的老人曾经说过的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④日出即光明的未来,是深藏在黑暗中的人们所一直期望的东西,它象征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然而,在陈白露在此时绝望自杀,日出与生存在黑暗中没有光明未来的人们形成对比,使读者看完之后产生强烈的悲剧意识。而方达生在工人的打夯声中萌发了要改造这个吃人社会的想法,他站在工地里,看着日出,神情更加坚定了。方达生是迎着日出的人的代表,从方达生来看,日出象征的是革命的到来,象征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人运动,是希望,是黄金的未来。
两部作品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意象来展示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女性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特别是《月牙儿》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文本中的意象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月牙儿这个意象成为“我”心灵的感应物,与“我”形影相吊。而《日出》中也多次描写陈白露在窗前一坐就是整晚,但从来没有写过她是否看到过窗外的日出,直至她自杀的那个凌晨,在陈白露服毒之后仍是没有亲眼所见,作者隐晦地暗示陈白露是无法看到日出的那一类人,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即她最终的悲剧结局。
四、作者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
老舍素来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对旧社会的父母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用“诗化”的散文笔调描写了母女两代被迫沦为暗娼的社会现实,对于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分层,老舍都不太注重,相反,他对人物的内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展现出小女孩成长的心理过程,以及她对这个社会的看法。老舍的小说中不乏对命运的描写。例如《我们这一家》中,我是警察,所以我的儿子,我的女婿也是警察,甚至我的儿媳妇的哥哥和父亲也是警察,警察的女儿只能嫁给警察。《月牙儿》中的“我”也是一样,最终沦为和母亲一样的暗娼。“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次遭受命运的捉弄,作者借她们来挖掘出社会的缺陷,同时也使人们正视这些缺陷,有勇气去改变这不公正的社会。
作为戏剧大家的曹禺,非常注重将戏剧矛盾尖锐化,他从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展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上层社会中心狠手辣的银行家潘月亭、中产阶级的阴鸷的襄理李石清还有那个被迫亲手杀死自己三个亲生儿女的小书记员黄省三,甚至是那个从未出场但为所有人忌惮的金八爷,他们四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的阶级矛盾。同时,这里面也包含了曹禺对人生命运的思考,显示了命运对人的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抗争这一矛盾。他给笔下的女性都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性格特征,使她们本身就成为一个矛盾体。无论是繁漪还是这里的陈白露,都论证了这一特性。他将人物悲剧命运的改变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坚信一切丑恶的东西必将打破,并且有信心打破。
《月牙儿》与《日出》共同展现出了30年代中国女性的基本生存状况,掺杂着血汗与泪水,一方面,是对真善美的践踏,是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侮辱与压迫,他们被压抑到窒息,而另一方面则是假丑恶的横行,虚伪做作、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令人不耻。这两种极端形成对照,引起了人们对这残酷社会的强烈仇恨,同时也激励着人们为了黄金的未来不断反抗、战斗。(指导教师 陈慧颖)
注释:
①④曹禺《雷雨 日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1
②老子《道德经讲义》,中华书局,2013-4-1
③老舍《我这一辈子.月牙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 年出版。
[2]老舍:《老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出版。
[3]陈秀平:《老舍的悲剧创作论略》,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出版
[4]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