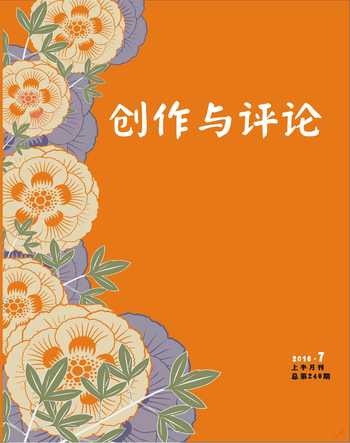庆余年
1
年关逾近,父亲越发期待大雪的降临。
家乡素有年俗,大年初一的第一餐需以萝卜开菜——大抵是从俗语“冬吃萝卜夏吃姜”而来。小时候拔萝卜洗萝卜是最不愿提起的苦差事之一。父亲对年中吃食大有讲究。早早地查好天气,年前最大的一场雪后,便背着个背篓带着我到田里挖开厚厚的雪层和冰层拔萝卜。
我喜欢吃萝卜,却永远无法爱上拔萝卜这道工序。可父亲有言在先,男孩儿,需得自力更生。所以每至大雪,或是扭捏或是委屈,但父亲身后,我总是屁颠屁颠地跟着,去向萝卜地。
拔萝卜许并不是多惨痛的事,洗萝卜,方才是痛苦之源。父亲对传统的遵循已不是我能理解。冰天雪地里萝卜顺利到家,却远未完事。还未来得及烧壶开水烫烫已然僵硬的双手,父亲便又下达指令——用雪,把萝卜上的泥擦干净。小时候是忍着泪进行的,不懂为何灶上锅里腾腾的热水不能取来用。慢慢长大,父亲解释说,温度一高,萝卜就失了鲜味,不中吃,也不中留。明白个中道理,却还是每每都大不情愿。
唯独,新年开吃,父亲总会难得和颜悦色的往我碗里夹上大大的几块炖萝卜。那种甜到心里的鲜味,未尝过之人,怕是难懂。
只是,这些年,雪渐渐少了,年前求一场大雪,也是并不容易。许是父亲也慢慢老了,佝偻的背影总会蒙上一层落寞。我开始接替父亲,每日期待年前的大雪。味道,竟也是不同了。似乎,再无那份不言而明的痛苦与不情愿。而期待的,也不再仅仅是大年饭桌上的那顿鲜味,还有父子俩相顾相惜的喜悦和快乐。
2
我不懂母亲。
每年年前大扫除,我都不可避免地跟母亲闹矛盾。
母亲保留着太多普通农村妇女的旧习,平时不常在家,一些分歧也难得暴露。而每逢过年大节,回到家里,我和母亲的“大戏”就拦不住的上演。
“这个旧了扔了,放在家里占地。”
“扔什么扔!崭新的!不要钱买啊!”
“这个扔了算了,都是上世纪的款式了。”
“扔扔扔!就知道扔!!过年你姐姐回来也可以应付着用来换洗!你就知道扔!”
如此对话,我俩难得有人退步放行。
年轻人总以为,日子过好了,老东西该淘汰的总该放弃,旧的不去新的难来。而老辈人对于那些沉淀下的事物分外看重,割舍不掉。就拿衣服,我跟母亲不无耐心的解释,咱旧的不要了,每年三套新的,一套穿两年,那也必是足够的。可母亲不以为然,默默的把我手里的旧衣服又收回橱柜,只道“你不懂”。
母亲说,年轻人总有太多的年轻气盛,也有太多的浮华,花花世界看多了,再难懂老辈人奋斗的辛酸。农村人,为了供一个孩子走出山村,不省吃俭用,不处处节省,盯着口袋过日子,那必不行的。
而我总想,如今,苦日子该过去了,虽无大繁盛,小日子总是有条件过的。辛辛苦苦紧巴巴的过了大半辈子,总不能再委屈自己。
每年的母子大戏仍不免俗气的唱着。娘俩能一辈子亲热,拼的不过是一世缘分。树静风止的遗憾我没想过。也许,在我想来,能让活着的人,更幸福一点,就对得起生活。
岁月是挡不住的,但个中欢喜与生活的贫富无关。日子过好了,哪里,都觉得开心。
3
三姐打电话回来,说带小外甥回来过年。
细细算来,大半年没见过小家伙了。
我是家中幺娃,父母算是晚年得子,上有三个姐姐,虽是出生农村,却算是得全家宠爱于一身,没过过想象中的苦日子。幼时总会抱怨农活太多,姐姐们也不过是笑笑,接过我手中的活计,笑说我没过过真正的苦日子。也确是如此,从小,被姐姐们保护的太好。
许是姐弟情感过分深厚,童年的大半记忆,都是姐姐的身影。大姐二姐教我读书写字,小姐读书不多,只在一旁威逼利诱循循导之。大姐嫁人早,一跟爸妈闹矛盾,她婆家便是我最好的避风港湾。二姐读书时最多的给我带糖豆,童年的甜味,大多出自二姐书包。而小姐,总喜欢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絮絮叨叨,看着我写作业。
我时常想,也只有那般简陋的时代和条件,才能有如此简单却乐不可支的幸福欢喜。像是微风细雨,从不动人心魄,却如影随形,让人好不怀念。
时光匆匆,初中,高中,大学,如今,三个姐姐都已成家立业各在一方。想像儿时般厮守定然不可能,也唯有年时,方能短暂的嬉笑说闹。忘了多久没有全家人一起喝杯甜酒烤个糍粑了。小时候四姊弟哄抢油炸的光景,也终是成了一种怀念。
一代人老,一代人长大,又有一代人,开始新生。如今,三姐最小的孩子也到了我童年中的那个年纪。只是,这一辈,兄弟姐妹四五个人,也唯有这年时,方能难得的聚首。
4
奶奶今年九十七岁。严重的老年痴呆已经不容她再记得多几个人。
印象里奶奶对我们姐弟四人有过严厉,有过凶恶,却难得有温暖的回忆。父亲一辈五兄弟姊妹,奶奶向来疼爱老大老二,爱屋及乌,大伯二伯家的小孩在一大家子里自是如鱼得水,好不欢畅。只是,大伯早逝,二伯晚年也不大愿意与奶奶亲近,慢慢的,本可四世同堂坐享天伦的奶奶余年却显孤独。我不懂上辈的家庭恩怨,只知道,父亲终是说服母亲,把奶奶接过来照顾。
有时想想却也恍惚,看着坐在门口就着暖阳昏昏欲睡的奶奶,全然没了往昔的凌厉与张牙舞爪。只是每每出门,奶奶总是温言温语的说:“孙啊,早些回来,天不好,要早些回来。”
大年三十,母亲照往年给奶奶沐浴更衣清洗。年夜饭桌上,母亲扶奶奶坐在上席。奶奶精神矍铄,似沾染这新年的喜气,满是皱纹的脸上欢笑不断。
“真的是麻烦了,要你们为我操劳来去。好人会有好报,你一定会多子多福,儿孙满堂。”饭桌上,奶奶握着母亲的手,突然这么说到。
亲愣愣的看着,为奶奶夹菜的筷子不觉抖开。
“这么多年来,也是你娘第一次夸我……”看着父亲,母亲哽咽,像是委屈,也像是怨言。
全桌沉寂,只有奶奶不明所谓的依旧微笑。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妈,现在,都好了。”
“外婆,吃饭饭……”小外甥在母亲身侧,似懂非懂。
是啊,现在都好了。是非过错,都该烟消云散了。人在,就都好。
5
而我,却不知该说什么了。
过年,在中国人的传统记忆里,其意义更显得格外的的重要。每至年末,个个心生欢喜满是期待。也许是期待一顿年迈父母下厨张罗的饭菜,也许是翘首一种许久不见的重逢。也许,在等待,给家里家外的长辈,做一个长揖道句万福。兴许,也是期待,期待只有过年才有的,那并不如何厚重的红包。
也许,慢慢的,年味,真的淡了。但,当庆幸,人情尚浓。
6
时间催人老,哪个不白头。余年当牵手,十指把家扣。
李小岗,1992年生于湖南邵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沙市作协青年文学讲习班第一届学员,公开发表作品若干。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