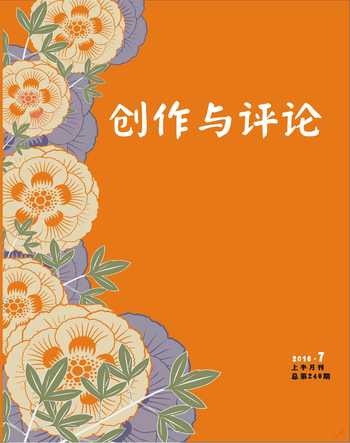时与度
子时(23时-1 时)
子时的变化,似乎是能听到的。子时里面有着隐隐的改革意味。当时间刚步入子时,我分明感受到了那便是子时,那应该就是子时。子时的我听到了窗外的风击打着一些树木的声音,那是寂静的一种。屋外,那里有一些古老的树木,那是一些被无意间保留下来的树木,它们竟然逃脱了改革的斧痕,这让我感到有点吃惊。父亲经常对我说:每到子时,风声便呼呼叫着。
子时,这似乎并不是值得记忆的时间,子时本应是睡觉的时间。但这一天我感到异常清醒,那时我的脑海里出现的竟然是疾病的问题,以及与一些疾病相关的人。这样的表达,往往会给人矫情和不可理喻的感觉,这里我要为自己辩解,那时我脑海里确确实实想的就是那样,我就那样矫情地想到了疾病以及与疾病相关的人。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并不是单单在子时入侵那些民间,疾病在任何时间入侵那些民间。疾病也在改革着民间。子时的风声,继续呼呼吹着。子时只有我,子时没有一个能看透我心思的人与我对视,子时的我应该收获了我所想要的寂静,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乡野,这里的田园牧歌是一种对比式的田园牧歌,自然世界的寂静,酣睡的人群,连呼噜声都听不到,只听到风声、夜鸟声、夜虫声、植物声。寂静,似乎就不再有强烈的改革味道。改革弱化,改革淡化,疾病暂时淡去。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出生地。我必须要交代一下自己所在的地域。我的出生地,古树已经很少,但现在有如火如荼的核桃树,我曾经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核桃树的种植,而嫁接的活基本都是我父亲做。嫁接是一次改革。出生地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改革,出生地必须要遭受那样的改革。但对于古树的砍伐,是我所无法真正能够承受的改革。出生地的许多人都参与了砍伐古树,现在依然如此。出生地在改革潮流中,还没能真正找到既能保护古树又不会影响生产的方法,人们就那样砍伐,就那样继续砍伐着。寨子里面的很多人,都曾进去过看守所,原因是砍伐了一些古树,像村东的李进了看守所三个月,出来后瘦了二十多斤,性格变得唯唯诺诺,村东有好几个姓李的,有好几个都瘦了二十多斤,好几个姓李的都变得唯唯诺诺,这与他们进去看守所之前完全判若两人。我们都不得不把自己放入改革中。我要改革我自己,如果我无法改革自己的这副皮囊,那我就无法改革自己的思想。如果我无法强行改革自己的思想的话,我就通过借助一些外界的力量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革,也许我最应该借助的是来自自然的改革,自然可以通过洗涤来对思想进行净化,同时对思想老是死板进行改革。也许,改革这个词汇同样具有其粗暴的一面,也许,应该用一些柔软一些的词汇,同时也是柔软一些的方式,对思想进行重塑。而自然应该就是一个最为恰当的方式。就像子时的寂静。寂静的子时,粗暴消退的子时。也许,我们许多人都需要一些柔软些的方式来对自己进行改革,或者用一个最为柔软的方式来改变,毕竟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需要重新审视和重塑。我一直以为人们只是生活于生活的表象,子时的我开始觉得实则不是这样,人们经常要遭受来自生活表象的冲击,进而对灵魂进行改革,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与快乐,都是如此。
子时,我正在努力完成对于自己的改革,我乐于被改革,我乐于被自然的寂静改革。
丑时(1时-3 时)
丑时是一个可以把信仰真正袒露的时间。丑时,某户人家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个祭祀活动。他们举行那个祭祀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家里死了一些牲畜,同时走失了一些牲畜。那样的死亡和走失发生在了一个月之间。这样的死亡和走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地域里,同样发生过类似的死亡和走失,但那是属于人的死亡和走失,在那个地域,一个村寨把村寨封起,禁止外地人进入那个村寨,举行了七天左右的祭祀活动,在那七天时间里,他们要祭祀自己的山神、树神、水神……那一家人同样要祭祀自己的一切神灵。万物有灵的观念,在丑时得到延续。那是已经延续了千百年的祭祀活动。那个巫师这样对那家人说,自己的言说也是延续着千百年的言说,那家人是听不懂的,我也曾在某个夜晚的睡眼惺忪中听到了那种安魂的声音,但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父亲母亲也一句听不懂,虽然我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我分明能感受到父母眼里那种由内心的虔诚油然生出的信任。那家人需要安魂,我同样也需要安魂。我一直在自己的文字如是说。
宗教。我们已经无法离开宗教的濡染,我们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是那样,我们不排斥,有些时间里,我们还会信,但我们并不是宗教的狂热者,我们并不是极端的宗教主义者,我们以很平和的姿态面对宗教。平和,平衡,和平,和谐,一些词语可以在这样的情境下,得到派生繁衍,毕竟我们所要追寻的是一种很安心的心灵。我们的宗教的形式,同样朴素简单。我们的宗教在成为真实的物时,这些物基本都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本身就具有化人的作用,风化人,雨化人,自然化人。当被自然感化后的宗教再去感化人的话,人早已是在双重或多重的宗教中,做着所谓修行的事情。许多人拥有宗教,是为了修行。许多人心里面有所相信,是为了修行。许多人修行是为了能在安魂,为自己安魂的同时,也为别人安魂。当原始的宗教形式遭到破坏遭到歪曲后,原始宗教那种由原始的心灵(更准确些应该是原初的心灵,没有遭受污染,被大自然不断净化的心灵)所组成的自然世界,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一片真正属于自然的寂静的森林了!众多样式的宗教形式,在那些民间存活的话,一些东西可能就会得到存活,诸如哪怕是一小片的寂静,哪怕是用我们正常的听力所无法听到的寂静。在潞江坝的某一处,某个江岸上还有一小片原始森林,那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与一小片寂静的存在一样是很匪夷所思的,但可以把它简单地归结到宗教上,许多人也就开始相信了一小片寂静存在的合理了。在那片原始森林里必将也能拥有着一片寂静,这样的寂静属于自然万物,自然界的声音,无论是分贝有多高,它都是寂静的。这与人类世界所制造的喧嚣不一样,世界的喧嚣往往会让人变得更加喧嚣,而自然的喧嚣往往能让人变得更加安静。我在出生地也好,在潞江坝也好,我热衷于自然界,但我会毫不犹豫地先观察一个地域的植被,然后再去关注那个地域的人与生活。在我的出生地,在云南大地,或者可以再把这个空间扩大,当生活在一个具有强烈的空间感和时间感的世界里,我看到了自然在成为宗教样式的同时,同时自然也包裹了众多的宗教样式以及信教的人,似乎没有自然世界的存在,许多宗教样式的存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就会变得徒留躯壳而已。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宗教,那些柔和些的宗教往往源自自然。丑时,大部分人已经沉睡,这时在一些地域,只剩下自然世界的某些部分是醒着的,醒着的自然世界,醒着的寂静,醒着的宗教,以及醒着的信仰。
寅时(3时-5 时)
寅时的我有一种强烈的荒芜感。灵魂的荒芜。内心的荒芜。大地的荒芜。荒芜的大地上,如果长出一些丰茂的草,荒芜便消失,荒芜就变得丰腴。寅时的我,灵魂就是一片荒芜的大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睡觉,但不做梦,我长时间处于梦的荒芜与虚空之中。而在这天的寅时,我睡觉,做了一些梦,噩梦连连,鲜血淋漓。噩梦,可能与脑神经衰弱有关,也有可能未必。
灵魂渴求自由。但并不是任意的自由,以及泛滥的自由。那些噩梦,似乎是有一点点启示性的东西。许多噩梦基本都是关于追逐的梦,我基本都是那个被追逐的人,我几乎就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或者我反抗的手段基本就是一种。逃跑,是我反抗的方式,我要抗拒那些所谓鲜血淋漓的场,我要远离那些场,我要避免成为那些场中的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成为一具尸体,也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自由,也可能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灵魂,也可能就意味着灵魂即将到处飘荡流浪。我要避免成为一具尸体,我要让肉身和灵魂达到某种程度和意义的和谐。但寅时的我,并不依靠宗教,我将依靠噩梦中的那些绚丽的大地,那些繁茂的大地。
卯时(5时-7 时)
自然。自然万物开始在这卯时醒来,某些自然万物又在卯时沉睡。醒来的自然。沉睡的自然。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自然。听得见与听不见的自然。一只猫头鹰开始沉沉睡去,它真正入睡的时间可能是五点,可能是六点,也可能是七点。我的父亲在刚步入卯时时便醒了,父亲说几乎每天早上,他都在卯时醒了。卯时,在父亲的表述中异常准确。卯时,一些鸟开始鸣叫,一些鸡也开始鸣叫,它们看到了亮光,卯时正是光亮不断酝酿并最终凸显的时间段。火塘再次被父亲点燃。父亲开始在火塘边抽醒来后的第一根烟。我总觉得父亲应该多睡一会才是。特别是那些寒冷的冬日。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叹了口气说是睡不着了。父亲要熬过卯时,才能通过干活来消解许多无聊孤独的时间。醒来的父亲。醒来的火塘。以及醒来的孤独。这与醒来的自然是不一样的,醒来的自然往往是喧闹的,那些喧闹至少能把孤独弱化。是在卯时,我在火塘的亮光中醒来,火塘于我们而言也是神灵,毕竟神灵给我们带来光亮以及温暖。我穿好衣服,来到屋外,冰冷异常。一些鸟类是开始叫着了,但只是断断续续地叫着。抬头就是月亮以及星辰,星辰被月亮的光所遮蔽,群山泛出浑浊的影子,但只是群山绵延的影子,群山的内部尤其在夜间无法穿透。黑夜,确实很好。于父亲而言,于我而言都很好,只是于父亲,到了卯时,父亲的黑夜便消失了,那时开始的黑夜于父亲而言,不再具有任何撼人心魂的东西,也许父亲是感觉到了卯时的冰冷才逼迫着自己起来,并借助于火塘来抗拒冰冷。我是发现了卯时的黑夜依然具有震撼人的美,特别是自然的寂静在卯时所给人带来的震动,那是在那之前我所不曾感受过的。
辰时(7时-9 时)
我随着自然醒来。再睡一觉吧!再做一个梦吧!我梦到自己成为了那些伟大释梦者的一员,我看着一个病怏怏的人,我不用问他,我就知道他也一定是被噩梦缠上了,还因为是爱情,还因为是自然……
我梦见了属于我的大地河流。我的大地河流,永远不是类化的,而是有着原初意味的迥异与特质。那是通过人们的口得到流传的大地河流,那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亲眼看见的大地河流。美好的大地到底在哪里?我把自己分解成一些碎片,在天地间随意飘荡,我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大地。我在辰时的某一刻醒来,我花一点时间,我的腰里别着一把刀,拿着绳子,朝大地深处走去,我要渡过一条河,我要背一捆柴回来。辰时,我见到了属于我的大地河流。我是幸运的。未必所有的人都能拥有一片大地一条河流。我在许多大地上到处行走,我一次又一次渡过那条属于我的河流。即便这样的行走不是有意为之,但已经足够。我的大地从广阔辽远,逐渐缩减,甚至缩减为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纹络里,布满通往大地的路径。叶子表面的线条,便是通向大地深处的路。那些纹络通向明晰的同时,还通向未知。我一次又一次地通向未知。歇斯底里经常会驱使我做出在别人看来有点神经质的事情。我到处行走,在许多人看来那是无所事事。在行走过程中,我见到了许多双惊异的目光,有探寻,有不解,有鄙夷。辰时,我的大地,是与那些庄稼人不一样的,他们的大地似乎只是那些庄稼地,他们几乎不去关注与庄稼无关的事物,除了那些因为影响庄稼长势要被除掉的植物。曾经在出生地我扛了把锄头,跟着母亲,烈日当空,汗水接连滴落,我的任务同样是锄草,但不能伤及庄稼,玉米是柔弱的,豆藤是柔弱的,我小心翼翼。而现在我不需要担心庄稼……
辰时。我还没有真正醒来。
巳时(9时-11 时)
哲学。时间的哲学。生存的哲学。自然的哲学。当把自己抛入一片密林(一片密林便代表了理想的自然,真正的自然就应该是有一片密林作为支撑,如果是一片原始的密林就更好,毕竟一片我们无法洞穿其中的密林里面囊括了许多东西,而人可能就会少点,少了一点人烟,也便少了一点过度以及泛滥的欲望,也才有可能有那种最为原始的让人动人的寂静)中,就会真正感觉到时间。时间在一片密林里面有了质感,时间在自然境地中真实存在着。一种属于自然世界的生存哲学,就在一片密林里面开始发生,并以自然的方式终结,或者至始至终都从未终结。但在自然世界里,我们所能感受到更多的是生的开始。在一片密林里,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时间是模糊的,时间可以属于过去,时间可以属于现在,时间甚至都可以属于未来。在一片原始的密林里面,似乎看不到时间要消失的样子。就像这天巳时的我,肚子并不饥饿,当我走出户外之后,发现的竟然与自己所想象的情景不一样,我那关于时间的观念在我的出生地瞬间就被击垮,我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时间观,我在这里看不到出生地的过去(许多人都曾经提起过过去的出生地也是一片密林),我只看到了现在(冬天的萧索,树叶的枯落,大地的荒凉,这样的萧索、枯落与荒凉是会让人莫名感伤的,这天巳时的我很感伤。巳时的我以为出生地的过去就是这样,巳时的我以为出生地的未来也是这样),我感觉很难看到出生地的以后(以后是一个时间不断得到繁衍伸展的概念)。巳时的我需要关于时间的哲学,同样需要生存的哲学(也许,我甚至可以把个人的生存扩大化,可能本来我只是重视自己个人化个性化的生存,但我想略微夸大一些地说是在思考一群人的生存,或者是一个地域的生存,该如何才能更好地生存,该如何才能真正体会到自然的寂静?这样的问题不停困扰着我,也同样困扰着那些民间。但让我略微感到吃惊的是,那些民间的许多人并没有因这样的问题而显得很焦虑,相反是很平静地面对这些问题,当然其中也是有一些粗暴地面对着这些问题的人。在我的生存哲学中,或者应该是从自然的哲学中所收获的并不是粗暴,而是和谐与平和)。巳时的我,暂时离开了家,我想进入某片密林中,但当我走到路口,见到一群扑棱着翅膀的鸡时,我才发现确确实实是没有密林的,至少在巳时的我是无法见到真正密林的。
午时(11时-13 时)
村寨是有历史的:有活的历史,像那些老人;也有成为物的历史,像那块记载着村寨最早的族谱的墓碑。历史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着。当老人离世,当墓碑消失,当别的那些形式消失,村寨还应该拥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于一个村寨,于一个村寨里的人,是重要的。
未时(13时-15 时)
未时的我假寐,胡思乱想。未时,应该有很多人关注着时间。那些放牧的人,以及那些被放牧的牲畜,一步入未时,当意识到时间将逝对于双方的意义,都显得急匆匆的样子。也许,慵懒惬意的时间往往是属于还未步入未时的时间。
申时(15时-17 时)
乡愁消失。申时的我,感觉到那种伤感与愁苦的东西逐渐远离了我,乡愁的消失意味着的是松弛、不猜疑、不感伤。即便眼前的大地,较之别的季节更加显得苍凉如暮,但照样可以起到安抚人的作用,这便是原乡的作用。在面对原乡的时候,即便再有那么浓烈的乡愁也会暂时消失。我有属于我的乡愁,面对着一个许多本应该井然有序的世界,特别是人们内心世界本应该是井然有序的世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世界时,乡愁就会诞生,乡愁就会加剧,乡愁就会异化。
这天申时的我,出现在了那片荒凉的大地之上。帕后出现在了那片荒凉的大地之上。帕后,是小名,年纪很小,眼睛纯净,她一个人在那里嬉戏玩耍,大地之上只有一棵粗壮的古木,古木旁边是一个孤独的庙宇,帕后也是孤独的吗?也许,帕后并不孤独,假如帕后是孤独的,那她应该去找别的同伴们,但帕后并没有去找她的伙伴们。我来到了帕后的旁边,我才发现那时的帕后真的并不孤独,帕后正在观察着一群蚂蚁。大地之上行走的蚂蚁,对于大地而言,那片大地已经足够宏阔,那些还有一些枯索的草和灌木,那样的草与灌木对于那些蚂蚁而言也已经足够组成一片密林。帕后呆呆地看着一只又一只蚂蚁从那块石头的缝隙处爬入到石头底下,帕后呆呆地注视着一只又一只蚂蚁躲在某棵草下面乘凉,申时的帕后和我正感觉随着时间的缓缓流淌日光也正在变弱,那一只又一只蚂蚁也不再攀附着那些草,它们开始浩浩荡荡地朝那块石头走去,如果把那些蚂蚁换成是人,浩浩荡荡的人群将把那片荒凉的大地填满,并用人的数量来制造出大地其实并不荒凉之类的错觉。而帕后和我看到了局部和细节的不荒凉,或者只是属于蚂蚁与别的一些微小动物的不荒凉而已。我忘了交代帕后和我两个人观察那些蚂蚁时的姿态了,那时的帕后和我都是蹲着看着那些蚂蚁的,帕后叫了我一声,我也叫了帕后一声,后面的时间我们基本都不说话,我们似乎都是在感受着属于大地的寂静,可能更准确些应该是大地的喧闹。帕后,很留意那些蚂蚁,我先回去了,好的,帕后的声音充满童稚,那是属于童年的声音,我的声音喑哑,那是属于成年人的声音,对比,产生了对比。申时即将过去,我也要暂时换个地方。移步换景。有多少意义?
酉时(17时-19 时)
酉时的我出现了某个古老的建筑面前,那是一座庙宇,古老的庙宇。某个古老的建筑,或者那不能属于古老,毕竟那个建筑才建起有四五十年的样子。在那个古老的建筑的古老的门上,我看到了虫蛀的图案。虫蛀。齿痕。初看以为是古老的图案,或者这本身就是古老的图案,只是制作图案的不是人而已。古老的村寨,古老的图腾崇拜(有许多个建筑上有某种动物的图案),古老的文化,在战战兢兢之中的保留与坚守。在那里,许多建筑,似乎只有旧,但又不是,就像那棵古树,它散发出来的是生的力量,经久不息的生的力量。文化不能强植。遮蔽。不为所知。但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到那种不为人知的角落,除非那是没有人所想保留的事物。
村庄。建筑。古老的文明以及白族的元素、汉文化的元素、旧文明的元素(标语),新文明的元素(依然是标语),这些标语在释放着一些改革的讯息,古老的建筑和文明和文化也在经受着改革,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着变革,在一些民间,已经很难再见到那种属于最传统的东西,只有一些人还在坚守着,他们正以被别人认为保守的姿态在坚守着。
戌时(19时-21 时)
这一刻我想化身为巫师。一个在夜间行走的巫师。许多巫师都是在夜间行走的。当然也是有那么一些不分白天黑夜到处行走的巫师。我见到过许多巫师,当我想化身为巫师时,我把那些曾经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些巫师进行了重新审视:一个骑着白马的巫师,风度翩翩,白马风度翩翩,马的鬃毛在风的撩拨下撩拨着像某片草野中摇曳的茅草;一个与村寨中的那些妇女没有任何区别的女巫师,她背着一个绣着花的包,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一个臃肿肥胖的巫师,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任何羞赧之意地跳着舞蹈,也许那时巫师觉得自己的舞蹈很美,也可能它觉得自己的舞蹈很糟糕,但那些仪式中是不能缺乏那样的舞蹈的……戌时在缓缓流淌的过程中,我开始改变主意,那些巫师形象都不是我理想之中的形象。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巫师对于那个民间的误读,对于人的误读,对于人所造成的极其不好的以影响。
我看到了河流死亡的一些方式。戌时的我似乎也听到了几种河流死亡的方式。而在巫师眼中,河流究竟有多少种死亡的方式呢?这是我特别想了解的。也许,在他们看来,河流之神的消亡,便是河流的死亡,没有魂魄的依存,最多也只能是一个空壳。我把自己暂时设想成一个举行招魂仪式的巫师。我需要一种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里应该有着河流一般的低唱或怒吼。曾经,我认真地听着那个巫师驱鬼时的调子,似乎只是内容不一样,而调子是一样的。戌时的我,用的就是那种古老的招魂调子。我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巫师。也许,我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装神弄鬼的一般巫师而已。我以自己的方式,为一条河流招魂。我想象着自己是这样为一条河流招魂:
喂!河流之神,快回来!
喂!大地之神,快回来!
喂!滋生童话传说的河流,快回来!
……
这里的“喂”,被拖得长长的,还要有声嘶力竭的意味。我手中还要拿面铜镜,我曾见到许多男巫师的衣兜里,都有一面铜镜;我还要骑一匹白马,曾经我也见到过一个男巫师骑着匹白马,在滇西北的大地上卷起一阵又一阵的尘土;我手里还要拿一些香,原料是松柏,烟雾缭绕,香味沁人心脾;我的身上还要有一些纹身,这样我才能借助万物之神的力量,来对抗现实的污浊;我手里还应该拿个盘子,里面放置着一些熟食(异常丰富,有肉,有米饭),一杯茶,一杯酒。我用纠结且略微悲切的声音,在那些河谷大地里喊着。我拿着那些东西,经过一条铁索桥,或者是从一个溜索上滑过,强烈的晕眩感差点就把我击垮。我在那些古老的桥墩旁,跪了下来,点燃香,倒一点茶,再倒一点酒,再撒些熟食,然后开始念念有词。我的声音应该如泣如诉如歌,开始低沉缓慢,渐渐地变得迅疾,最终成为撕心裂肺的嘶叫。“喂……”我听到了拖得足够长,与那个河谷里的回音相互碰撞在一起,相互补充着。我的周围,应该是一些虔诚的人。但我又分明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怀疑,他们眼中透露出的不信任,他们神色鄙夷,他们跑着冲着经过了铁索桥,他们一溜烟从溜索上滑过,嘴里学着我的喊叫声,“喂……”我顿时成了一个小丑。难道,我就这样被人们抛弃?难道最终,巫师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被人们抛弃?
在我的念念有词中,我分析着河流变小的原因。也许那些人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把大部分的原因,归结到他们头上。我听到了那些离开我的人们的说话声,“我们便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这样,我们还能生存得下去吗!”在滇西北的怒江边,澜沧江边,有许多人依然是靠山吃山,他们定义的农耕文明,依然是以毁林开荒为代价的。我在一些地方走访调查时,看到了人们把一棵树木伐倒的同时,还把那棵树的根挖出了,据说那些树根可以卖给别人做根雕,价格不菲。我的招魂仪式里,有着赤裸裸地直面,听众可能就很难接受。以前许多的招魂仪式所面对的,都往往不是真实的世界,或者往往不是现实世界之内的事物。而现在的我,竟然想把人们拖入真实世界。我看到了人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时,表现出了以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回到现实,准确一点应该是走出巫师的世界,走出信仰的世界,来观望这个世界。我不再是一个巫师、当把独属于一个地域的信仰剔除,就像是把骨头上的肉剔除,那就只是一个骨头,那时,很多骨头都是相似的,最多只能分辨出是羊的骨头,马的骨头,牛的骨头而已,有时甚至连属于哪些动物的骨头,都无法分辨出来。现在,云南大地的许多个角落,那些有异质的事物正慢慢被剔除。世界的许多个角落,最终将沦为一个角落。在这个地域,幸好还有那些幸存的巫师,还有那些幸存的多种民族语言,还有一些人身上的民族服饰,还有一些独属于这个地域的日常生活。这些符号,依然在支撑一个世界。我一开始出现在这个地域时,看到的只是那些植物世界与以往经验间的迥异。从语言开始,从音乐开始,从腔调开始真正深入一个地域的符号。许多民间的歌者,与那些我所见到的巫师很相似,是太相似了。他们用深情,有时还是沙哑的声音唱着对大地的爱与忧。这些歌者,是另外一种巫师,巫师被我的含糊丰富,也许,某一天,我也可能会成为某一种巫师。有时我会矫情地希望,自己的文字是在举行一场又一场招魂仪式,而招魂的对象是那些受到工业社会惊吓的万物之神!戌时的我最想成为的原来是民间的歌者。一个真正立身于大地之上的民间艺人。
当戌时接近尾声,我又想化身为一个巫师。一个并不高深的巫师,一个只是对人类思想进行一定塑造的巫师,我的存在只是一种警示,而非其他。我将不是任何有恶意的巫师,我要成为一个对天地负责的巫师。
亥时(21时-23 时)
闭上眼睛,我必须要早点沉睡,我必须要彻底放空自己,也只有这样,噩梦才会远离我,也才可能那些自然、一些雪、一些被雪覆盖的密林才会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出现在我脑海与出现在我面前是一样的,就像看到鸟儿飞过一样,当脑海以及梦乡被这样的物事填充,亥时的我才会远离那些莫名的伤感,似乎我的伤感都是矫情的,似乎我一直害怕被别人认为是矫情的,而其实我不用去这样介意别人的看法,我应该只需要介意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角色,以及自己从自然界中所收获的东西,我收获了许多让人诧异的东西,鸟儿飞过,一场风卷来,一场雪降临,我的梦乡将被大雪遮掩充斥。闭上眼睛,或者我不用那么早就沉睡,我可以在那个静谧的夜晚把自己的所有听力都打开,我可能会听到那只在我的亲眼目睹下沉睡的猫头鹰在夜间再次发出的声响,我可能会听到月光洒落在屋外那些草叶上面的声音,我也可能会听到亥时霜就开始降落的声音。我真就静静闭上了眼睛,我的脑海里面果真是一片空白,那些曾经预见的声音开始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开始填充我的脑海,我的脑海不再是贫瘠的,而是开始变得富足丰厚。首先有了一片茅草地(茅草地是实实在在的,不再是隐喻,我能清晰地说出那片茅草地所在的位置),一阵风袭来,是柔风(在那种凶猛异常的烈风来临时,我不曾在那片茅草地出现过),茅草摇曳,一棵茅草摇曳,一片茅草开始摇曳,那是异常壮观的摇曳,我牵着一匹白马,那个巫师骑着一匹白马,我们都出现在了那片茅草地,那个巫师诡异地朝我笑了笑,我诡异地就出现在了那个巫师面前,那个巫师从怀里掏出了一面铜镜,他用力擦了擦镜面,然后让我看了一眼,就一眼,说实话我还没有真正看够呢,而他就那样迅疾地收了回去,这回他诡异地笑着的同时还诡异地问我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那时我根本无法肯定的问题,我本应该看得很清楚才对,那时我的眼睛纯净灵敏,但似乎我只是看到了层叠的茅草以及层叠的两匹白马。那个巫师竟然跟我说,你看到的是神?难道一片茅草地就是神?难道两匹白马都是神?
子时(23时—1时)
又到子时,时间依然在变化着。
时。时间。
度。思考。
时间思考。思考时间。
……
李达伟,白族,1986年生,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大理。已在《民族文学》《文学界》《清明》《青春》《散文选刊》(上半月)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作品七十余万字,有长篇散文《隐秘的旧城》和《潞江坝书》。长篇系列散文《暗世界》获2014年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曾获滇西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 曹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