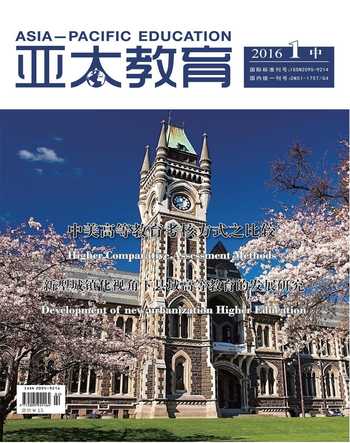混杂环境下的挣扎
王芳 余兴红
摘 要:克里奥尔一词源于西班牙语Criollo,原意为“血统和文化混血”。目前欧美学界对克里奥尔有两种不同的理解。criollo指的是一种语言形式,这种语言接近土话和“民族语言”,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破碎的或近似系统的语言。Criollo通常用于指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欧洲人后裔,对这些人有许多不同的叫法:克里奥尔人、欧洲克里奥尔人、“红腿子”等。埃拉.柏林用“大西洋克里奥尔”这个词指称“那些凭借出生、经验或选择而成为一种文化组成部分的人们,这种文化从16世纪开始在大西洋沿岸——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兴起。”西印度群岛英语作家里斯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小说《藻海无边》就反应了这种克里奥尔文化现象。本文尝试论述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困惑。
关键词:克里奥尔人;安托瓦内特;身份;混杂
目前,已有不少针对《藻海无边》中女主角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本文结合西印度克里奥尔人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安托瓦内特的家庭混杂现象与混乱的精神现象对她的身份探索的影响。相比于前面的研究,本文把关注点集中在安托瓦内特生存环境的“混杂”与精神状态的“混乱”上。要强调的是,本文不仅强调安托瓦内特作为被排挤的“边缘人”的困惑,也突出了其他研究未涉及到的她的白人意识。
一、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人
西印度群岛牙买加的克里奥尔社会起源于欧洲的殖民者和非洲奴隶之间的一系列互动。这个社会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非洲的,而是被称为‘克里奥尔的——这种文化是更广泛的新世界文化综合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定居在加勒比地区的白种克里奥尔人是退化的英国人。虽然在法律上,克里奥尔人和来自母国的人是平等的,实际上,他们遭受到各种歧视。墨西哥诗人弗朗西斯.德.特萨拉的一首诗就充分表达了克里奥尔人的不满:“西班牙,你对那些新来乍到的人,是仁慈的母亲,而待我们却像刻薄的后娘。你慷慨赐予他们珍宝,留给我们的却是困苦和惆怅。”在殖民地,掌握政治权利的绝大部分是来自母国的白人。为获得独立,1790年爆发了黑人奴隶和黑白混血人反对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度的革命,最后广大的印第安人、黑人及混血种人在这场斗争中付出了生命,但是原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但没被触动反被强化了。因此,对于一般的混血人和黑人而言,独立运动是一种变相的骗局,白种克里奥尔人成为他们新的敌人。
二、《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的家庭混杂现象:黑白之间
在《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一直都生活在混杂的家庭环境中。笔者将从原生家庭、再生家庭及安托瓦内特自己的家庭三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安托瓦内特的原生家庭:缺失的父亲、庄园主母亲和弟弟
从文本可知,她的成长过程中缺失了父亲这一角色——他们失去经济支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种植园主,而是被上流社会嘲弄下层民众排挤的克里奥尔遗孤。“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也可理解为,殖民入侵和民族迁移造成殖民地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被殖民者血缘上的父亲在象征意义上已被殖民权力‘阉割而失去相应的权利,从而无法确认主体身份,而父亲地位的下降则又直接导致了民族集体记忆的丧失。”在《藻海无边》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拉非独立运动后,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广大黑人和混血人种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意识到这是掌握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中心的克里奥尔人的“骗局”,反抗力量不断增强,白人种植园主的地位岌岌可危。安托瓦内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问,开始了复杂的探索过程。
与父亲的缺失相反,里斯在《藻海无边》中花了很多笔墨写安托瓦内特和母亲安妮特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的克里奥尔人,安妮特一直不被牙买加的太太小姐看好,在丈夫死后,更是遭受各种冷言冷语。从天堂跌入地狱并没有打消她挽回旧生活的梦想和决心,但是,她在外所受的委屈似乎都被转化成对女儿(酷似自己)的“冷暴力”。在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证据。“谁知她竟把我推开,出手并不粗暴……或者到没人纠缠的地方随意走走,她要安宁,要清净。”这是安托瓦内特对母亲表示关爱所受到的拒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德明认为“母亲形象作为生命的给予者和生命的保护者正处在依附与独立两者的交接点上,母亲就像母国(殖民宗主国)一样,既给被殖民者以保护,又给后者以限制和压抑,这正是殖民/后殖民状况的某种隐喻。”在《藻海无边》中,安妮特既是作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这一角色出现,又是英国这个宗主国的隐喻。安托瓦内特对母亲的多次亲近的失败,也隐喻了她对宗主国试图亲近的惨败。因为,尽管她与这两者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但就是有某种东西在她们之间阻隔着,(在文本中我们可以把弟弟比埃尔看作是阻隔之一)不让她亲近,也不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
(二)安托瓦内特的再生家庭:英国白人父亲与缺失的母亲,友爱的姨妈
安妮特嫁给了英国白人梅森,安托瓦内特有了一个“再生家庭”,成长环境在原生家庭的基础上变得更复杂。
安妮特一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引燃了土著人对他们的仇恨。这毁了他们的家园也让比埃尔断送了的生命,也让安妮特疯掉。安托瓦内特在弟弟比埃尔死后去看望母亲时的,女儿想亲近和安慰母亲的苦心再次遭到拒绝。“我双臂搂住她,吻了她。她紧紧抱住我,我都透不过气来了,……‘不,不,不,说着一把推开我。我摔倒了,撞在隔板上弄痛了。”后来安托瓦内特如是说:“……虽然她还活着,可是我必须当她死了,忘了她,为她祷告。”在此,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开始缺失于她的生活。
和母亲所带来的失落不同,安托瓦内特的姨妈柯拉却弥补了不少缺憾。这位被梅森先生理解为不愿帮助安托瓦内特一家轻薄的女人,总是在默默扮演着一个智慧的、关爱家人的角色。当梅森先生在客厅大肆讲进口劳工计划时,她及时阻挠;在黑人闹事而梅森先生盲目乐观时,她清醒地点明“明天就来不及了……”;当比埃尔被烧伤后,是她冷静处理伤口,作离开决择;在“逃亡”过程中,一直是她以一个保护者的姿态拉着安托瓦内特的手;在安妮不依不饶地想回去带鹦鹉时,是柯拉警醒了她;走在黑人阻挠她们的去路时,“她寸步不让,直盯着他两眼,嗓音镇静地用炼狱烈火来吓唬他,终于逼得黑人让步。在笔者看来,柯拉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安妮特作为母亲和库利布里女主人的责任。她了解库利布里的情况,力图避免矛盾,且在矛盾爆发时冷静处理,还一直陪在安托瓦内特身边弥补缺失的母爱。联系前面引用的“母亲形象的隐喻”,柯拉在此可理解为安托瓦内特提供安全感的美好家园。
可是,家园为安托瓦内特提供的安全感很薄弱。来自母国的白人父亲和哥哥操纵了她的命运。在这个再生家庭中,安托瓦内特与白人父亲和哥哥之间的关系隐喻了殖民地克里奥尔人与宗主国的关系。
梅森先生几乎是在安托瓦内特最难堪的情况下出现在她的家园,对于安托瓦内特而言,梅森先生绝对是一个毫无预警地闯进他们家并引起一系列变化(包括母亲安妮特的重回青春),而且也让他们再次站在黑人反抗风口的陌生的“白人爸爸”。梅森不仅不能理解柯拉姨妈作为克里奥尔人嫁给英国白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和代价,而且不肯试着去理解黑人反抗所能带来的危险。虽说如此,安托瓦内特仍然试图去接纳这样一个继父。为什么要去接纳他?除了他是一家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们要依附于梅森先生,就像殖民地不得不依附宗主国一样,尽管当时大部分拉美地区已经独立。在母亲疯后,安托瓦内特到了进入修道院学习的年纪,梅森先生以继父的身份经常去看望安托瓦内特,并带她去吃饭见朋友,还送她漂亮各种礼物。最后,还要给她邀请英国朋友一起过冬,在安托瓦内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相中“乘龙快婿”。安托瓦内特或许觉察出了一点不妥,但是她只能“又感到惊愕、忧伤惶惑了,憋得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当晚,安托瓦内特小时候的噩梦再次出现。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如是说,“在这种附属与屈从的历史关系中,一切赐予都是单方向的;价值主要是对一方而言的。互相的关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安托瓦内特对梅森先生的接纳或许换来了几年的安稳生活,但最终她还是要离开她的避难所,面对未知的人生了。直接把安托瓦内特推向转折路口的却是她同父异母的兄长理查.梅森。不考虑妹妹的未来,认为她能嫁给一个英国人就已经算是“好福气”,还声称可以“拿性命交托给他”。但是事实证明,他亲手把妹妹推进了深渊并且丝毫不打算拉她一把。再次印证了萨义德“价值主要是对一方而言的”这个说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梅森父子辜负了安托瓦内特对宗主国的认同感。也正是如此,她的身份认同道路又更曲折而又丰富。
(三)安托瓦内特自己的家庭:英国白人丈夫与缺失的自己
在梅森父子的操纵和罗切斯特的甜言蜜语灌溉下,安托瓦内特接受了一桩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婚姻。在处理与罗切斯特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安托瓦内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仅是一个妻子对待丈夫的态度,也代表了她作为一个克里奥尔女性对待宗主国的近亦驱的文化心态。在自己的家庭中,安托瓦内特在混杂中探寻身份并逐渐迷失自我,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彻底崩溃,实现了梦中预示,一把火毁了房子,结束残生。
在她的白人丈夫罗切斯特看来,这场婚姻只是一笔买卖。尽管他的新娘很美,但安托瓦内特只是个可以给自己带来财产却又不合心意陌生人。这恰恰也是宗主国对其殖民地的真实观感——殖民地只是能为自己带来大量财富和增强权力的他方,别无它用。
但是,在安托瓦内特看来,无论是对罗切斯特还是宗主国,她希望能得到认同,几乎是以一种冒险的心态接受这场婚姻。正因如此,她才会在婚前忽然改变主意不愿意嫁,但说唱俱佳的罗切斯特用甜言蜜语把安托瓦内特稳住了,于是安托瓦内特在不自觉间踏进了泥潭。其实,“你对我一点也不了解”不仅指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不了解,也指代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殖民母国对克里奥尔人的不了解。无论是罗切斯特和安托瓦内特之间,还是宗主国与克里奥尔人之间,都存在着一条看似离得很近实际上却深不见底的鸿沟。安托瓦内特的抉择象征着克里奥尔人对母国的一次探险。
不像罗切斯特所想,安托瓦内特从未认为她的婚姻是买卖。她极尽谦卑地维护着他们的婚姻。到达格兰布瓦之后,她努力地想让丈夫喜欢上她最爱的地方。除此之外,她还努力打开心扉,告诉他各种自己从未告诉过别人的心里话。从拿着木棍睡觉才有安全感的事情说起,以及被骂白蟑螂的疑惑,甚至是把母亲发疯的事情全盘托出……其实,安托瓦内特只是为了让罗切斯特了解、理解自己,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托付。同时,这也是以安托瓦内特为代表的克里奥尔人对母国的一种主动亲近。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掺杂着安托瓦内特的种种不安。她曾问罗切斯特“英国当真是个梦吗?”但是罗切斯特反而认为安托瓦内特所拥有的美丽小岛才像梦。两人在罗切斯特想避免麻烦的心态下停止了争论。安托瓦内特的疑问既表明她对遥远的宗主国的不理解,也表达出她对亲近罗切斯特、亲近宗主国所要承担的风险的担忧。对于安托瓦内特而言,英国是充满迷雾,似美梦也似噩梦。而对于罗切斯特而言,西印度群岛绝对是在带给他财富时也剥夺掉他某些重要权力的地方。由于对于痛苦的感受,他选择仇视这个地方。两者的不同态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和宗主国相互之间不可理解的现实。
但在他们婚姻的早期,双方都因不同的理由而选择略过这个不可能得到调解的问题。安托瓦内特在她的探险上显得奋不顾身。在与罗切斯特的聊天中,她开始显现出她的执著,疯狂:“……只要说声死吧,我就死了。你不信我说的?那试试吧,试试吧,说声死吧,我就死给你看。”安托瓦内特的这份疯狂不单单是出于对罗切斯特那冒险式的爱,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接近宗主国寻求身份认同的执著。
但是,当有人跟罗切斯特告密说安托瓦内特家有疯病史时,作为支配者的罗切斯特当认定安托瓦内特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后便开始不屑于逢场作戏,且设计让她一步一步成为“疯女人”。相对于罗切斯特的无情,安托瓦内特则不惜请求克里斯托芬用巫术为她挽回婚姻,而且听取她的建议先对罗切斯特解释“疯母亲”的悲惨经历。但是罗切斯特一句一句地喊她“伯莎”,甚至与仆人阿梅莉发生关系,完全击垮了安托瓦内特。在他们离开格兰布瓦前,她说“对,我没资格。对不起。我不了解你。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不能替你说话……”这既是安托瓦内特对罗切斯特死心的表现,也是她作为克里奥尔人主动亲近宗主国被拒绝后的失落。她刻意忽视差异,努力展示自我,但最后还是不被接纳,不被认同。最后的失落让她认清其实她无论是对罗切斯特或是对英国都是一无所知的,她不仅不能代替两者说话,还不能与他们平等对话。安托瓦内特彻底迷失在身份认同的旋窝中,苦苦挣扎却不得解救。
三、《藻海无边》安托瓦内特的精神混杂现象
作为一个生活在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安托瓦内特一直都是处在黑或白两种身份的缝隙间。她在文本中说过克里奥尔人被称作“白人黑鬼”、“白蟑螂”,这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克里奥尔人的身份困惑。安托瓦内特这类克里奥尔人在寻求身份认同时的心理历程就类似于基督教传统中的林勃意象——地狱边缘那个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的悬置状态——被囚禁在此的鬼魂并非因为犯了什么事,只是因为生在了基督之前。所以他们既不能享受天堂之福也不受地狱之苦,但是他们受着在向往中生活而没有希望的惩罚。
(一)安托瓦内特的白人意识
在面对黑人及混血种人时,安托瓦内特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安托瓦内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克里斯托芬当作是家人一样看待,但她仍会以一个更高的姿态俯视黑人克里斯托芬。如在安托瓦内特去寻求她的帮助以挽回罗切斯特的爱时,她们讨论到了英国。“心想‘这个没知识的死脑筋黑人老婆子,就连有没有英国这么个地方都弄不清,她怎么会知道我最好该怎么办呢?”在离开克里斯托芬的家之前,安托瓦内特甚至怀疑她会出卖自己。这件事情上,不仅说明了安托瓦内特对克里斯托分的不完全信任,无论黑人愿不愿意接纳安托瓦内特所代表的那个族群,作为克里奥尔人的她所具有的白人意识是不可能完全接纳“黑人世界”的。
最后,在安托瓦内特与桑迪的交往中,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个克里奥尔姑娘在文化身份上的自我选择。在桑迪的第一次出场中,安托瓦内特明确交代由于梅森先生的教训,她羞于认自己的混血儿亲戚了。第二次出现则是在安托瓦内特有主见地用石子击打巨蟹后,一笔带过是桑迪教会她而已。最后一次出现则是在桑迪要求安托瓦内特跟他离开时,但是她拒绝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男人求爱的拒绝,也是安托瓦内特这个克里奥尔姑娘对为她展开怀抱的另一个世界的拒绝。同样的,这是她的白人意识在作祟。
(二)被本土文化疏离的安托瓦内特
尽管安托瓦内特不断在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间徘徊,努力寻求认同,但是并不能改变自己作为克里奥尔人被疏离的现状。同时,她亦敏感地觉察自己与他们的区别。
在牙买加的太太小姐看来,对于安托瓦内特的父亲而言,他的续弦安妮特太年轻貌美,与他一点也不般配。更致命的是她是来自马提尼克岛的姑娘。因此,在父亲去世后,她们根本不再往来。甚至在安妮特与梅森先生的婚礼中嚼是非,不看好他们。对此,安托瓦内特清楚地明白作为克里奥尔人,他们与白人从不会同舟共济。
对于白人父亲梅森,安托瓦内特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隔膜,并知道他不能理解她们。因为他只相信自己所想的,所认同的,没有人能改变他的观点。作为从宗主国来的西方白人,他与母国一样,习惯用一套固定的修辞来理解殖民地/边缘世界。这些修辞“都是宣言性的,不言自明的;它们使用的时态是无时间的永恒态;它给人的印象是重复和力量;它们总是与欧洲的同类物——有的时候被点明,有的时候没有被点明——相对称,然而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对所有这些功能进行描述时,经常只需使用一个简单的系词:是。”对于梅森先生来说,他的奴仆们是“黑鬼”,是“懒得出奇,不会惹出事”的人,所以根本无需去担心黑人反抗的发生,更不用愁着该怎么对抗。因此,安妮特和柯拉姨妈的劝说都是杞人忧天。他始终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西方殖民者亲临边缘世界的姿态来处理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除去感受到与梅森的不同之外,安托瓦内特还明显地感受到了英国这个母国与自己的区别——与她在这个混杂的家庭感受到的一样,虽然她与梅森先生已是是一家人,可是差异使得他们之间无法靠近,表面的完整并不能弥补碎片间的缝隙。
与蒂亚在水中翻跟斗的打赌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托瓦内特这个试图融入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尝到了委屈失落的味道。但是,真正的失望要算在离开库利布里前所受的一击。“我看见蒂亚和她母亲,我朝她跑去,因为她曾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只剩下她了……只见她手里有块带尖棱的石头……我们互相瞪着,我脸上有血,她脸上有泪。就像看到了自己。像镜子里一样。”这也代表着安托瓦内特企图从蒂亚身上寻求身份认同的希望的落空,她无法在白人世界找到认同,也无法在黑人世界找到。不同的是,代表黑人的蒂亚与安托瓦内特一样,是遍体鳞伤的。似乎在说明一个道理,对抗,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克里奥尔人的安托瓦内特是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代表的族群与黑人和混血人种之间是存在着比表面肤色看来更大的差异和分歧的。她不属于黑人抑或是黑白混血人种的任何一类。但另一方面,但是但在另一方面,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都没有选择她,她也没有选择它们。与《无名的裘德》这部小说所嘲弄的一样,你所期望的东西正好是你得不到的。
参考文献:
[1]张德明著.《流散族群的身份构建: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6.
[2]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
[3]〔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
[4]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Latin America history》,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104页.
[5]〔英〕简里.斯著《藻海无边》,陈良延,刘文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1页.
[6]王涛,陈红梅《〈藻海无边〉中镜像技巧的运用——女主人公之身份探讨》,《南京林业大学报》,2008年3月,第8版第1期.
[7]朱云《〈藻海无边〉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困境与主体意识的丧失》,《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8卷第5期.
[8]张德明.《〈藻海无边〉的身份意识与叙事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