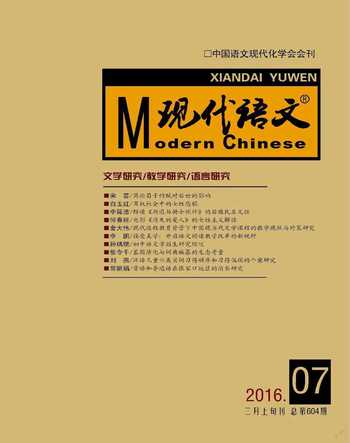师陀小说研究述评
摘 要:作为文坛的多面手,师陀曾创作出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但其创作数量最多的体裁是小说。而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镇,师陀的研究经历了由被发现、到被搁浅、到再度被热评的80年。本文拟以师陀小说为切入点,力图梳理、探究师陀研究80年的浮沉历程,并试图归纳每一阶段的研究特点。
关键词:师陀 小说研究 述评 阶段特点
师陀即芦焚,原名王长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中,师陀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鲜明的文化品格标举于文坛。作为文坛的多面手,他曾涉猎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多种体裁的创作,共计271篇文学作品。但他用力最勤、同时也受研究者广为关注的还是其小说方面的创作。
1937年,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戏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从此,师陀的小说开始进入更多评论家的视野。
一、建国前的小说评论:散点式和感悟式批评
师陀的小说创作多集中于三四十年代,因而在建国前的三四十年代也曾一度出现师陀小说研究的热潮。由于当时评论家各自的独特个性和不同的关注点,这个时期的小说评论呈现出散点式的特点,即没有出现集中针对某一作品的评论与研究的现象。同时,这个时期的小说评论多带有评论家本人的感悟,即感性评论多于理性分析,因而这个时期的小说评论也具有感悟式批评的特点。
根据现有资料,这个时期关于师陀(芦焚)的小说研究共六篇,皆以书评的形式出现。[1]并且,这六篇评论文章的发表时间集中在1936年——1937年。它们分别是:李影心评《谷》、刘西渭(李健吾)《读<里门拾记>》、杨刚《里门拾记》、孟实(朱光潜)《<谷>和<落日光>》、王任叔《评<谷>及其他》和汪金丁《论芦焚的<谷>》。
李影心的《谷》原载于1936年8月2日《大公报·文艺》。在这篇文章中李影心肯定了师陀在文字表现技巧上的努力,她认为“《谷》的作者有一种特出的风格,使创作永远保持着清新的生机,现在我们愿说,亦是那特出的风格,支配了通篇创作色调的一贯。”杨刚在《里门拾记》(原载于1937年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里,则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十二个短篇装成了这个集子,看书名,就知道作者心里有着了他那‘大野上的村落,和大野后面的荒烟”。“里门拾记是辛酸的,哭哭笑笑的,但也掩盖不了它字里面的和善,那使他在恶骂的时候并不见出刀笔;以及他自来自去无所依赖的笔锋,那初读来,令人想到鲁迅,细究究,却以为鲁迅近于宫笔,芦焚则滃云点染,取其神似而已”[2]。在这里,杨刚将师陀与鲁迅齐名,更确切来讲,是看出了师陀作品和鲁迅作品的神似之处。除了对师陀作品思想内涵的褒扬之外,杨刚同时也肯定了师陀运用文字技巧的能力。“芦焚不在颜色上做功夫,也不好作比喻。偶书几笔,似乎特意避免用譬喻,全赖景物自身的色象传达它本质的美”[2]。此外,杨刚还针对《里门拾记》里的一些具体篇目给出了自己的感悟、判断。
在杨刚发表《里门拾记》的同一时期,也有一位学者关注到了《里门拾记》的艺术价值,他就是刘西渭(李健吾)。刘西渭的《读<里门拾记>》原载于1937年6月1日的《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刘西渭便以一位批评家的敏锐视角迅速捕捉到《里门拾记》和《老残游记》、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及艾芜先生的《南游记》的相似与独特之处。接着,刘西渭将师陀和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两相对照。他认为“沈从文先生和芦焚先生都从事于织绘。他们明了文章的效果,他们用心追求表现的美好。他们尤其晓得文章不是词藻,而是生活。”[3]而针对师陀的写作特征,刘西渭则深入肌理地指出“讽刺是芦焚先生的第二个特征,一个基本的成分,而诗意是他的第一个特征,一件外在的衣饰”,“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3]而谈到师陀本人,刘西渭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风格的欣赏:“我记得第一次芦焚先生抓住我的注意的,是他小说的文章,一种奇特的风格。他有一颗自觉的心灵,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性格,在拼凑、渲染,编织他的景色,做为人物活动的场所。”[3]笔者认为,在同时期的批评家里,刘西渭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住了师陀的创作特点。他这篇评论文章的发表,更是为广大读者了解、研究师陀起到了开创性的奠基作用。
然而,在这一时期,也并非所有的批评家都对其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褒扬。孟实就在《<谷>和<落日光>》(原载于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中,指出“他爱描写风景人物甚于爱说故事。在写短篇小说时他仍不免没有脱除写游记和描写散文类的积习”[4]。而基于文学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左翼作家王任叔在《评<谷>及其他》一文中,批评师陀疏于描写真实的人物:“不管是‘诗意也好,是‘织绘也好,我们所要探索的是真实,——真实的人物,活动着的社会上的真实的人物:一种显明的性格,一种活现的典型。而作者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个潇洒而略带倔强的隐约的风貌。”[5]而且,王任叔认为“是沈从文先生的手臂,长在作者的身上了”[5]。
总而言之,虽然这一时期的小说评论呈现出的多是感悟式文字,但却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了师陀的文学地位。也正是这一时期评论家对师陀的关注,才为以后的师陀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文学史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冷寂后的复归:史料的发掘整理和文学史的编写
新中国建国后,师陀研究曾一度陷入冷寂的状态。直到1980年代,学界才开始对他重新关注。这一冷寂后的复归,离不开学者们对师陀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文学史著作中对其的编写。
(一)史料的发掘整理
对一个作家的研究,离不开对其生平资料的查阅、整理,同时也离不开对其文学作品的搜集、校勘。而在师陀史料的系统整理和深入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刘增杰先生。
早在1984年,刘增杰先生就编著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该书分为生平资料,创作自述,评论、研究论文选编,著作年表,著作目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六个部分——可谓是对师陀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在这本书中,刘增杰先生以小说为大宗,将每一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发表及入集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考证,并在年表中注明。同时,在这本书中刘增杰先生将师陀的生平资料一一进行了考证,并搜集整理了当时批评界对其作品的评论。这本书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学者开展对师陀的研究立下了创始之功。从此,师陀研究有逐渐升温的迹象。
继《师陀研究资料》发表后,刘增杰先生对师陀资料的校勘整理并没有停止。在2004年,刘增杰先生主持编校的《师陀全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刘增杰而言,《师陀全集》的编纂不仅是单纯的作品汇集,而是融合了文献考证与校勘的学术工作,完成起来不容易。[1]这本书依据文体分为5卷,共计8册书,其中收录了师陀创作生涯的全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剧本、书信、日记、论文、创作谈和回忆录等。《师陀全集》,尤其是附编部分回忆录的整理,可谓是大大方便了研究者资料的搜集,更是为文学界提供了意义非凡的史料。
另一位对师陀创作的相关史料关注较多的是马俊江。他根据自己查阅的相关资料,发表了《<师陀著作年表>勘误补遗及其他》。他从篇名、写作、及发表时间、发表作品的刊物、入集情况等几个方面,对上述年表的错误与疏漏进行了补订。[1]同时,他也发掘出了少被研究者关注提及的师陀小说《三十六人与一匹马》。这篇小说曾发表在左翼文艺刊物《尖锐》1卷2期中。此外,他还提醒研究者注意甄别师陀作品不同版本的差别。
(二)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一方面是对文学史料的编纂、汇集,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相关作家地位、价值的重新估定与评判。笔者同时认为,文学史中对某一作家的评判则会在某些程度上影响文学对其的研究热度。
1954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师陀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其评价涉及师陀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上,概括性的评价即“虽然在写作技巧上还相当圆熟,但积极意义就很少了”[6]。这充分体现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史家在政治与审美之间的踌躇,但政治话语最终还是替代审美诉求的事实。[7]
1979年出版的两本文学史书籍中都涉及到对师陀的介绍、评价——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前三十年的一部总结之作,它的成就代表了前三十年的水平,它的不足也反映了前三十年的局限[1]。在这本著作中,唐弢只用了300字的篇幅对其进行描述,并且主要从思想意识和艺术刻画两个方面简单评价了《里门拾记》,点出了师陀小说的乡土气息和文体风格。
然而,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师陀则被列为专章论述。文章开篇,夏志清便对师陀作品的风格做了整体评价:“他早年以故乡河南村镇生活为背景的一些素描和故事,文笔典雅,饶有诗意。”[8]但是,“由于这样过于讲求文体的雕琢,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例如《谷》、《里门拾记》《黄花苔》《野鸟集》及《落日光》等,短篇小说和小品散文这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便很不分明。”[8]接着,夏志清便以典型作品为例,评析探究师陀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以及创作特征。从《落日光》到《果园城记》,从《马兰》到《结婚》,夏志清都对其一一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高度赞扬了《结婚》的成就:“若纯就它的叙述技巧与紧张刺激而论,《结婚》的成就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师陀能够在他紧凑的叙事中注入这点恐怖的成分,所以他把《结婚》写成了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曾一度引起文学界的轰动。他挖掘出了诸如张爱玲、沈从文、师陀等作家的才华,并得以重新确立他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而这本书的出版,势必也开拓了师陀研究的视域,唤起了更多批评家对其的关注、研究。
1986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杨义将师陀分专节论述。杨义独树一帜地就作家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时空中的创作内容、创造风格、创作追求的动态变化进行评述,评论视角和方法也较为灵活多样。在该书中,杨义将师陀定义为“多姿多彩的小说体的探索者形象”[9]。
1987年,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师陀也仅是被作者用200字的篇幅简单提及。作者将他归为“京派”作家群,并且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创作,在30年代以芦焚、40年代以师陀的名义分别论述。这种划分,一方面能够对师陀的创作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另一方面却也容易给读者造成辨识方面的混乱。
而在1998年修订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师陀的论述则被明显扩展和深化。作者阐述了师陀作品中的“中原文化意象”“精神还乡结构”以及“文体的模糊性特征”。此外,作者还对师陀在京派中的艺术个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芦焚农村人物贫富的清晰度”“他的讽刺的加重”以及“小说叙事更加讲究”[10]。在40年代的小说章节叙述中,作者着重评述了师陀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短篇集《果园城记》和讽刺长篇小说《结婚》。作者认为《果园城记》“是一部出色的短篇集。”[10]在这部小说中师陀“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以他所特有的既凄凉又温暖的回忆手法,写一个小城的历史和各种小人物的命运”[10]。对于《结婚》,作者则认为“是师陀最好的讽刺长篇”。通过对这些文本结构方面的探究,作者认为“师陀自觉进行‘文体创造的倾向”[10]。
三、研究热度逐渐升高:学术论文数量的激增
伴随着史料的发掘整理,尤其是文学史著作对师陀的肯定与评价,研究师陀的学术热潮逐渐兴起——学术论文的撰写数量在1990年代以后激增,并达到相对繁荣时期。
(一)1980年代的学术论文创作
刘增杰先生不仅在师陀史料搜集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研究师陀的原创性论著里面亦有奠基之作。1982年,刘增杰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的学术论文《师陀小说漫评》,可谓是为新时期师陀研究热潮的兴起拉开了序幕。在该篇文章中,刘增杰对师陀的生平、小说创作、学界对其的评论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并且,刘增杰敢于针对学界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的质疑,哪怕是夏志清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提到:“师陀之所以步入文坛,得沈从文帮助不少”[8]。刘增杰则认为此种判断值得考量。他以1980年12月31日师陀致刘增杰亲笔信为证,信中师陀曾表示:“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关心。[11]”刘增杰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为师陀研究廓清了许多不当之处。
(二)1990年代的学术论文创作
相对于1980年代以面为主的研究状况,1990年的师陀研究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格局。[7]在此,笔者选取了两篇具有标志性成就的学术论文为例。
杨义的《师陀:徘徊在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创新性地将师陀在乡村和都市的不同心理揭露出来,而并非仅仅侧重其乡村叙事。同时,杨义还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师陀与京派的关系。杨义的论文在观点论述方面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钱理群的《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是师陀研究文本细读方面的优秀作品。它主要聚焦于师陀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通过“凝望·飞与幻想”“跋涉者”以及“生命的怪圈与‘时间”等三个方面,对《果园城记》深厚的意蕴内涵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解析。
(三)新世纪以来的学术论文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师陀的学术论文数量激增。“据粗略统计,师陀研究前70年的学术论文不足30篇,而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多达120余篇。”[7]而且,研究者的重心也逐渐由专家、学者向在校大学生转移。笔者在此就以相关重要篇目为例。
解志熙《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以开阔的视野将师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归入论述范畴。他力图在中外文化资源的背景下,探寻师陀在小说史上的独特之处。他对师陀的叙事,创造性地提出了“二反”:乡土小说呈现出“反田园叙事”的倾向,都市小说呈现出“反摩登叙事”的倾向。此外,他从“生活样式”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城乡社会生态,并认为师陀相比其他作家来讲,“或许不大的才情,或许不小的成就”。
在关于师陀乡土小说的论述方面,不同学者论述了其不同方面。2004年5月,赵严峻的《师陀乡土小说论》,通过对师陀前后期小说创作的比较,以及师陀与五四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继承关系,得出师陀小说“批判的理性”和“眷恋的思归”两种文化视角矛盾杂糅的特点。同时,该论文还论证了师陀小说还具有将写实和抒情两种审美风格互补融合的特点。2007年,刘元的《论师陀的乡土小说创作》,点明了师陀小说将“游子还乡”的古老母题注入了现代精神,塑造了一系列游子的形象。此外,该论文还将师陀小说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评析。2008年,关士礼的《师陀乡土小说新论》,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为坐标系,从情节、主题、人物诸方面清理出师陀一部分乡土小说文本的异质性。同时,该论文还提出师陀的存在主义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存在主义。他还以《无望村的馆主》为例,分析师陀存在主义小说的当代“接受障碍”现象。
2002年,梁鸿的《论师陀作品的诗性思维——兼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诗性品格》,指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诗性品格基本上循着两条发展道路:古典诗性和现代诗性。在师陀小说体现的“离开——归去——离开”这一归乡模式中,感受到的是一群现代知识分子无处可依的境地。他们面临的是“故乡”和“异乡”的双重失落,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途中”,只能永远在行走的荒谬感、孤独感和无归属感。
2002年,张永的《论芦焚乡土小说创作的荒原意象》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芦焚小说创作的荒原意象。2003年,王鹏飞的《论师陀早期小说中的悲剧色彩》指出悲剧色彩是师陀早期小说的一个明显特征。他从悲剧色彩入手,串联其早期的主要作品,对蕴含在作品中的悲剧色彩进行解读。
2004年,倪燕的《讲故事的人——师陀小说的叙事技巧研究》,深入探讨师陀小说作品的创作模式、文本叙述方法和他的小说理论,合理地评价师陀在叙事艺术方面的成果与创新。在论文中,倪燕论述了师陀小说在叙事视角、人物塑造以及人称方面的特点。
2006年,陈晨的《“乡下人”的精神诉求与文学想象——沈从文、师陀创作比较论》,将均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和师陀进行比较。一方面,沈从文一心一意地建构“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师陀始终无法回避故乡衰败与凋零的现实;另一方面,沈从文自觉地塑造理想中的“乡下人”品格,由此寄托出他对中国社会人生未来的构想。师陀则从对故乡丑恶人事的揭露和批评出发,转向了深沉的文化思考,将个体生命的感受与体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融为一体。
2007年,简金芝的《论师陀的创作心理变迁》一文就通过对师陀心理变迁的分析,去触摸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普通作家的生命隐衷,并力图更亲近地去理解师陀作品的复杂内涵。
纵观师陀小说的研究历程,其经历了起落浮沉的80年。在这80年的厚重时间里,由刚开始的被发现、被关注,到被搁浅、被遗忘,再到研究热潮的再度兴起,师陀小说的研究历程似乎也验证了师陀本人的人生信条:“暗暗的开,暗暗的败,然后又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12]师陀的小说研究并没有结束,师陀作品的研究更只是刚刚起步。作为文坛的多面手,师陀其他体裁作品方面的研究更有待更多的学者挖掘其内涵和价值。同时,作为一位思想深邃的作家,师陀创作受哪些方面的影响更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注释:
[1]姚喆:《徘徊在田园与都市之间的乡土文学——师陀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
[2]杨刚:《里门拾记》,大公报,1941年,第2期,第4页。
[3]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1937年,第1期,第2页。
[4]孟实:《<谷>和<落日光>》,文学杂志,1937年,第8期,第4页。
[5]王任叔:《评<谷>及其他》,文学,1937年,第9期,第2页。
[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7]王欣:《近八十年来师陀研究述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6页。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刘增杰:《师陀小说漫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2]师陀:《<黄花苔>序》,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郭荣荣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