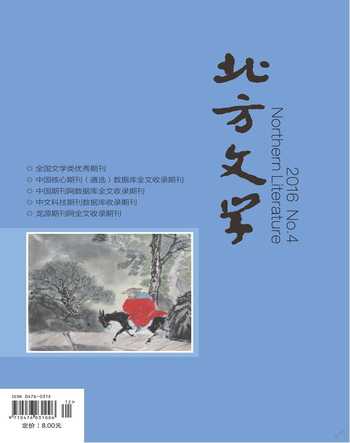在现实与乌托邦的交汇处
彭云涛
摘 要: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中存在着众多鲜有人关注的二元对立关系,本文借助结构主义文论的观点,从坎波斯和朗波里奥两个地域之间的对立谈起,再从文本中挖掘异质文明激荡、人与自然冲突的深层含义,最后,围绕“我”串联起极具象征意义的三个人物形象,从而深化对文本整体性象征意义的理解,启迪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结构主义;《乌拉尼亚》;二元对立;深层意义;象征隐喻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于2006年出版的小说《乌拉尼亚》一经问世旋即受到极大的关注,中国官方也美誉它为“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它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时,意外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坎波斯”,这里的居民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他们生活简单自由、心地善良淳朴,但随着殖民者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逐,这个遗世独立的理想王国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中不断遭挤压,最终被迫迁徙,虽“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能重建家园,每个人却都心存“天堂”的信仰。
有论者质疑这种乌托邦社会存在的可能性,批判其语言平淡、情节零散、题材小气,也有论者盛赞其为心灵空虚落寞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庇护所,称其结构新颖、人物充实、诗意盎然……本文笔者则力图从结构主义角度重新梳理小说中繁多的二元对立关系极其蕴含着的丰富隐喻,从而深化对文本深层内涵的理解,启迪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一、坎波斯与朗波里奥:表层结构中的两地对话叙事
在结构主义看来,叙事是对现象的描述或者与现象产生某种联系,它是对意义的编织和构建,作者选择的叙事方式与其所要传达的思想必然具有某种联系。从整体上看,勒克莱齐奥有意学习墨西哥历史学家路易斯·贡扎拉孜的前一章的末尾作为下一章的题目及开头写作方法,这种叙事形式突出了全书的连贯性、激发读者向后阅读的兴趣,同时,该形式与故事内容也相一致,因为故事本身的结尾就是开放的。从叙事视角来看,作者以“我”(达尼埃尔)的视角展开叙事,其间穿插与拉法埃尔、马尔丹的书信,由此展开朗波里奥和坎波斯两地之间富有张力的对话叙事。
“乌拉尼亚”一词来自于古希腊神话,原意是“天文女神”,这里将其引申为“天上的国度”,“坎波斯”即是这样一个地上的天国,关于坎波斯的叙述,主要来自“我”在旅行途中结识的“最奇怪的年轻人”——拉法埃尔,他出身在魁北克的狼河,随父亲来到坎波斯,而坎波斯有个习俗,即男女长大就得离开村子,拉法埃尔想看海,便离开坎波斯去寻找海了,后来,钱花完了又重返坎波斯。拉法埃尔这一叙事视角的介入,空间上,不仅可以深入坎波斯的内部,切身了解并描述这个地上天国简单美好的日常生活,而且拉法埃尔作为一个外来者又可以站到坎波斯的外围,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观察和打探坎波斯与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狼河之间的差异;时间上,拉法埃尔从长者那里得知坎波斯的由来,在书信、笔记中为“我”讲述其亲历的祥和生活,看海归来后他又目睹坎波斯被占领、居民被迫迁徙的惨景,因而,拉法埃尔是坎波斯由盛而衰的见证者,采取这一视角使得叙事更加客观真实、细致全面。实际上,拉法埃尔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坎波斯”,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由,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和兴致。他的这种特质又为“我”提供了最为直接生动的感受,它们与“我”童年的记忆融合,更深刻地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和对现状的反思。朗波里奥的叙述则主要以“我”为主体,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作为一个还保有良知和天真的外来研究员,不仅观察着科学家、银行家等人虚伪、堕落、腐化的生活,体会着朗波里奥的孕育、变化和扩张,同时也介入其间,控诉当局对像莉莉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的挤压,在土壤学的演讲中呼吁人们应像爱护自己的皮肤一样爱护土壤……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直接叙事交替使用,展开两地差异性对话叙事的同时也传达出作者的态度,启迪读者做出反思和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叙事视角下,勒克莱齐奥选用了不同的叙事时间观。持续进步、无限发展,注重未来的线性时间观为现代社会所取信和偏爱,这也是理解现代性的基础和核心,它在朗波里奥的发展、扩大以及吞并中有很好的体现:一开始革命者将这里的人全部杀害,把尸体埋到一片田里,之后零零星星的科学家入住到此,他们对朗波里奥进行了一番甚嚣尘上的改天换地,以至于最后阿朗萨斯将贫瘠不堪的坎波斯也纳入囊中,可谓是步步为营。而古老的文明常倡导一种退化时间观,它认为最好的时代永远都在过去的时光里,这个世界是退化的而不是向前发展的,坎波斯即是一例。最初世外桃源般简朴单纯的生活模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后来,外来殖民势力慢慢渗入,与世无争的价值选择已经难以维系,最后被迫四散天涯,悲凉之音响彻耳际。这种退化时间观反应在个人身上就体现为一种返回童年的渴望,这即是贾迪所说的“要学会做人,我们首先都得学习怎样做孩子。”
二、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深层结构下的异质文明激荡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存在外结构和内结构两个结构系统,结构主义不仅仅要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更要把握和分析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内涵,由此才能更清晰深刻地理解文艺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与情感。以坎波斯和朗波里奥为代表呈现出的地域差异,除了影射现代人与传统人观念的差异,更凸显出异质文明的冲突,是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对峙,也是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
关于教育。可以说,坎波斯到处都是学校,无论何时何地,人与人互相学习、请教,是彼此的老师。上课就是聊天、听故事、做梦、看云。在坎波斯人看来,重要的不是记忆连篇累牍的知识来装点自己,正如贾迪所言:“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因为一切的记忆都不应以记忆为目的,而应融化知识、指引人们诗意地生活。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建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之上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又集中体现在现代教育体制之中。居于山冈上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们,他们接受的都是课堂上的教育,以将象牙塔里的学问换得专业杂志上的几篇文章或者参考文献中的一条索引为傲。来到朗波里奥的他们更是将知识视为一种权力和获得财富的手段,他们不顾当地居民的安危,设立研究所,大肆投资房产、兴建工厂,弄得民不聊生。事实上,错誤不在现代教育内容本身,而是这种教育方式切断了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提供了通途,现代教育体制所孕育的文明已然失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而看似落后的古老传统却蕴含着强大的平衡力,它不仅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更保护着每一个人内心的和谐。
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两种文明也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坎波斯为代表的古老传统保留着母系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尊崇,年轻、美丽的奥蒂成为引领这个彩虹民族前进的美好象征,她给拉法埃尔的性启蒙更显现了母性之爱的无私与博大。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男性在社会中日益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睥睨万物,这使他们将女性视为私有财产抑或是发泄性欲的工具。以加尔西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们,打着研究红灯区的名义,伤害单纯质朴的姑娘们,小说讽刺到:“那不过是一个把包括纯科学在内的一切都当作权力追求方式的团队成员所制造的不值一提的搞笑事件中的一个小变奏而已。”最后,他们为了维护虚伪的体面终于将这些无辜的姑娘赶尽杀绝!
在勒克莱齐奥笔下,土是居于自然元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部小说中也不例外。作为地理学家的“我”,在一次演讲中通过追溯土地的诞生,反观现代文明对土壤的大肆破坏,朗波里奥一座座新兴工厂的繁荣是以人与自然的失衡为代价的,“他们的钱是从黑土地里,从孩子被草莓酸腐蚀到流血,腐蚀到指甲脱落的幼小的手指的疼痛中榨取的”,一栋栋光鲜亮丽建筑的背后隐藏着散发阵阵恶臭的垃圾山……已然谈不上什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不用提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了。坎波斯却不同,尽管土地贫瘠、资源匮乏,这里的居民仍互相扶持、辛勤耕耘。晴朗的夜晚大家最爱的便是一起躺在温润如母亲怀抱的土地上欣赏闪烁的星群以及水一样的夜色,人、土地、天空浑然一体。拉法埃尔写道“对于所有在大地上生活的——不仅是在大地上生活,对于所有生命来说——天空是一种补偿”,可见,在这个古老文明中自然与人不仅和谐共生,甚至作为对人的回报,自然还启迪着人的精神向更高远的地方进发。有趣的是,坎波斯人尽管热爱着故土,在他们成年后却被要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他们的世界早已超越了脚下的方寸之地,而现代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各自为政,看似日益占据更广阔的土地,实则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就如“我”与拉法埃尔第一次相遇时见到的旅店老板,他整日囿于旅店巴掌大的空间,举着挤满密密麻麻字符的报纸,这不正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吗?
三、象征性人物群像:整体视野下的主题升华
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①事实上,将朗波里奥和坎波斯仅仅视为纯粹的两个地域和异质文明的对峙还不够。结构主义重视整体性,即相对于部分而言整体具有逻辑优先性。霍克斯说:“在任何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 人物的功能不仅是由他与这个体系的其他功能部分的关系所决定,也与不同人物之间错综的关系密切相连。为了更好地保持结构的整体性,传达复杂内容,作者有意以“我”为基点,联系起其他人物(包括达莉娅、莉莉、奥蒂等),在串联之中每个人又都各自具有象征意义,他们构成一个意义的整体。正如有论者所言,《乌拉尼亚》的价值在于一次富有启示意义的独特历程,在于其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大量丰富的隐喻。②作者将自己对世间真、善、美等普世价值的坚定信仰寄寓到人物之中,从而使小说摆脱现实主义一地鸡毛的琐碎叙事,达到净化和升华主旨的作用。
对于一个内心具有爱的能力的人来说,爱的不断受挫是无法击垮她坚持爱下去的勇气的,达莉娅即是这样一个人,虽饱受欺骗、遍历苦难,仍敢爱敢恨、无怨无悔,年轻时,勇敢地投身革命,坚定地为受害者和正义事业发声,年迈时,热情洋溢、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愈发明显,收养丧母的女孩,为女性维权排忧而乐此不疲……她的生命光芒四射。正是这束不变的光让“我”对她的“爱”历久弥新。达莉娅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真”这一普世价值,一路走来没有悔恨、没有愤懑,唯有沉实的心愿和坚定地步伐。
在朗波里奥和坎波斯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地域,即阿特拉斯花园,这是众妓女的居住之处,姑娘们为那些所谓的体面人提供服务以获取微薄的收益,最后却被他们以“净化河谷风气,关闭‘可耻的花园”为由驱赶、迫害。莉莉也在受害者之列。第一次从研究员口中听到对莉莉的亵渎时,她便成了“我”一生的牵挂,虽然“罪恶像脏水一样从她身上流过”,却没有在她温和、清香的身体上留下丝毫痕迹,“她的微笑,她那女人的身体和孩子的面庞,依然保留着她来自土地的芬芳。”她始终保持着善并相信着世间的善,当“我”去探访她时,她不仅热心以待,还在路人怀疑的眼光中保护着“我”以免受他人误解。清澈、纯净的泻湖容易被污染,唯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明净。莉莉的“善”是她在污浊世界里备受欺凌的原因,却也神奇般地保护着她。
坎波斯的奥蒂是另一个重要的女性,她实实在在是“美”的象征。当奥蒂觉察到拉法埃尔对自己的爱慕时,她无私地给拉法埃尔以性启蒙教育,在日后的生活中又落落大方,不给他任何心理压力。因为“对她来说,爱不是独占,不是悲剧。她说爱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它会改变,会转移,会回归。她说一个人可以同时爱着几个人,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甚至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她说爱很简单,有时候没有结果,爱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当坎波斯人被迫流亡时,她担起引领全族重寻家园的重任,途中还为贾迪举办丧礼,帮阿达拉接生……奥蒂美丽的容颜之下有着一颗更唯美的心,是这个彩虹民族名副其实的象征。
可以说,通过对这部小说二元对立关系的梳理以及对人物群像特殊象征意义的整体性思考,除了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对现代文明肆意扩张的控诉、批判以及对淳朴善良的乌托邦文明的向往,更蕴含着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启迪和祝愿。坎波斯的参事贾迪曾说:“没有任何东西会永恒不变。只有星星永远还是那些星星。我们应该做好出发的准备。坎波斯不属于我们,它不属于任何人。”人类一直苦苦寻找的天堂不在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也不属于任何人,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遥远的光点,在奔向这个光点的时候,人们秉心敛性,反思自己,从而不断完善自己。小说以引用约翰·欧文的《乌拉农·乌拉尼亚》为开篇,颇具启发性:“万事震惊,心余平静:/风暴交错似无情,/雨后盼得彩云归,一晌通明。”也许,对于这个彩虹民族来说,风暴和波折看似无情,实则是对人坚定信仰的考验,坎波斯不仅仅是一片地域,更是心灵中一方永恒的净土,风雨过后必将重见彩虹。
注释:
①[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②高方、许钧主编:《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页。
参考文献:
[1][法]勒克莱齐奥.乌拉尼亚[M].紫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 高方、许钧主编.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 赵小琪.结构主义视野下白先勇〈臺北人〉新读[J].贵州社会科学,2009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