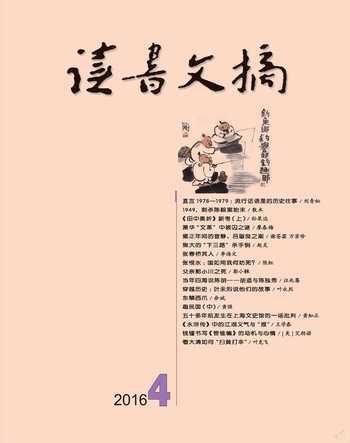看大清如何“扫黄打非”
叶克飞
禁毁书籍与奴化教育始终并行,最终使得清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对传统风骨和人性摧残最烈的一个朝代。
雍正六年 (1728年),护军参领郎坤向皇上递了一份奏折,结果倒了大霉,遭遇“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他犯了什么大错?奏折中有句话“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坏就坏在这:“援引小说陈奏”。
在奏折里为什么不能提小说?因为小说是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皇上带头不喜欢,郎坤不触霉头才怪。
清廷反感小说并非无因。有清一代,禁毁小说作为官方行为,呈常态化存在,堪称“思想阵地的重要分战场”。
在金庸的 《鹿鼎记》 中,天地会是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它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主要由游民组成。会众流动性强,需频繁联络,同时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组织。所以,他们以地下活动为主,有各种秘密“切口”。因为会众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切口既要复杂保密,又要易接受,因此多脱胎于通俗小说。
天地会还有自己的创会史,在这个虚构故事里,有抵抗外侮,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的群雄大聚义,带着许多通俗小说的影子。它随着天地会的发展逐步充实内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中,已长达数万字,成了货真价实的小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制最烈的一个朝代,文字狱与焚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武器。清廷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众思想。
有清一朝,禁毁书籍与奴化教育始终并行,最终使得清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对传统风骨和人性摧残最烈的一个朝代。
禁毁小说是毁书运动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设,许多人都会拿乾隆年间的 《四库全书》 说事儿。但所谓“全书”,非但不全,在四库之外的,许多都要遭遇被毁命运。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四库全书》 纂修工作启动,首先是对全国书籍进行大清查。乾隆认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故打算借清查之机,一举予以销毁。
这次大清查焚毁书籍无数,行动到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销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史部书籍亦“灾情惨重”,吴晗曾称:“清人纂修 《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小说当然也难逃焚毁厄运,仅在1779年到1882年间,就有多起例子。如1780年1月,两江总督萨载上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包括讲述甲申之变的 《剿闯小说》。1781年2月,萨载再度请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 《樵史演义》“纪天启崇祯事实,中有违碍之处,应请销毁”。
无独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抚刘墉 (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罗锅) 也上奏,称 《樵史演义》“虽系小说残书,于吴逆不乘名本朝,多应冒犯。应销毁”。1781年11月,又是刘墉上奏,焚毁小说八十余部,其中包括了著名的 《英烈传》,这部小说讲述朱元璋开国故事,自为满清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抚郝硕奏缴12种书籍,其中包括以岳飞为主角的 《精忠传》,而关于岳飞的最知名小说——钱彩的 《说岳全传》,不久后也遭禁毁……
防 《水浒》,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登基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谓“琐语淫词”,指有伤风化的剧本和小说。当时环境尚算宽松,被禁小说仅两本,一是李渔的 《无声戏二集》,一是 《续金瓶梅》。但前者被禁,多少带点政治色彩,预示着满清政府禁毁小说的真实动机也许并不单纯。
据载,《无声戏二集》 在刊刻时,曾得时任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的资助。其中有关于张缙彦本人的情节,指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张“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得“不死英雄”赞誉。顺治十七年 (1660),御史萧震弹劾张缙彦在小说中自我标榜,张最终遭遇籍没、流徙宁古塔的命运。这张缙彦也是活该,降李自成,降清,活脱脱三姓家奴,既然如此,老老实实就算了,还为自己盖“贞节牌坊”,时常以明朝遗臣自居,清廷自然会对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开刀。
《续金瓶梅》 的作者是丁耀亢,官方说法是“经查阅该书,虽写有宋金两朝之事,但书内之言辞中仍我大清国之地名,讽喻为宁古塔、鱼皮国等”。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黄色小说,但在康熙收复台湾后,开始对小说界全面开战。当时,清庭三管齐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狱,另一方面则打着“端风俗、正人心”的旗号,加强对小说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 (1753年),乾隆下谕,禁止将小说译成满文,理由是满人一向单纯淳朴,小说会把他们教坏。次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标直指 《水浒传》,认为此书“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 《水浒》 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奏请将此书焚毁禁绝。
乾隆自己也对 《水浒传》 很是忌惮,那年初,广东东莞莫信丰和增城王亮臣分别聚众起事。七月,直隶、山西又相继奏报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是,《水浒传》 成了“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严禁。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确以“社会动乱根源论”的旗号查禁小说。
乾隆执政后期,教乱、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莲教起义,纵横数省,使得满清国势转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控制,坚持“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败坏;人心败坏,是因为小说误导”这一逻辑不动摇。
嘉庆皇帝坚决继承老爹的遗志,他的目标不仅仅是 《水浒》,在谕旨中,他称“更有编造新文,广为传播,大率不外乎草窃奸宄之事”,换言之,重点在于“编造新文”。所谓“新文”,应是那时流行的公案小说,代表作是 《施公案》。此书主题虽是断案,但出身绿林的侠客黄天霸是主角之一,后被“招安”,情节逻辑有点像 《水浒》。
《水浒》 作为以造反为主题的最著名作品,一直难逃被禁命运。咸丰即位时,天地会势力不断扩张,分支不断衍生。咸丰元年 (1851年),清廷再度禁止 《水浒》,当时湖南大乱,上谕将湖南地区的天地会分支“动乱”与 《水浒》 直接联系在一起,但谕旨中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仅湖南就有多处坊肆刊刻售卖 《水浒》,可见乾隆年间就颁布的禁令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只是咸丰朝要忙活的麻烦事太多,太平天国、英法联军都是威胁祖宗社稷的大敌,朝廷哪里还顾得上禁毁小说?
即使官方真的将禁毁 《水浒》 落到实处,意义也不会太大,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书越禁越受欢迎,《水浒》 是清廷禁止次数最多、禁毁措施最为严厉的书籍,但偏偏也是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既然有利可图,书坊也甘愿冒风险刊刻,据马蹄疾 《水浒书录》 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至同治的231年里,《水浒》 的刊印达到22次,可谓越禁越流行。
二是想造反的照样造反,他们的许多行为模式确实模仿小说,但却并非因为读了小说而造反,其根源还是不堪满清统治者的压迫。民国人刘治襄在谈及义和团时曾说:“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 《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 《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陶成章曾在 《教会源流考》 中写道:“洪门 (即天地会) 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扩清之功,故又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 《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
清代两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一是太平天国,一是义和团,二者都有不少小说演义的痕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原为永安州书吏,身份与宋江类似,他也以宋江自期,号小宋公明。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以为只要念动咒语使神附体即可刀枪不入,多少也是受了 《封神演义》 的影响。
除了害怕百姓读小说造反之外,清廷对洋人也十分警惕,严禁西方传教士利用小说传教。雍正年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发明了“以小说传教”的模式,编撰章回小说 《儒交信》,将天主教义与儒家学说融合,加强传教效果。嘉庆十年 (1805),朝廷下谕,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嘉庆十八年(1813)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天理教众“夺门犯阙”,朝野震惊。不久后,嘉庆便下谕,严禁民间结会拜会及坊肆售卖小说,年底又下旨禁止开设租赁小说的书肆。这标志着清廷的禁书从单纯的毁书发展到了流通领域。
高压管制不能阻碍小说市场的高度繁荣
清政府查禁小说的重点,一是“诲淫”,一是“诲盗”,后者的代表是 《水浒》,前者指的则是所谓的“淫词小说”。
首先发难的是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这位被康熙盛赞的“名儒”,任上强调正风俗。康熙二十五年 (1686),他颁发告谕,查禁淫邪小说,称不法商人为赚钱,刊印那些色情文学,导致小年轻心猿意马,败坏世风。
次年,给事中刘楷上奏,称“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希望能彻底禁绝。
康熙同意此说,再度展开禁书运动。康熙五十三年 (1714年),他下谕禁绝淫词小说。对刊刻者施以大棒:“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处罚规定被收入 《大清律例》 卷二十三刑律贼盗的条款中。
但禁例所约束的往往只是规矩人,包括有职业操守的书坊、一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李渔和烟水散人徐震。可是胆大妄为、品流低俗者却不管这一套,仍大肆编撰出版淫词小说。这些小说多为抄袭或拼凑,水准低劣。
李渔在张缙彦一案后,并未受到牵连 (这也客观说明清廷的主要目的不是禁书,而是清理门户),《无声戏》 虽遭焚毁,但后来又以 《连城璧》 之名刊刻。可是,随着清廷在思想领域的逐步收紧,李渔的创作空间也愈发狭窄。
对于书籍出版业而言,清廷禁毁书籍带来的影响反而不大。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书坊众多,涉猎也广,经史子集、科举“参考书”等,都在刻印范围内。色情小说因其读者广泛,更畅销不衰。
嘉庆十五年 (1810年),御史伯依保奏请查禁《灯草和尚》、《肉蒲团》 等几部小说。这位御史谏言的本意是重视思想控制,博取领导欢心,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数日后,嘉庆称这些都是老三篇了,新编之“语涉不经”的小说则不见奏闻,明显是“没话找话说”,摆忠心,没实质,皇帝骂他年老平庸还妄思升用。这事儿固然是笑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小说出版市场,不仅旧本翻印无法禁绝,新作还不断问世。
民国学者张秀民曾考证,清代苏州有书坊53家。其实,实际数字远多于此,道光十七年 (1837年),苏州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就多达65家。
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确实与满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观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写婚外情的 《醋葫芦》、描写同性恋的 《品花宝鉴》、描述妓院生活的 《九尾龟》 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题并不淫秽,仅仅涉嫌低俗,也遭禁毁,比如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闻名后世的 《三笑姻缘》。
即使是奇书如 《红楼梦》,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 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
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 《红楼梦》 刊刻、传播。他认 为 《红楼梦》 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
道光即位后,颁布 《御制声色货利谕》,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 也在“淫书”之列。
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 《红楼梦》 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 《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 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 《北东园笔录四编》 中称“《红楼梦》 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 《寄蜗残赘》 中称 《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
《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 《庸闲斋笔记》 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 《红楼梦》 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
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满清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宫中流传下来的 《金瓶梅画》,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金瓶梅》 也非满清贵族的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 《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运。
大厦将倾时,小说管制变成笑话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政府对小说的管制也渐渐失控。
清朝后期最大的一次禁毁小说行动发生在同治年间,主角是洋务名臣丁日昌。此时的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总结此次动乱,许多大臣仍是老调重弹,将罪名加于 《水浒》。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六年(1867年)奏请禁毁小说,意图以道德约束百姓,自然甚得上意。同治下旨,“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不过,此时的清朝简直是“百废待兴”,地方大员们压根没空响应号召,唯有丁日昌所辖的江苏展开行动。他为此特设“淫词小说局”,筹措经费,出钱收缴淫词小说,集中销毁。颁布告示中写道:“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 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他先后两次开列应禁书目,各类共计达到265种之多。
“《水浒》、《西厢》 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已可看出小说的流行程度。丁日昌“迎难而上”,这场“运动式焚书”,落实力度很大。他将地方官员对待此事的认真程度与官员考核挂钩,颇有成效。
在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单中,有著名剧本,如 《西厢》、《牡丹亭》 等;有文言小说,如 《情史》、《子不语》 等;还有描述性生活的“涉黄”小说,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春灯迷史》、《巫山艳史》 等;有才子佳人小说,如 《金石缘》、《品花宝鉴》等;有公案小说,如 《龙图公案》、《清风闸》 等;有神魔小说,如 《女仙外史》、《绿野仙踪》 等。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及其续书、《红楼梦》 及其续书也都在列。
因为仅有江苏一省“严格贯彻落实”的缘故,所以,同治九年 (1870年),御使刘瑞祺再次上书奏明各省书肆刊刻售卖违禁小说,要求销毁小说书版。由此也可侧面看出,清政府对书籍的管制基本处于无效状态。
甲午战争后,举国震动,救亡图存之念深入人心,加上报刊这种新型载体的盛行,现代小说开始出现。尽管戊戌变法后,清廷一度钳制言论,波及小说,也难改大趋势。庚子事变后,报刊在租界内发展更为蓬勃,小说成了主要的启蒙方式,如林纾译 《黑奴吁天录》,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 杂志,都具历史意义。
可笑的是,直到清朝即将灭亡之际,仍有人提出禁书。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咨议局通过一项 《发起通俗教育社》 的议案,其中也提到小说,认为“中国小说善本绝少,非淫乱则荒唐,其最烈者如 《西游》、《封神》 等书,启人迷信,积之又久,以致有义合拳、红灯教之结果”,认为“应行禁止”。但此时,上海各大书局发展极快,竞相翻印传统小说,小说大量普及,禁毁就成了装模作样的笑话。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统计,辛亥革命以前的白话通俗小说有1160余种,其中在鸦片战争以后创作并出版的有560余种,超过半数。可见,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时,所谓的小说管制也完全失控。
(选自《新周刊》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