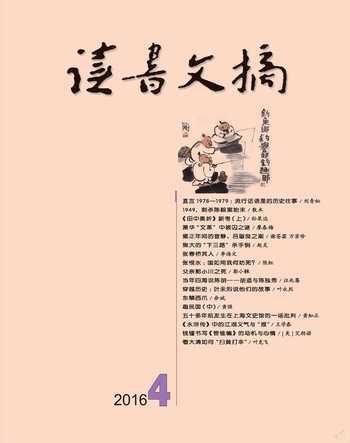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之案
谢苍霖 万芳珍
曾静投书始末
雍正六年 (1728) 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省会西安的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一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骇异,当即把投书人带入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信。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书信中对世宗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而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鼓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世宗破例授予岳钟琪,以示非同寻常的恩宠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钟琪感恩图报,恨不能肝脑涂地。而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朝堂上尤其是满洲贵族中有许多人心存妒忌与猜疑,诬陷、中伤他的密疏积垛成堆,世宗置之不理。岳钟琪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辞职,世宗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岳钟琪十万火急,即日密邀陕西巡抚满洲人西琳来署会审,还动了大刑,无奈“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改变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即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约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乡贯住址和起谋由来等情况,第二日又说出了“同谋”者的情况。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实姓名叫曾静,湖南永兴人;“张倬”真名叫张熙,是曾静弟子,湖南安仁人。曾静原为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其“悖逆”思想的形成则受清初名儒吕留良的影响。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桐乡西南)。此人早年曾从事抗清,顺治中应试为诸生,既而懊悔,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试,乃至削发为僧 (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卒。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仇恨与日俱增。所谓“江南无主游民”,便是表示抗拒清朝统治。出于对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崇拜和信仰,案发前一年,曾静特地让张熙到吕留良的家乡去访书。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沿途又听到贬毁世宗的一些传闻,回去后一一向曾静汇报。当时民间传说岳钟琪上书指责世宗 (实无其事),曾静于是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他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书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嘱咐张熙见机行事,路上倘若感觉形势不利就返回。张熙由川入陕,路上听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心中发怵,本该返回,转而想既然出来一趟,索性豁出去,于是来到西安,没有料到中了岳钟琪的圈套。张熙上路后,曾静预料凶多吉少,便在自己的衣服里子上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字样,以备一旦死于不测好让别人认尸。
以上是案发后曾静和张熙所招供的投书策反的由来,张熙最初向岳钟琪所提供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详尽。他所交代的“同谋”,实际上仅仅是他和曾静平时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这些人与策反活动毫无关系。所谓湖广等六省“一呼可定”,更是狂言妄语。岳钟琪一时也难辨真假,六天内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世宗震惊之余,怀着似乎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他在岳折叙及盟誓的一节文字旁加朱批云:
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拟。朕实嘉悦之至(《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
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弹劾,下狱判斩监候,至乾隆初年方获释。所谓“消灾灭罪”“君臣之情”,不知从何说起。
世宗的“出奇料理”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世宗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和门生,搜缴其生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及其“同谋”和各家亲属。雍正六年十月,除张熙已在押及已死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和吕门弟子严鸿逵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数捕获。主要有:曾静及其门人廖易;曾静熟识的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刘之珩老友谯中翼;张熙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吕留良之子吕毅中;严鸿逵门人沈在宽;为吕留良师徒刊印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兄弟;为吕留良编过文集的孙学颜等。搜获的书籍文稿主要有:曾静家中“大逆之书”三册;张熙家中“逆书”两册及策反信原稿;吕留良及其弟子的所有著作,包括讲义、语录、诗文集和日记等。此外,张熙随身携带的 《拟生员应诏书》 《吕留良诗钞》 和刘之珩刻印的 《握机图》 等,先已被岳钟琪搜缴而去。
十一月,世宗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受审者宣讲清朝列祖的“深仁厚泽”,及世宗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攻心,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 《归仁录》,颂扬世宗“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之德。
第二年 (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接受最后处置。世宗成谋在胸,在四月十五日的朱批中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透露风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此后数年间,世宗的“出奇料理”相继出台,归纳起来为两大举措。
一大举措是对曾静、张熙从宽发落,利用二人做宣传。事发之初,世宗对张熙的自投罗网表示深感庆幸,说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读过“逆书”(策反信) 后,世宗自称先是“惊讶堕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如此论朕也”。接着故作大度,自诩“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清代文字狱档》 第九辑)。他明白,“逆书”中的“诬谤”别有来源,非曾静、张熙凭空捏造,因此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二人,心中已拟定处置二人的基本策略,即利用,而其前提是感化。软骨头的曾静、张熙既然被感化,于是世宗于七年 (1729) 十月命免罪释放曾、张,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再者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则曾静反有功于朝廷。当然这不过是托辞,世宗不杀曾、张的真正目的是借以显示自己“无故加之而不怒”,亦即表明自己无辜,同时留下二人现身说法,为自己作宣传。
此案涉及大量“反面材料”,最触目的如策反信列举世宗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具体事实如言世宗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胤礽、胤禩、胤禟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世宗收纳废太子妃嫔,常领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世宗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等,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按理说这类材料应该严格保密,防止扩散才是,可是世宗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世宗为此做出一副“内省不疚,何恤人言”的姿态,命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谕旨,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 等,合成 《大义觉迷录》 一书,有意让“反面材料”充斥其中 (当然都经过 《上谕》 批驳),堪称古今一奇。
《大义觉迷录》 经刊印后颁发各省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这部奇书,然后把曾静交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事毕把他送回原籍候旨。世宗此举意在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他在 《上谕》 中自明心迹云:“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乎?将以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大义觉迷录》 卷一)几乎要赌咒发誓,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世宗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节节索踪,最后根究到已经败亡的胤禩集团,据说是胤禩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世宗打击残余政敌又有新的借口。
世宗“出奇料理”的又一大举措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
世宗在连篇累牍的 《上谕》 中对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上述思想言论大张挞伐,剖析“以御服为旃裘,固属悖乱”,而称蛙声莽年是学吕留良,“以王莽篡弑之岁月,指拟本朝,比之于闰统”,“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指斥三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党同叛逆”。他认为:“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五月二十一日《上谕》) 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世宗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罪条拟定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世宗又来了一招“出奇料理”,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规定生员必须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如果生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具呈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要听取天下公论,犹如孟子所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以显示“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人人过关的威胁手段。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天下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无一人有异词 (纵有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世宗于是名正言顺地就诸臣所拟裁决如下,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吕家财产抄没,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故免议,其嫡属如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4人斩监候,另2人及各家亲属流放3000里外,另11人处杖刑,4人免刑释放。
时为雍正十年 (1732) 十二月。
世宗于雍正十三年 (1735)八月驾崩。十月,继位尚未改元的高宗违背父训,公然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当年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他所持理由很简单:“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十月初八日《上谕》) 同时,高宗下令毁禁 《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著作也遭禁毁。真实原因是此事宣传太过,泄密太多,不利于“收拾人心”。后来,在宁古塔的吕留良后代有开面铺的,有开药铺行医的,有的还捐了监生。高宗把他们流放到更荒远的黑龙江,配给“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入士流(陈垣 《记吕晚村子孙》)。
(选自《三千年文祸 (第三版)》/谢苍霖 万芳珍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
——兼论 “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