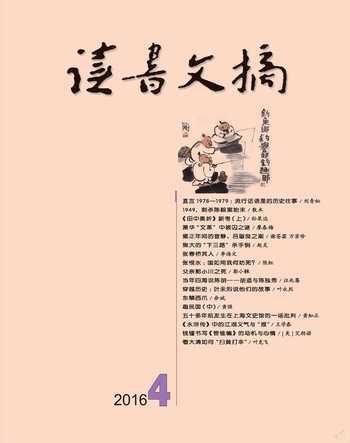张恨水:国如用我何妨死?
在中国,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张恨水这个名字几乎是无人不知,《金粉世家》 《啼笑因缘》 等作品也几乎是无人不晓。据说,出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那批“张恨水迷”们一点也不亚于当今的“粉丝”,就连堂堂的“少帅”张学良,也为了一睹大师的风采,亲自摸到了张恨水的寓所,做了一名“不速之客”。
张恨水除了著作等身之外,还有“三绝”,着实叫人不可等闲视之。——其一,能够同时撰写多部小说,最高纪录是七部长篇同时着笔;其二,从来不打草稿,每每是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甚至没有什么涂改;其三,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穿插于小说之中,可谓是手到擒来、游刃自如。
后来,台湾的一位学者甚至还为张恨水总结出了七个“第一”——而且是至今无人能够企及的“第一”:一为作品的数量最多,这是与他同时代的乃至上一代的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二为所采用的文学形式最多,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七律、七绝、五律、五绝、古风、歌行、新诗)、词、曲、赋、骈体、游记、通讯、政论、考证、尺牍、戏评、影评、画评……无不涉猎;三为发表过的文字最多,高达3000多万字,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刊载过的习作、日记、文件、画稿等等;四为读者最多,从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到大中学校的学生,甚至还包括学者 (如陈寅恪、夏济南)和政治家(如毛泽东、周恩来);五为被改编成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也最多,例如电影、话剧、戏曲等等;第六,因此被人冒名伪作的“赝品”也最多,据说当年在东北就有一家“张恨水书店”,专门出售这一类的伪作;第七,从创作的题材而言也属最多,仅以小说为例,即有言情、社会、讽刺、武侠、战争、旅行、官场、梨园、校园、市井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
面对非议,张恨水说:“吾固以小说为业,略进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可稍稍自慰矣。”
然而,当年在新文学运动的圈子里,尤其是左翼文学阵营形成以后,张恨水便很难再有往日的风光了。他所采用的那种章回体的旧形式,他所持有的那种缺乏“阶级意识”的立场,还有他所一贯表现的那种“风花雪月”的内容和情调,全都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这是一篇由太阳社作家钱杏邨(阿英) 执笔的发表于1933年的文章——《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在上海事变期间,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在诗歌方面,固然呈现着强度的活跃,在小说的写作方面,也是非常的努力。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从成为了他们的骄子的 《啼笑因缘》 的作者张恨水起,一直到他的老大家程瞻庐以至徐卓呆止,差不多全部动员的在各大小报纸上大做其“国难小说”。
……虽然当劳苦的工农士兵勇猛的起来反抗,他们也欢欣无间的为他们作了《健儿词》,高呼着:“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但他们,封建余孽本身,是只有“大声唤”的、没落的封建阶级,他们是没有“出路”的。
……张恨水的这几篇小说,如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胡话”,这“胡话”正表示了封建余孽以及一部分小市民层的“自我陶醉”的本色……一般的说来,反映在张恨水作品里的阶级意识,是封建余孽的意识。然而,是不纯粹的,在他的意识里,同样的也具有相当的资产阶级的要素的部分。
可以这样说,左翼文坛的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了上个世纪末。《张恨水传》 的作者石楠曾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次旅途当中,他与同船的几位乘客无意间聊起了张恨水,哪知众人异口同声地斥责他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甚至是“黄色作家”。石楠说,当时的他真像是挨了一刀:“这是诬蔑!张恨水先生从未写过诲淫诲盗的黄色小说,怎么能说他是黄色作家呢!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也不公正,他是人民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家!”他气愤地为之辩护说:“以前的定论,全都属于极左文艺思潮的流毒!”
不可否认,当年的张恨水确实是以大量的通俗小说而登上文坛的。他不同于郁达夫、徐志摩等人,从未喝过洋墨水;也不同于叶圣陶、朱自清等人,不曾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然而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他是个“封建余孽”吗?是个“黄色作家”吗?至于他的作品是否受到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暂且不论,仅从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表现出的态度上,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响当当的爱国主义作家!
——那是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张恨水怒火中烧,他提笔写下了 《耻与日人共事》 《亡国的经验》 《学越王呢?学大王呢?》 和 《中国决不会亡》等一系列的杂文,愤怒声讨侵略者的残酷罪行。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上的强国无论是谁,他都不能并吞中国。中国决不会亡!”
——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恨水再次拍案而起,他不仅将正在 《新闻报》 上连载的长篇小说 《太平花》 中加进了抗日的内容,而且还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抗战小说——《九月十八日》 《一月二十八日》 《仇敌夫妻》 《风檐爆竹》 《以一当百》 《最后的敬礼》 《无名英雄传》,以及纪实文学——《江湾送粥老妪》 《汽车夫胡阿毛》 《不歇劲》 《神枪手》 《盘肠勇将》 《两兵士》 《大刀队七百名》 《却里张》 《冯木匠》,还有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后来,他将这些作品辑成一集,取“弯弓射日”之意而名之为 《弯弓集》,并自费出版之: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风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爪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此后,张恨水还创作了长篇小说 《东北四连长》,反映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抗日的民族英雄们。为了能够获得感性的认识,他亲自采访了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向他们详细了解军事常识以及士兵的心理。小说在 《申报》 的副刊 《春秋》 上连载之后影响颇大,就连著名的硬派电影导演王次龙也爱不释手,并准备将其改编为电影,遗憾的是时局渐紧,最终未能如愿。
张恨水没有过高地评价自己,仅仅自喻“伏生”而已;但他敢于面对现实、抨击现实的勇气,却远非伏生老儿可以比拟。
面对颂扬,张恨水说:“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进步文艺界看到了,中共南方局也看到了。
——那是1938年的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张恨水在没有出席大会的情况下,仍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理事,而且是理事当中唯一一位写章回小说的作家。好友兼同仁张友鸾得知后兴奋地前来道贺:“这说明新文学的作家们已经捐弃了门户之见。”释怀归释怀,但他还是没有说到事情的实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发挥作用了。张恨水终于被革命作家认可了,张恨水也终于摘去了头上的那顶“封建余孽”的帽子!
在张恨水的一生当中,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他自己的出色表现,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他终于改写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
1944年的5月16日,是张恨水五十岁的诞辰。为著名作家祝寿,这是中共南方局为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压迫而采取的一种新型而机智的斗争方式,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此来增强文化人之间的团结,壮大抗战文学的队伍,更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指明前进的道路。在此前后,被祝过寿的有郭沫若、洪深、老舍、欧阳予倩、王亚平、叶圣陶、茅盾等人,他们都是为新文学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因此,当张恨水得知自己也成为了被祝贺的对象时,不由得诚惶诚恐起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逃避——坚决不参加已经为他筹备好的庆祝茶会。然而不管他逃到哪里,5月16日这天,重庆的各家报纸上还是刊登出了一批批祝寿的诗词与文章。
——这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老舍写的 《一点点认识》:
恨水兄是一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这,在别人看,仿佛就有点“狂”。但是,我说,能这样“狂”的人才配作文人。因为他敢“狂”,所以他才不肯受苦,才会爱惜羽毛。我知道,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代表了文协,也就是代表了整个抗战文艺界对张恨水的看法。
——这是 《新华日报》总编潘梓年发表的祝寿文章 《精进不已》:
一个作家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三十年,不为富贵所摇惑,贫贱所移易,只此一点就已很可钦敬。而且凡是读过 《新民报》 的人,读过 《新民报》上恨水先生所写的文章的人,都能知道恨水是怎样一个作家,都能知道他是一个自强不息,精进不已的作家……他有他的识力,他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
这样的文字无疑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张恨水的肯定与赞许。
张恨水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他的眼泪潸潸而下。但是,除了自己的人格与立场之外,他还希望人们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作品,理解他这几十年来所坚持选用的创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是深深地理解他的,就在这天的 《新华日报》上,还同时刊登出了这样一则短评——《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回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和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也正如此,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应该说,张恨水此生无憾了!张恨水终于从共产党那里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理解和评价!
那天,他自己也写下了一首 《五十述怀》。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对于自己五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写下的是这样两句“鉴定”:
卖文卖得头将白,
未用人间造孽钱!
——虽说过于谦逊了些,但这是事实,而且确凿无疑的事实:他始终都是清白的!
(选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