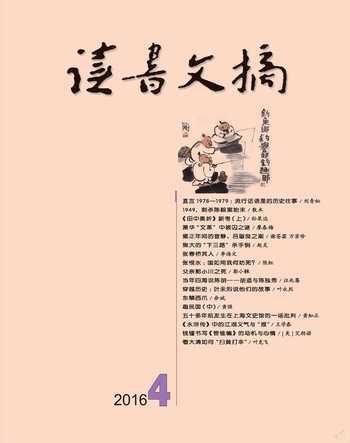东鳞西爪
王国维不买严复的账
作为首屈一指的大译家,严复对自己的翻译颇为自信是顺理成章的。他曾在信中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这话说来一点不托大:林纾译的那些小说,换个人也办得了,虽然未必那样文采斐然,若他翻译的 《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 等大作,不是像他这样精通西学的,谁办得了?所以这个账当时的人应该大都是认的。
不是没有微词,《原富》的一些译法就在 《新民丛报》上引发过一场讨论,梁启超对严复以“计学”译economic(经济),对严过于追求译文的古雅,都有商榷之意。黄遵宪等人也有话说。
然而,都属“微词”。真正对严复不买账的,似乎只有王国维。
严复有狂傲之名,王国维则是谦谦君子,罗振玉曾请其译编 《农学报》,他自谓译才不如沈纮,就荐其任之,自己协助。但关乎学理,则当仁不让。
他在 《论新学语之输入》 一文中对严复就不大客气:“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赞其“工”是礼貌,责其“不当”才是重点。而且他拿来挑刺的,没准就是严的得意之笔,比如evolution译为“天演”,sympathy译为“善相感”,他之不以为然,溢于言表:“‘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
对严的好用古语,王国维也觉不足为训,他举的例子是严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
王国维未曾一一指出,实因他所关注者不在一词一语之辨,而在译界之大势。
他最不耐的是严复不肯沿用日本人已有定名的译语,“进化”、“同情”、“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在他看来,“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自创新词,比日译还难懂,既然如此,干嘛不用?
只是当时王国维人微言轻,所说未必能扭转风气,但后来的翻译,确是走上了他希望的那个方向,严复自创的许多术语均败于日译,现代汉语词汇中日语出身者,委实不少,只是我们已习焉不察了。
钱钟书“骂人”
钱钟书是否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的“骂人”话,已成一桩公案,而且注定会是无头案。杨绛先生曾撰文“追本溯源”以正视听,但很多人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无他,只因太像钱先生的口吻。从某个意义上说,叶公超是“懒”,吴宓是“笨”,陈福田是“俗”,此其一;“骂”其中一人,亦能见出“骂”者的才高气盛,然对三人排头并“骂”,似乎更特别地“钱钟书”,此其二。所以纵使有人道出此语版权别有所属,没准会有更多人认定,这活脱脱是钟书君的口吻。
钱钟书在为 《吴宓日记》 所写序中自承“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对当年的孟浪表示抱歉。其实,钱先生的读者虽然没几人有幸亲聆他臧否人物,对他的“取笔弄快”却是半点也不陌生。古今天纵其才的人物,其才气的发露,臧否人物也是一端。钱先生在 《林纾的翻译》 中将林翻译时不时擅自发挥的添写归为文章家的“技痒难熬”,让钱先生舍弃“取笔弄快”的愉悦,他肯定不爽。我们若从“骂人”的角度去读的话,会发现即使 《管锥编》、《谈艺录》 这样的著述,衡文论诗,疏证考订之间,亦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波俏,逸趣横生。
当然文学是较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尽展骂人的艺术。他笔下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无一逃得过他的讥刺挖苦。早有论者说过,《围城》 里不是“愚人”即是“诬人”,或者既愚且诬,《围城》 序里说得更直截了当——都是“两足无毛动物”。我总觉得,制造一个众人登场的场合,拎过一干人来挨个挖苦过去,必是作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之时。大约有观众就有表演性,而钱先生最善将种种的表演变成出丑卖乖。《围城》里的几次“社交”不必说了,《人·兽·鬼》 中有 《猫》,作者差不多有一半笔墨花在客厅里的来客身上。以小说结构艺术来说,未可称善,然这里的旁逸斜出或者正是钱钟书的兴味所在。
早有人索隐过了,《猫》 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未尝不可看作小说化的臧否人物。钱钟书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其快感类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趣一个”,故我们大可不必津津于对号入座。“骂人”之为艺术,常在其“艺术”的自足,就像“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我们首先当它是句隽语。
“风流”汪静之
新文学初期的人物中,有两个姓汪的都因写新诗而有名——汪敬熙,汪静之——听上去一字之差,我常会混淆。汪敬熙时在北大读经济系,新潮社的成员,后来留学美国,成为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曾任中研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身后名”系于生理心理学,写新诗那茬没什么人提了。汪静之出名时还是个学生,其出名与胡适对这位小同乡(都是绩溪人) 的提拔不无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只有“诗人”的名分,他大红了一阵后就无声无息了。但五四初期的文坛上若是“数风流人物”,肯定先会数到他,而不是汪敬熙。汪静之的诗集 《蕙的风》 乃是新诗中的第一部情诗集,有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上将其与胡适 《尝试集》、郭沫若 《女神》 一起,当作新诗最初的代表,虽然我的印象中,诗集里的诗都没有汪敬熙的 《雪夜》 来得耐读。
直到1984年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杭州访了汪静之之后,我才将二人对上号。而这时汪静之早已被人遗忘,对我们而言,他也只是个很无感的名字,要说“风流人物”,那是徐志摩吧?有个师妹好像写过有关文章,我们一伙人还跟着去了趟海宁,寻到徐志摩的墓,凭吊一番。富阳县也走了一遭,那是为了访郁达夫的故居。
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研究生经费居然够我们为时半月游学江浙。但我们谁也未曾想到去访访汪静之,虽然他还在。我们后来是听骆寒超老师的建议去访的汪静之。汪静之一点也不“人物”。他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楼道里堆满杂物。一位老妇应的门,后来在屋里还见到一位,两位腰都有点佝偻了,也不知哪位是他太太。都不大吭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们其中的一位就坐在过道里摘菜。我们留意她们是有缘故的:《蕙的风》 就是写给他追求的女子,虽然求之不得;后来追到的是另一女子,因诗人已出名,他的太太也便像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汪静之长得很矮小,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老头的样子,敝旧的衣服,好像还有点酒糟鼻。好像并不是我们有意八卦,他自己就说起他的情史,扳着手指数出好几个他追求过的女子。听他讲当年风流,我时不时地开小差,仿佛怎么也不能将眼前的糟老头子与当年大红大紫的诗人对上号。
那日从汪家出来,几个人一路都在笑。汪静之扳着手指历数他的恋人,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排花榜似的,太有趣了。难得有位曾经的名人肯八卦自己。算起来他那时应该七十来岁,大概一向也就是那样一派天真。
三十年代,汪因为章依萍引荐到暨南大学教书,据说与许多“望之俨然”的教授相反,他是全然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有学生问 《蕙的风》 其名何来,他便滔滔不绝说他理想的爱人叫傅蕙兰,诗就是为她而写,求之不得的过程,原原本本地道出,连带着把与现夫人的情史也一五一十道来。课上学生与他驳难,或是搞恶作剧,他也不恼。未见其人时,学生对这位 《蕙的风》 作者自有所待,意中必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待见了面则难免失望,后来皆称之为“汪诗人”,就颇多调侃的意味了。
以那天趋访得来的印象,我不大好想象他怎么讲课。他授课倒庶几是诗人式的:他开的课叫《诗歌原理》,让学生每人买一部他的诗集,不大讲“理”,每讲原理则“就近取譬”,放声朗诵他的诗歌。他的情史也是可以在课上讲的,他要写的小说,他对现在女人哪里会谈情说爱的质疑,还有因学校减薪时常请假的理由“学校减薪打八折,我教书也打八折”的高论,也不妨在课上一说。率意如此,倒也颇受学生欢迎。假如不能从他这里得到多少知识,总也算是亲炙了诗人吧——以天真、童心为诗人定义的话,他应该算标准的诗人了。
《蕙的风》 即是以天真、大胆、直白的诗风出名的,讴歌恋爱而有几分童稚气。下面这几句据说传诵一时:“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就像看到他的人很难联想到“风流”、“浪漫”一类字眼,今人也很难想象这样的诗句当年能够“尽得风流”,一方面又被卫道士大加攻击。毕竟,那是“恋爱刚到中国的时候”,少男少女也许一读之下即生内心的悸动以至颤栗也说不定。
三十年代章依萍因 《枕上随笔》 中一句“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被骂得狗血淋头,且有“摸屁股诗人”之号,其实原是汪静之所写,未发表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倒觉比 《蕙的风》 的浅白更有诗的意思,虽说格调不高,还谈不上美学意义上的颓废。
其实汪静之的人与诗是一点不颓废的。
张荫麟“专打天下硬汉”
“数风流人物”而造出的佳话,凡并称者,多半有主角有配角,居于后者往往只是陪衬,凑数而已。清华外文系“三杰”中之颜毓蘅,论名声、成就,远不能和钱钟书、曹禺相比,固在“龙虎狗”的排序中已见端倪,“四子”中的杨世恩则亦不能与朱湘、孙大雨等相提并论。
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四才子”虽然也是八卦性质,四人中就没有一个弱的,学生时代即露圭角,日后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钱钟书不必说,吴晗,史学名家,夏鼐,考古方面的权威。只有张荫麟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其才,然半部《中国史纲》已成经典,而当日的才名似更在吴、夏之上。张殁后,钱钟书作 《伤张荫麟》,有自注云:“吴雨僧师招饭于藤影荷声之馆,始与君晤,余赋诗有‘同门堂陛让先登,北能南秀忝并称之语。”可知当时另有将张、钱二人并称的说法,较之“四才子”说可能是小范围流传 (因今人称引,尽出于钱诗),以南宗北宗大师喻二人,其推许更是不同寻常。钱钟书公开发为文章与诗,一向持论苛言,《伤张荫麟》 一诗则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意。若当年赋诗有酬酢成份,多年后重提“忝并称”之句,则说明他之乐于接受这样的并称。
张荫麟与钱一样,也是心高气傲之人。与他交情颇深的吴晗说他“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我们可从他二十年代的书评中领教他“毫不客气”的犀利。钱钟书有言,二十不狂是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没头脑。张荫麟书评的气盛言宜,正见出他的“志气”。其与钱钟书年轻时代书评相通处有二,一是词锋凌厉,不稍假借,二是并非柿子拣软的捏——正相反,端的是“专打天下硬汉”。钱初出茅庐即挑周作人等大人物的错,张荫麟“打击面”更大,冰心、苏雪林等辈犹其小焉者,张东荪、郭沫若、冯友兰、顾颉刚、胡适、梁启超等人均是他指谬纠错的对象。而且他不是盯着大人物偶然之失的小疵 (他考据功夫了得,然其评论予人印象深刻处却不在此,对枝节性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为他所不屑),若谓之“逞能”,则他的“逞能”必在大处落墨:有所攻均是往方法论、概念之类的要害处招呼,往往令对手难以招架。
张荫麟四面出击,所评论者覆盖文、史、哲三界多个领域,当真有“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味道。初试啼声,他就拿梁启超开刀,在 《学衡》 上发表的 《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一文,就梁启超断 《老子》 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条批驳,时年十八岁。他批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指其误用“默证”且直斥其疑古文章近乎策论家之罔顾事实、但为我用:“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名动一时,他指其定义混乱,主观武断。郑振铎的文学研究更不在话下,在 《评 〈小说月报〉 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一文中,他对郑提出的“新途径”颇多讥诮,指其了无新意可言,“反有令人喷饭之处”。关于冯友兰的 《新对话》,他托戴东原之名指陈作者对朱熹的理解所据有误,且说冯的概念含混不清……
张荫麟不是钱钟书式的幽默家,不过辞锋锐利之外,也时或令人莞尔。比如评郭沫若译 《浮士德》,他说“郭君在近今白话文学作家中,文字尚为明晰可解者”(此语看似肯定,实则将“近今白话文学作家”之文风一笔扫倒),话锋一转,即对译者自诩的“尽善之努力”大加挖苦:“此种不苟之精神,吾人甚乐为表彰。然据后序中所自述,郭君之成此书,不过初译费时一暑假,改译‘仅仅只有十天。倚马可待,固足自豪,然观其译本中谬误之多,吾人毋宁劝郭君不必如此匆匆。人生虽促,然不宜在此等处省时间也。”对冰心等女作家,亦是挖苦到家,他干脆把文坛的捧女作家拟为袁枚辈搜罗女弟子以自娱的行为,而对 《真善美》 杂志上的女才子之文,直斥为“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 antal rubbish”,“以充国文课卷,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如此“毒舌”,如此“恶攻”,并未招来任何打压:张一无以酷评“逆袭”之意,也未见有人指其以骂名人搏出位。这就见出彼时的争鸣氛围。学界大佬们的气度则更令人怀想,梁启超被挑眼后反而对张的才华大加赞扬,冯友兰对张的挑战、揶揄亦不以为忤,放下师辈的身段与张有来有往的讨论。—— 求之于今日,岂可得乎?
冯友兰的大手笔
冯友兰为西南联大写的纪念碑文是一篇震铄古今的大文章。有人这样评道:“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你道“有人”为谁?是冯友兰自己。晚年追忆平生,撰此碑文乃是他平生一件得意事:“余中年为古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事实上冯友兰的文章早就受到推许,试想西南联大那样一个文人墨客汇聚的地方,放着闻一多、朱自清、钱穆、刘文典一干人,若不是早有文名,也轮不到他来做。冯友兰以哲学家名世,但他那一辈的人早年都有很好的文言文训练,中年后他又揣摸精研古文,且在这上面有“自期”,这才写得一笔好文章。不仅是文言文,他的白话文章简洁畅晓,也足以让大多数新文学家汗颜,读《中国哲学史》便知。纪念碑文和这部书,一文言一白话,都是大手笔。此所以李慎之在冯友兰去世后的悼文中,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之外,特别提到他的文章:“冯先生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在以白话文写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冯先生的书特别好读,已是学者的公论。因此读冯先生的书不但可以了解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可以学会做文章的本领。”
不过冯友兰先生对自家文章,最自负的恐怕还是他的古文。《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虽戛戛独造,却毕竟是学术论著,不能将文章之美发挥尽致。碑铭、陈情表之类的文章则古来就是高手驰骋,能见高下的文体。此处说到“陈情表”,盖因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之外,1943年冯就时局上书蒋介石的陈情书,也被推为“当代大手笔”。其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员教授会议要给蒋介石上书于时局有所建言,公推冯友兰执笔。冯文写就,众教授读罢均大为称赏,雷海宗且对冯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信中肯定有立宪的要求,据说蒋介石看后“大为动容,为之泪下”,甚且有推行立宪之意 (参看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是不是读书人的一厢情愿,不得而知,但此陈情书的情理俱到,言辞恳切可以想见。
可惜,这样一篇至文,居然失传了。
(选自《东鳞西爪集》/余斌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