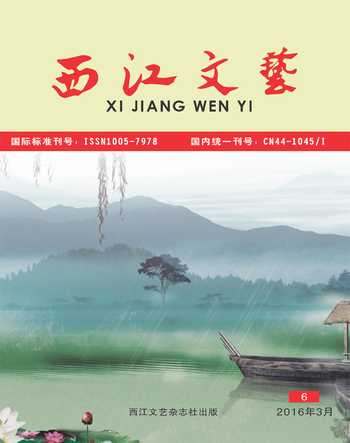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佛教
明晨
【摘要】:利玛窦是十六、七世纪来华传教人士,《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了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所见所感,他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光去审视中国,以偏见的眼光来介绍佛教,重头到尾都将之斥为“邪教”。利玛窦的偏见无疑与其作为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攻击佛教争取教徒的意图有着莫大关联,显示了利玛窦的宗教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佛教;《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
一、利玛窦其人及《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年间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发展了徐光启等知名士大夫,被尊称为“泰西儒士”。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所著甚多,,誉为“东西方交流第一人”。《利玛窦中国札记》详尽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利玛窦来华宣传天主教,必不可少与中国佛教和道教两大宗教接触。本文试图通过《利玛窦中国札记》来了解利玛窦眼中的佛教,并分析利玛窦中国佛教观的根源。
二、利玛窦眼中的佛教
利玛窦初至中国将自己打扮成“西僧”形象,但是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由“附佛”逐渐转向“辟佛”,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佛教从佛、法、僧三宝角度进行了全方位性的批判,力图构建基督教自己的权威,扩大影响力。
1、佛教教义与宗教仪式
利玛窦较早认识到佛教与基督教具有相同之处,因此来华初期,利玛窦将自己打扮成“西僧”的形象,以“和尚”自居,对佛教加以利用。但是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利玛窦则做了相应的调整,鼓吹佛教教理来自西方,佛教的大量理念是“从西方借来的”的思维。利玛窦以佛教的宗教仪式为例, “一些非宗教的礼节在某些方面,和我们教会的仪式很近似”,针对佛教的诵经和塑像,利氏认为“格里高利式的唱经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庙宇里也有塑像,他们献祭时所穿的袍服也和我们差不多。”[1]利玛窦举出由于两者的相似性,撒拉逊商人“误认为这个民族信仰基督教。”[2]同时利玛窦认为中国佛教教义体系不完善,易误入歧途,“原始的宗教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模糊,以致当他们放弃对那些没有生命的神灵的迷信时,很少有人能不陷入无神论的更严重的错误之中。”[3]他以基督教的灵魂永生的观点否定了佛教的转世轮回的观点。
2、寺院僧侣
利玛窦在札记介绍了寺院僧侣的来源,“来自最底层的群众,年幼时就被卖给和尚们为奴。他们由做奴仆而成为弟子”。[4]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者,不遵循清规戒律,甚至为非作歹,“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5]同时弟子“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6][7]利氏在参观南华寺时,也得出这样的言论:“有的和尚过着放荡的生活,有很多子女;还有许多和尚拦路抢劫,使得行旅不安。”[8]利玛窦指出,有许多和尚住在皇城中,名声显赫。他们不仅把百姓、显贵、后妃“引入歧途”。“还从富有的太监那里征集大量的资金”。[9]通篇之中,利玛窦将佛教僧侣描绘成一群不守戒律、为非作歹的恶人。但在另一处史料中,利玛窦又提到“虔诚的信徒坚持吃斋,并供奉偶像经常祈祷。”[10]可见利氏间接承认佛教徒中也有许多信仰坚定的信众。
3、佛教寺院与寺院活动
由于得到广大信徒的供奉,尤其是王公大员的捐奉,修建寺庙和塑造偶像活动极为频繁。而在利玛窦眼中却是“寺庙装饰奢华,偶像面目狰狞”, “庙旁有高塔,塔中有贵重的大钟和其他宗教用品。”[ 11]庙中的偶像“身躯巨大、面目狰狞”。而利氏所言偶像“面目狰狞”,在寺庙中以驱魔伏妖为职责的神灵,其面目看上去表情凶狠,但这是对妖魔邪恶凶狠,并非是对芸芸众生。更多数神灵塑像是以慈祥和蔼的面目出现,如弥勒佛、观音菩萨等。利玛窦攻击佛教偶像面目狰狞,无疑出于辟佛的需要,充斥着偏激的感情色彩,并非客观、理智的介绍。
利玛窦认为寺院过多参与了世俗活动,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异端势力充斥佛教,寺院成为嚣嚣之地。在介绍寺院时,他提到了“每个成员在他任职的岗位上都可以随意建造多少房屋……这些房间以低价租给来求指导的外人。这一习俗的结果便是,这种普通住房原是用来作为宗教中心的,但看起来却像是嘈杂的大旅店,人们在那里聚会,花费时间来崇拜偶像或学习这种邪教教义。”[12]利氏还提到在韶州的教堂建起后,当地的民众把教堂当成寺院看待,“要把这所房子当作他们崇拜偶像的庙宇那样来用,庙宇老是大开大敞着而且常常是轻浮闹事的地点。”[13]在他眼里,佛教寺院没有自己清规戒律,显得很“轻浮”。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卷第一章《传教团又恢复了在韶州的新居留点》,他提到在购买光孝寺附近一块空地时,“官吏已经收了寺里方丈的行贿,”故而官吏在索价时把价格提高了十倍。[14]在第五卷第二十一章《利玛窦墓-中国皇帝的赐地》,他还提到一位皇宫宦官被判死刑,“为了挽救他乡间的别墅不被夺占,”而将之改为寺院。而利氏已经清楚了解到“建造私人寺院是违法的”,但很多权阉在官员的默许之下修建这类寺院,寺院悍然参与众多违反乱纪的活动。[15]
4、佛教与士大夫
士大夫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特权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占据了优势地位,若能争取到士大夫的支持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大有益处。而许多士大夫与僧徒交往甚密,利玛窦较早认识到了这点,便夸大佛教与儒教隔阂,以便拉拢士大夫,剔除佛教影响。儒教伦理与佛教教义之间固然存在着分歧,但是经汉晋以来的融合,两者的冲突渐趋弱化。但利氏旧话重提,夸大两者分歧,“当时的中国儒家有告诉我们……凡是与之有关的事物最后都衰亡了。儒家指明,释迦所许诺和吹嘘的那种好运,国家不仅没有得到反而经历了无穷的灾患。”[16]在参观南华寺时,他特意记录了一位官员言论,“这些寺里的和尚声名狼藉……他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也和他们的全然不同。”这位官员深信“(除了儒教)教义之外,别无他教”。[17]而在和李贽的一次辩论中,利玛窦亲身感受到佛教对于佛教的一些分歧。利氏写到李本固“赞成偶像崇拜而反对儒家祖师孔夫子的学说”,而在场的一位儒学官员“大声抗议”,认为“这是很不得體的”。 [18]而另一位儒学者李挚,“剃光了头,当了和尚。”并“纠集信徒,写书攻击士大夫的领袖们,赞扬偶像的辩护士。”但他被逮捕押送北京,因不甘忍受屈辱而“用刀自刎殒命了”。[19]利玛窦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几分幸灾乐祸,他认为这是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的失败,无疑警世士大夫信仰佛教大无所利,反遭其祸。在认识到儒佛之间的分歧之后,无疑会加深利玛窦“合儒斥佛”的思想。
虽然政府明令禁止僧侣与士人交往,两派之间有很多的分歧,但佛教的思想仍会影响到士大夫。所以利玛窦断定由于佛教观念在知识阶层中的渗透,士大夫们“以为神就是物质宇宙的灵魂,就仿佛是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颗心灵那样。”[20]争取士大夫摆脱佛教束缚成为利玛窦传播基督教的重点工作。
三、利玛窦佛教形象的分析
利玛窦对佛教态度有一个大转变,“在晚明,佛教徒声誉不好,时时受到士大夫的攻击,聪明的利玛窦很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正是利氏等辟佛批佛的原因之一。”[21]但需要指出的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对佛教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敌视的。在札记第二卷第六章提到,他们刚入内地时,将官员所送的两块牌匾“仙花寺”和“西来净土”悬于教堂門楣上,此举意在表明自己的“方外”身份,消除地方官员对他们的嫌疑与警惕。利氏也很得意地写到“这两块匾大大提高了神父们在各阶层百姓中的声望。”[22]很显然两幅题词将天主教与佛教归为同类,而利氏也很坦然接受。如果这样无法说明此时利氏对佛教的态度的话,那么另一行为就十分明显了。1582年他初次到肇庆时,比附于僧侣的,剃须去发披架装,“玛窦初至广下舶,晃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23]。显然是一副云游四方的“西僧”模样。“但首批传教士不久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末尚存的佛教不受知识精英赏识”[ 24],故而有意疏远佛教人士,尤其是1596年利玛窦换上儒服之后,就开始了激烈的“辟佛附儒”。
文化间的差异造成了天主教与佛教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像斯宾格勒所说“两种不同的文化,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25]被隔开的文化的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利玛窦最终选择了一条“补儒易佛”的文化传教路线,把天主教与佛教的矛盾凸显出来。[26]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也使得利玛窦在理解佛教教义上,有很多缺憾,“由于他……并不理解佛性体现于万物中的观念,更不明白佛教徒视万事万物为一体,且可将此移至意识之中的信念,是利玛窦成为佛教和道教不可调和的敌人”。[27]利玛窦与三淮的辩论,与袾宏等人论战,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佛教的教义和礼仪等方面。所以说,利氏对佛教的批判是一种直观的、不深入的、简单的以基督教的立场为基点的批判。
传教士所确定的“补儒驱佛”策略是利氏排斥佛教的指导方针。“他却毫不掩饰地对佛教表示反感。也许这一态度追本溯源至耶酥会为布道而确定的策略性警句‘补儒驱佛”。[28]作为一名虔诚地执行其传教使命的传教士,利玛窦对佛教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因为佛教是一种正式的宗教,拥有最多的信众和教徒,而佛教徒在他看来都是偶像崇拜者,利玛窦把佛教视作天主教在中国的对手。其他宗教,如道教,因其竞争力小而较少受到利玛窦的激烈排斥[29],如能对佛教的批判获得成功,则必然会扩大基督教在华影响,起到其他宗教批判所起不到的作用。
在对待佛教人士态度方面,利氏有很多情绪化的因素。“在佛教与天主教的关系中,佛教的态度是开放的”。面对利玛窦咄咄逼人的态势,从文献资料来看,较少有大幅度的文章来回击利玛窦的挑衅行为[30]。天主教与佛教关系的破裂的主要责任在天主教一方。”[31]利玛窦“在表达摒弃佛教时的粗暴语气,这与他一贯十分高雅的姿态格格不入。”[32]可见,利氏对佛教的批判带有很多的个人情绪。
四、结语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对佛教的非难,必然会导致佛教势力的反击。佛教文化在两汉时期传入我国之后,到明代,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它已经和中国文化充分融合。中国文化在“摄取了佛教以后,便使中国思想界扩大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和阳明学。”[33]传教士对佛教的仇视,对佛教文化的激烈批判,必然会走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从而导致士大夫的敌视。事实上,不久佛教势力很快就与士大夫联合起来了,公开批判天主教。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难”爆发,儒家学者与佛教僧众向天主教修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批判运动。晚明中国佛教的确出现了衰颓的现象,佛教义理无有发展,佛门风化败坏,黄宗羲批评到“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付,聚群不逞之徒,较之以机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宁止洪水猛兽哉”[34],但更应看到佛教主流劝人为善恪守教规,利玛窦书中列举大量实例,从头到尾都将佛教斥为“邪教”,实际上反应的是作为一名天主教传教士的利玛窦在与佛教争取教徒中不惜抹黑中国佛教,是利玛窦狭隘宗教观的表现。
注释:
[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6页。
[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43页。
[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7页。
[4]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8页。
[5]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8页。
[6]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8页。
[7]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8页。
[8]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37页。
[9]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7页。
[10]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9页。
[11]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8页。
[1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9页。
[1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5页。
[14]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1页。
[1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633页。
[16]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7页。
[17]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39页。
[18]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64页。
[19]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6页。
[20]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 第369页。
[21]李新德:《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
[2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3页。
[23]张尔歧:《篙庵闲话》,丛书集成初编,第12页。
[24](法)谢和耐著、黄建华译:《中国社会文化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25]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53页。
[26]韩月香:《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肇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7](德)弥维礼:《利玛窦在认识中国诸宗教方面之作为》,《中国文化》1990年2期。
[28](德)弥维礼:《利玛窦在认识中国诸宗教方面之作为》,《中国文化》1990年2期。
[29]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30]戴继诚:《利玛窦与晚明佛教三大师》,《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2期。
[31]王公伟:《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11月。
[32](德)弥维礼:《利玛窦在认识中国诸宗教方面之作为》,《中国文化》1990年2期。
[33]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页。
[34]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