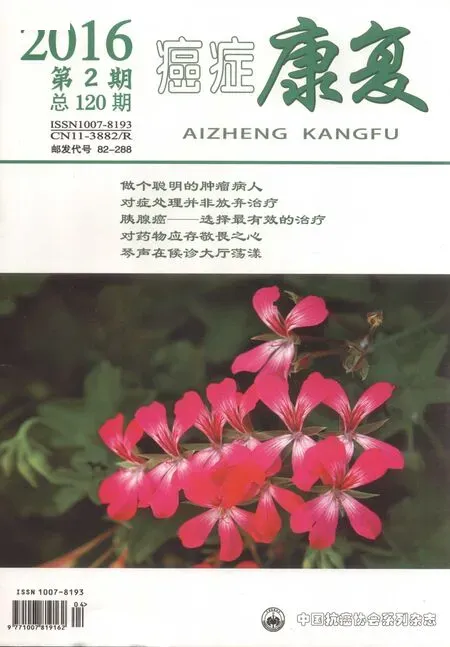深度对话刘端祺教授慎始敬终:缓和姑息医疗让生命画上圆满句号
□ 矢车菊
深度对话刘端祺教授慎始敬终:缓和姑息医疗让生命画上圆满句号
□ 矢车菊

刘端祺教授现任《癌症康复》杂志副主编,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康复部主任,北京癌症康复与姑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近10余年主要从事肿瘤的综合治疗,尤其是肿瘤的姑息治疗。
日本著名电影《入殓师》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将尊严还给死者,以及生者如何通过最后的优雅仪式与死者和解、告别。
死亡,通过入殓师的出色工作变得不再可怕,并使其与生命成为连续的整体。《入殓师》第一次以电影的方式温暖地向我们展示了生命需要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今,在医学领域,一门给生命画上圆满句号的学科——缓和姑息与临终关怀学科正在悄然兴起,尤其在癌症患者和医生群体中更是被频繁提及。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记者采访了缓和姑息医疗领域的专家——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北京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端祺教授。刘教授是我国较早关注缓和姑息治疗的内科学专家,他平易近人、谦和朴素的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教授结合自己的从医经历,生动全面、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解读了缓和医疗的意义。
记者:目前缓和姑息医疗在国内医疗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您是何时开始关注并将研究方向锁定该领域的?
刘教授:这主要源于我的经历和阅读与思考。从我踏入医疗行业到现在已经50年了,这段从业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20多年做消化内科医生,后面20多年是肿瘤科医生。首先,作为内科医生的那段时间,虽然也见到过很多医治无效最终走向死亡的患者,但对于患者的缓和姑息治疗以及临终关怀问题还不是十分关注。后来多次去农村和部队,也在国外(欧洲、澳洲等)参观过一些相关的医疗机构,并阅读了一些书籍和文献,逐渐地感觉到我国医疗界在处理患者死亡的问题上与先进国家存在不小差距。长期以来,我们在提倡“优生优育”的同时,却忽略了“优逝”——对患者的临终处置过于粗糙,既没有基础研究,也没有从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出有指导意义的经验。
其次,在我当了肿瘤科医生以后的20年间,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死亡患者。目前发达国家的肿瘤治愈率已经达到60%~70%,而我国则有70%甚至更多的癌症患者一经诊断就是晚期,大多数人最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优逝这个问题就非常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忽视了优逝的医学,不是完整的医学;没有优逝的人生,也不是圆满的人生。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优逝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我国大多数医院还处于集市般的粗放管理阶段。说起来,医学不完全是自然科学,它是自然科学当中最有人文情怀的一门学科。所有的自然学科当中,大概只有医学是以人的生死为研究和服务对象的,所以它必须要有人文情怀。从这个角度来讲,医生一定要做一个既关心病更要关心人、既关注生也要关注死的有人文情怀的完整的医生。如何关心一个面临死亡的人,这是摆在每个医生面前的一道试题,它牵涉医学的本源、医生的天职,是我在行医过程中一直琢磨的事。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我在西北地区工作多年,耳濡目染,看到不同的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很值得探究。汉族人群通常很忌讳死亡,如果一个人离世,亲人们往往在葬礼上哭得呼天抢地,悲痛欲绝,难舍难分;但紧接着又非常忌讳死者的遗物,常把死者生前用过的东西都抛弃、烧掉,死者生前住过的房间不敢去住,反映了对死亡的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汉族截然不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东乡、哈萨克、裕固等几个民族,都提倡居家辞逝,主张人要死在家里,要在家中享受临终前的那种温情,举行宗教仪式,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平静地接受死亡。在人死后的第2天,遗体一定要入土为安,葬礼十分简单、朴素。他们对待死亡是一种很平静、很接受的态度,把死亡看做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做生命的回归。因为理解,所以不再惧怕。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是藏族,他们对死亡的豁达十分震撼人心。在人们死亡以后,会有多种丧葬方式,没有奢华的仪式,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恸哭,基本都不保留遗体。以天葬为例:天葬师把遗体解剖得很细,安放到天葬台上,让周围的秃鹫过来吞食。秃鹫食尽散去,人们在颂经和祈祷中结束葬礼,庆祝灵魂升天。
同样面对死亡,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对待死亡的态度迥异,这也引起了我对死亡的思考——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死亡?
记者:您认为缓和医疗在肿瘤领域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教授:在中国,“缓和医疗”的用词很多,有“舒缓医疗”、“宁养治疗”、“姑息治疗”,老一辈的医学家称之为“姑息治疗”的比较多,后来感觉“姑息”二字比较消极,所以到现在用词还没有统一,但凡提到姑息、宁养缓和、安宁疗护的,都可以看做是舒缓治疗,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患者舒适。而临终关怀则是缓和姑息治疗的最后阶段,它是姑息治疗的重要部分,但还不是全部。
过去国际上曾经把舒缓治疗定义为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现在已经把这个范围扩大了,一切得病的人,对其进行的舒适治疗都可以叫做姑息治疗或舒缓、缓和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只是癌症患者,哪怕一个感冒患者,都可以接受舒缓治疗。对于一位早期癌症患者,医生和家属通常会给予安慰,给他战胜病魔的信心,这种心理疏导就属于姑息治疗的一部分。从狭义上来讲,特别是肿瘤治疗,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对于早期癌症患者通过简单的手术或者放化疗,基本上能彻底治愈,但也需要姑息治疗,比如心理疏导,手术之后要止痛、止吐等。另一种情况,主要针对那些不能彻底治愈的患者,这部分患者的治疗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抗癌治疗失败或者抗癌治疗估计不会再起更多作用的时候,就转成了姑息治疗为主。这会有一个时间的拐点,在这个拐点以前,是以抗癌、消灭癌症为主,以后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也就是舒缓治疗为主。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有一个最根本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文关怀——让患者舒服,尽可能减轻患者的不适症状,而不是以治愈疾病为目的。对于晚期癌症患者而言,缓和姑息治疗几乎是患者治疗的全部。
所以,我认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当癌症发现得比较晚的时候,缓和姑息治疗应当是癌症患者治疗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肿瘤科大夫都应该是缓和姑息治疗的专家,起码应该理解缓和姑息治疗的精华,而不能只懂开刀、开处方,只想着“化掉”瘤子,而不管患者的生存质量。每个医生都应该从那种“匠人”的心态中解放出来,把老一辈医学家人文关怀的精神传承下去。
记者:缓和医疗的治疗理念中,您认为最精华的部分是什么?
刘教授:是人文理念的建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患者的“共情心理”,即我们经常说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相当多的医生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只有自己得过这个病,才知道这病有多么难受。作为医生,对患者的共情心理是十分必要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由于缺乏换位思考和沟通,从而形成了医患互相抱怨的局面。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开始理解并重视这个问题,加入到了缓和姑息医疗的队伍。
记者:在2013年的ASCO会议上,关于使用临终镇静剂的报告中指出,临终时使用镇静剂并不会加速患者的死亡,但会令患者死去得更加舒服。国外好像已经有使用镇静剂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们国内在使用镇静剂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刘教授:提到临终时使用镇静剂,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安乐死问题。这就涉及到社会、哲学、法律这些更大的范围,医生作为参与者之一,只是从医学角度来参与其中。至于晚期患者临死的时候是否使用镇静剂,国内外都认为,原则上是允许的,并不是禁忌的。当然,用不用、什么时候用、用哪种药、用多大剂量,这要看患者,有时候也要看家属的需要。有一部分晚期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非常烦躁的,还有的患者非常疼痛,几乎痛不欲生。这些都需要给予药物治疗,这些药物包括镇痛剂、镇静剂、解痉剂,有的还需要一些激素。这些药物对于濒死的患者都是允许使用的,国际上的看法也比较一致,没有太多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完全属于医学上的用药技巧。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使用这些药物可以加速患者死亡,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可以推迟患者死亡,只是一种正常的减轻症状的治疗而已。所以,无论从医生还是患者,都不要把这些治疗看成是致死的治疗,也不要看成是一种安乐死的实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是从用药目的,还是用药种类或者用药规律上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
记者:什么样的患者需要临终关怀?在实施缓和治疗之前是不是需要一些法律程序,目前有相应的法律吗?
刘教授:如前所述,临终关怀是包含在缓和姑息治疗里面的,是指患者生命走向临终阶段的最后一部分缓和治疗。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开始临终关怀治疗呢?这需要综合考虑疾病发展规律,医生的个人治疗经验以及患者的体质等几方面。对于临终阶段的时间界定,各个国家不太一致。比如美国,在患者距离生命结束还有大约6个月的时候,经社保及第三方评估,认为可以进入临终关怀治疗阶段的,就会在各种治疗的报销比例上做调整,凡属临终关怀治疗的基本予以报销,凡属抗癌治疗的则不予报销或报销比例较小。德国一般是临终前3个月左右。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大体上也是3个月左右。对于肿瘤患者来讲,我认为广义的临终关怀可以从患者的抗癌治疗无效开始(至少算是“准临终关怀期”),向家属及患者本人“下毛毛雨”,进行必要的辞世教育和相关准备。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民间和医生对于临终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医生在疾病方面有预见性,可以大致预计患者的存活时间,在医生的心里面,临终概念比患者家属和患者本人的临终概念要长很多。对表面健康实际病入膏肓患者的预期寿命,家属及患者本人不会想到死期将至,对治疗往往有很高的期望值。这就需要医生跟患者亲属及时沟通,要把患者病情发展的不可逆性尽早说清楚,避免“生命不息,抗癌放化疗不止”,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甚至引起医疗纠纷。
目前我们国家对缓和治疗越来越重视,如对于国际上规定的针对缓和治疗常用的33种药品,在北京已经纳入医保,都可以高比例报销;上海对临终关怀的实施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以阿片类药物为主的止痛药物的使用,我国政府连续发布了10多份文件,使我国癌痛患者得到了初步治疗,国际上对此评价也越来越高。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公益组织,比如李嘉诚基金会,先后与全国30多家医院合作,共同出资成立了免费的居家临终关怀机构——宁养院,大大推动了内地姑息医学理念的普及和服务模式的探索。
记者:一位癌症患者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在面对晚期癌症患者是使用有较大毒副作用的“积极抗癌治疗”,还是采取缓和姑息医疗,谁最有决策权?
刘教授:应该医患双方勤于沟通,共同做主。患者的责任和义务是把自己的病情、需求以及既往就医情况充分准确地表达出来,不能有所隐瞒,也不能给医生错误的引导,要对医生有充分的信任。从医生角度来讲,就是共情,要充分理解患者,尽量考虑患者的需求,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做个体化的医疗决策。这个决策过程应当用文字记录下来,医患双方共同遵循。
记者:很多患者得了癌症之后,家属常常会选择对患者隐瞒病情,我们想听听您对该种做法的看法和建议。
刘教授:国外对于科学素养比较高的患者,一般都主张先告诉患者,而且让患者自己决定再去告诉哪些人,比如说要不要告诉其配偶、领导、同事等,医生是先跟患者商量的。咱们国家正好相反,有的患者甚至到了生命尽头也不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其实这也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那些主张先告诉患者的国家主要基于人权考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们国家主要是出于对患者心理上的保护和民间的传统,二者各有所长。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逐渐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对患者讲真话,让患者参与对自己治疗的讨论。随着时代的变革,互联网的发展,医疗资讯的迅速传播,大多数患者都具备了一定的医疗知识,或多或少会猜到自己的病情。这种情况下,与其让他猜测,不如跟患者坦白说明。按照心理学的研究,患者在最初收到这个消息之后,肯定会有五雷轰顶、世界末日的感觉,但很快就会接受现实,之后便会激起求生欲望,积极配合治疗,而这正是我们临床医生所需要的。
记者:当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每位肿瘤患者第一感觉都是恐惧和绝望。对于肿瘤晚期患者,在您所提倡的缓和姑息医疗的过程中,是否会建议加入一些比如宗教信仰或者其他心理治疗方面的因素?
刘教授: 肿瘤患者的心理问题非常普遍,肿瘤心理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我国有不少医院都建立了心理科,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宗教国家,利用宗教对死亡做积极的宣传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宗教在我国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宗教有宗教的智慧,对于医生来说,可以利用宗教的死亡智慧来引导患者及其家属,使患者能够根据医生的安排积极配合治疗,直面死亡,平静地接受死亡。所以,我认为医生利用宗教的智慧来做好临终关怀,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有两条要谨记:第一,医院可以允许举行
一些不影响他人的简单的宗教仪式,但是绝不能影响到医院的正常秩序;第二,坚决禁止患者病笃期间在医院内部进行传教活动。在宗教人士看来,这样做有趁人之危之嫌,在教义上也是不允许的。
“死非生的对立,而是生的延续”。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在小说《挪威的森林》里对死亡做如此描述。面对生命的最后一程,是选择“好死”还是“赖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在医疗的尽头,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无疑是对逝者最温柔的敬重。
(来源:金琉璃 本文受访者刘端祺教授对文章进行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