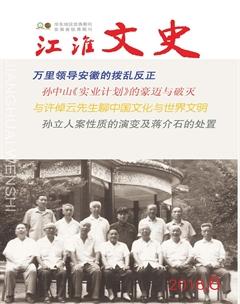“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一
1971年12月26日,星期日。
阴霾的天空、零星的雪花、萧条的街道、涂满红色标语的楼房……一掠而过,这就是卡车上被五花大绑的“囚犯”所能看到的一切。车队浩浩荡荡,正在执行“巡回公判”。
高音喇叭朗诵一段冗长的“毛主席语录”后,便开始宣读蚌埠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布告,每读到一个“囚犯”的名字,该人便被抓住头发、令其抬头亮相——清一色年轻而苍白的面孔!接着,按照当年统一的“剧本”、传统的“台词”,依次逐个宣判。我是本案第一个亮相者,因为我是“首犯”,更确切地说,我是B角“首犯”,因为A角王汇元不幸猝死。
1971年已是“文革”中期,在我们之前,蚌埠市的公判大会不计其数,尽管此类“政治活报剧”语出惊人,“剧情”跌宕起伏,却总是脱不了狠狠打击的那一套,正如老把戏一样,早被人们看腻,观众自然寥寥。然而,由我主演的这出“政治活报剧”却意外的盛况空前,连日来,在市体育场、市文化宫等地“巡回公演”13场,场场爆满!其原因是大喇叭中宣布的罪名令人耳目一新——“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人们急欲弄清这“俱乐部”与“反革命”本是不相关的两个概念,如此合成在一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俄罗斯民歌《小路》,那婉转的旋律从一台陈旧的电唱机中发出,大概是由于机子太老,黑色的胶木唱片明显的转速不足,同响彻城市上空的高音喇叭相比,它的音量未免太微弱了。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斗室中,十几名青年却已陶醉在这优美的歌声中,他们时而为之伴唱、时而为之喝彩——我便是这群青年中的一员。我们之间是同学、朋友关系,都是个人成分不好者,这种“贱民”身份注定不能升学,辍学后偏偏又赶上“大跃进”后的大萧条,就业无门,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我们都出生于抗战胜利前夜,即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当年为避讳“失业”二字,被泛称为“社会青年”。毕竟我们接受了几年相对正统的苏式教育,在思想上、认识上、行为上相对活跃,我们酷爱文艺,对“文革”中的种种荒诞现象深恶痛绝,私下也曾有过议论和抨击,但我们更多的时间则用在读小说、听音乐上面,也是我本人当年苦中作乐的“自画像”。然而,上述正常的文娱活动在当年也是遭禁的,就在我们倘佯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之上时,危险正在逼近,“曲曲弯弯”竟然一语成谶,预测出我们的人生之路将会崎岖而坎坷。
三
1970年4月24日夜,按照当年安徽省革委会统一布置,“蚌埠市群众专政指挥部”倾巢出动,对全市进行“政治大清查”(俗称“政治大扫除”),一夜之间捕人无数。在这次“政治大清查“中,有一位《小路》的听众被抓,此人从事照相行业,这个职业决定了他外向的性格和广交朋友、口无遮拦的作风,在政治风暴中被当作“出头鸟”则不足为怪了。
1970年5月28日夜,“政治大清查”已过月余,在葡萄糖厂打临工的我,刚脱下肮脏的工作服准备下班时,突然被驻厂军代表叫住了,宣布“从今天起进学习班,不准回家”,我当时竟出奇的镇定、坦然,脑海里只闪现一个字“咬”——我被人“咬”了!“咬”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注释:一是“上下牙齿用力对着”;二是“受责难或审讯时牵扯别人”。这第二种“咬”最为狠毒,因为它“咬”在神经中枢,“咬”在意识形态,“咬”在灵魂深处,我所遭遇的不幸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
更为可悲的是,在那名曰“学习班”的班房里。在头顶上300瓦灯泡日夜照射下,面对军代表提供的来自“咬”方的检举,我丧失理智,竟然“反咬”起来!“你不仁,我不义”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第二种想法也是最天真的想法——你军代表就算掌握了我听“黄色歌曲”,传“小道消息”,充其量也只能将我划为“落后分子”,没有真凭实据,你总不能定我“反革命”吧。然而,最终发现我错了,不仅定了案,而且成了轰动全市的大案要案!
四
2个月后,即1970年盛夏,当年《小路》的听众、今天的“囚犯”共15名被集中在市一级的“学习班”,由于公检法已被“砸烂”,这里只有一个笼统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对敌斗争学习班”。
这是一大片黄豆地,东北侧有几排荒废多年的灰色平房,随着来自全市各个角落诸多“囚犯”的到来,这里骤然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我是带着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心理而来的。第二天,一位姓李的班主任发表首次训示,他说:“你们年纪轻轻,不过都是些认识问题,但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改了就好”。这与我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一致,也是符合实际的,听后,烦躁的心情骤然平静下来。此外,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触颇深——“学习班”里有位高某,与我曾有点头之交,此人因有“前科”,作为“死老虎”,早在“政治大清查”之前业已进来,现在他是“学习班”的动力,到处“现身说法”。“彻底坦白是唯一的出路,否则你插翅难逃出这个学习班”;“我已彻底交代,现在完全自由”。这些都是高某的原话。的确,我见到的高某是很自由,对于前途无望的我,所渴求的不就是这种起码的自由权利吗?能回家,继续过我的贱民日子足矣!如此看来,我似乎有了绝处逢生的希望。
总体看来,我所在的这个“学习班”除了非法监禁之外,基本上还是按“文斗”的方式进行的,但今天看来,这正是“李班主”的过人之处,在“政策攻心”战术上棋高一着,“软刀子”诱供得心应手,收效远远超过刑讯逼供!这个“学习班”与众不同,每天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里面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外,其余时间均处于一种松散状态,使“囚犯”们逐渐适应现状,打消抗拒与防范意识。半年下来,在这个名曰“学习班”里,我与“同案”历经了洗脑全过程,于是,为了表现出态度好,大家对各自的“罪行”深挖再深挖,直至江郎“罪”尽,便开始“谄”。因为我对苏联反特工小说看得多了,“谄”得更为离奇,连“企图叛国演习”都“谄”将出来,令人费解的是,如此胡谄滥编不仅未得到制止,反而得到鼓励,我为此还被“解除隔离”,以示表扬。“李班主”当众说“小班子(指‘地下俱乐部案)的态度普遍好”,这样一来,唤起“囚犯”们奋笔疾书,自诬自毁,甚至出现检举者与被检举者有说有笑的奇特现象,纯粹把写“交代”材料当作儿戏!
不久,另一个案子的“首犯”姚某因“认罪态度好”被当场释放(实际上出了大门便被正式逮捕),事后,“副班主”开会当众宣布“你们回家过中秋节来不及了,看来你们可以回家过国庆节”(相差16天)这一“特大喜讯”,再次掀起“学习班”的“交代”热潮。由于我们的“集团”缺少名称,为适应“一打三反”的形势需要,大家便顺着“李班主”设置的“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的竿子往上爬……
如同今天的传销,如果乙被甲作为“下线”骗进来,那么乙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到下线丙,而丙再去拉自己的下线丁……以此类推,这便是商业传销的操作法,如此看来,我是身陷于“政治传销”了!两种传销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洗脑为手段。所不同的是,商业传销中的人们是想一本万利、发财致富,而“政治传销”里的“囚徒”是想超额坦白、恢复自由。人在被长期囚禁、反复洗脑后,似乎真的会出现走火入魔之态,会造就畸形人格,甚至不可思议的自诬自毁……无论是商业传销还是“政治传销”,最终必然是图穷匕见、骗局一场,待到清醒之日,则悔之晚矣!
五
人被囚禁,度日如年。
“十一”早已过去,“国庆节回家”的许诺迟迟未能兑现。就在这时,“学习班”出了一件大事——“囚徒”平某,因感委屈、前途无望而自缢身亡!这一突发事件给“李班主”造成了压力和急于结案的紧迫感,而日积月累,“李班主”案头上的供词堆积如山,如何将这些无中生有的供词弄假成真,而且要在极短的期限内完成,“李班主”自有“快刀斩乱麻”的绝招——对材料!所谓对材料,正如学生对答卷一样,将与某个问题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由其中一人当众朗读他的交代材料,其余人记录,由于这些朗读的供词多为编造,被提到的“在场证人”当然毫无印象,但既然人家自己都承认“恶毒攻击”,我又为何不能“证实”一下,落个态度好呢?于是便提笔照抄,如此你朗读过来,他抄写过去,一条条“罪行”便很快落实了!
六
结案之后,便进入听候处理阶段,奇怪的是,冬去春来,处理之日仍遥遥无期。更令人费解的是,“学习班”似乎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地下俱乐部”成员居然能围坐谈天而无人过问!更有甚者,我单位“办案人员”马某单独见我,劝我“翻案”!这话竟然出自我的对立面——办案人员之口,我感动之余,实在大惑不解!多年后,我才知晓上述怪现象的缘由——原来正是那个多事之秋,外面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蚌埠市群众专政指挥部”已被撤销,极左政策已经开始纠正,但军管会尚存(一年后撤销),他们拒不放弃其战果。据1993年出版的《安徽省志·公安志》记载,当年公检法军管会办案原则是“一人供听、二人供定、三人供判”,而我们“对材料”产生的假供词大大超出这个标准,必然在劫难逃。为防夜长梦多,军管会草草结案,硬是赶在年底之前,将我们按“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论处,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游街示众的一幕。
七
9年冤狱,终于等来雨霁云开。在蚌埠市“冤假错案复查办公室”不计其数的申诉书中,“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这个不伦不类的案由引起工作人员的特别关注,促使我们成为全市最早平反的“要案”。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下达的“(79)刑复字第176号”平反文书中写道:
原判认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汇元、郑学斌为首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誘年出于对我党的刻骨仇恨,经常纠集周万年、任遵循、杨华清、高森田、沈大求、李林等人,在一起放黄色唱片,偷听敌台广播,策划外逃,在市体育场、津浦大塘、郑学斌家用恶毒的语言,极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苏修侵略我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们唯恐天下不乱,狂妄叫嚣“只有战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否则“就等于慢性自杀”,渴望战争“早打大打,打起来以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大搞反革命地下俱乐部活动。
案经复核:
1.关于反革命地下俱乐部活动问题。王汇元、郑学斌、周万年、任遵循、杨华清等人,均系同学、邻居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在一起放“三套车”“冰山上来客”“拉兹之歌”“江姐”等唱片,传阅《说唐》《说岳》《三国演义》《复活》《白痴》等古典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无政治活动。原判定为反革命地下俱乐部显然不当,应予否定。
2.关于企图外逃投靠帝、修、反问题。这个问题是郑学斌在学习班为了争做坦白交待的典型,无中生有的假交待,并无事实根据,应予否定。
3.关于极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王汇元等人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形式主义极为不满,但由于不了解情况,上错了账,说了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言论,这是错误的,但属教育问题,不能视为恶毒攻击。
4.关于偷听敌台广播问题。王汇元、郑学斌、周万年等人,曾在刘承业、周忠华家偷听过敌台广播,事实存在,仍予否定,这是错误的,应批评教育。
5.关于仰赖帝、修、反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根据几个被告在学习班的交待材料,断章取义,提高分析认定的,并无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所谓王汇元,郑学斌为首的“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一案,没有事实根据,对各个被告判处是错误的,应予平反,现改判如下:
1.撤销(71)军管刑字112号对王汇元、郑学斌、周万年、任遵循、杨华清、高森田、李林、沈大求、李其昌、平秀洪、朱金保、宋财宝、刘永业、卓天池、毕大庆的刑事判决;
2.对上列被告宣告无罪。
该文书的落款日期为1979年6月29日,而我被“学习班”非法监禁的日期是1970年5月28日,历时长达9年,而这9年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两个凡是”尚未否定,“复查办”显然是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行事的,譬如最敏感的“恶毒攻击”罪名,便十分棘手,但在“复查办”的努力下,人民法院为我们做出了较为公正的结论:“关于极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王汇元等人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形式主义极为不满,但由于不了解情况,上错了帐,说了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言论,这是错误的,但属于教育问题,不能视为恶毒攻击。”
这个结论的措词严谨而巧妙,做到既不触犯“两个凡是”,又达到了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由此联想起我单位“办案”人员马某冒险劝我“翻案”,我认为这是人类的良知所致,是漫漫寒夜中的人性之光!
八
岁月如流。平反时我是36岁,此后,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现在是一名极其普通的退休者。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地下俱乐部”成员并没有因这次事件而反目成仇,除4名逝者外,大家仍然是《小路》的忠实听众,所不同的是,当年使用的唱机是老旧的,听众是年轻的;而如今使用的音响是全新的,听歌人却已垂垂老矣!这不仅只是“一曲难忘”,而是对逝去的青春深沉的追忆。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军管会胡判俱乐部”,这是我在平反不久作的一副对联。今天看来,这样认识未免过于浮浅,我们这起假案固然出自始作俑者的好大喜功和乱世无法,但我仍为在“政治传销”中遭洗脑后的失态而自责,“政治传销”囚徒为争取自由而掀起的“坦白交代热潮”,实际上就是对人身自由的渴望与幻想,而这些白纸黑字的“自供状”,恰恰是自掘坟墓。
值得庆幸的是,在依法治国方针深得民心的今天,无论“抢救失足者运动”,还是“政治传销学习班”等荒唐事件,绝无“再版”之可能。
——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