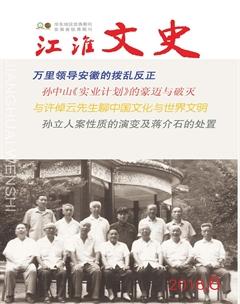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俞小平
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
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构,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接受校“文革”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即使井冈山兵团不承认校“文革”,他们仍然掌握着全校党务、行政、人事、财政、住宿、食堂、物资、保卫等大权,这使得井冈山兵团在北大的派别斗争中从一开始就注定处于劣势。
北大“文革”于我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历时4个月的武斗。这里,我从个人经历描述我所亲历的武斗事件。
北大武斗是怎么开始的?
原新北大北京公社成员,大多将武斗开始的日期定为1968年3月25日开始,那一天“地派”(“北京地质学院派”的简称)率领北京各高校近万人涌进北大示威游行,反对新北大北京公社、支持井冈山兵团。
3月22日,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倒台,聂元梓和校“文革”十分被动,士气低落。25日至26日,外校人员虽然与新北大北京公社人员发生冲突,但是规模并不大,且多为拳脚相向,没有听说几个人受伤,而且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人员大多没有参与。此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下令外校人员退出北大后,事情基本平息,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冲突。3月25日的冲突与其后3月29日、4月26日、7月22日、7月23日发生的武斗相比,在事件的策划、伤及人员、对于运动的影响上,都是完全不能比拟的。3月27日,全校人员大多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规模的北京市革命群众大会,北大的两大派系都去参加了。校内表面非常平静,但是气氛十分紧张,有传言说新北大北京公社要发起进攻,井冈山兵团总部安排各纵队(井冈山兵团的系级单位称为纵队,以各系的编号为纵队编号,如技术物理系编号为第17系,井冈山兵团组织就称为17纵,加上后勤青年工人组成的“海燕纵队”。他们也自称“井冈山人”或“老井”)派人前往28号楼井冈山兵团总部执行保卫任务。3月28日晚,轮到我们17纵值班,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前往28号楼执行戒备任务。
过了午夜,忽然听到外面噪声大起,有同学衣衫不整,冲进楼里说“出事了,出事了”,原来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大举进攻31号楼,把化学系井冈山派03纵的同学打出来了,很多井冈山人受伤,甚至有人跳楼逃跑。井冈山总部立即启动广播喇叭,来自17纵的总部委员程汉良在广播中呼吁井冈山人抵抗新北大北京公社的武装进攻。我们在28号楼的“老井”们组织了二三十人,每人拿了一根大约1米长、1厘米粗的钢筋当作武器防身,向31号楼推进,企图救援受伤的井冈山人。在31号楼南门附近,遭遇了数十名装备精良的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看到我们过来了,立刻排列整齐、手持长矛、高呼口号向我们冲锋。在对手优势武力的冲击之下,我们无法抵抗,只能狼狈而逃,退回到28号楼。稍后,40号楼也爆发冲突,打起来了,当40号楼的“老井”准备去救援31号楼的“老井”时,被早有准备的公社派战斗团堵在一楼楼梯口。“老井”们竟然打败了武装齐备而战力低下的红10团(新北大北京公社的系级组织为“战斗团”,西语系的新北大北京公社组织简称为“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北京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长都被俘虏。“战俘”被押送到28号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28号楼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老井”,也送来了越来越多的伤员,有些人被长矛扎伤,有些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印象深刻是一个陷入昏迷的伤员,他被送来后,放在楼道里的一张桌子上,一直没有苏醒,腰部一片鲜血,看护他的人说他的腰被打断了,不能移动。不久,来了救护的卡车,把这个伤员连桌子一起抬上卡车,送到医院去了。天快亮的时候,我顶不住困乏找了个房间去睡觉,尽管外面两派大喇叭已经吵翻了天。
井冈山兵团认定3月29日的武斗是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策划的。这次武斗之后,聂元梓的朋友、同为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清华大学团派头头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中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策划、发动武斗的阴谋,迫使中央表态,借以打垮井冈山兵团。后来,中央表态了,谢富治支持了发动武斗的校“文革”,谴责了损失惨重的井冈山兵团。但是“老井”没有垮,井冈山人熬过了最初的打击,撑了下来。
把3月29日凌晨发生在31号楼的攻击称为武斗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不是双方对阵的武斗,而是新北大北京公社编练的专业武斗队,对31号楼井冈山03纵的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校“文革”企图一举打垮井冈山最强大的一支纵队。新北大北京公社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重创03纵。当夜井冈山兵团至少有100多人受伤,很多“老井”被俘。但是这种偷袭式的强暴,也激起了井冈山兵团的同仇敌忾、奋起抵抗,最终使得北大“文革”走向大武斗的不归路。当夜对着我们冲锋的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从武器、装备、组织到后勤,都占了巨大优势。其后几天,一个“老井”给我看了他们从新北大北京公社派那里缴获的一支长矛,那长矛外面是橙红色涂层,显然是用无缝钢管原材料截取的,长约1.6米,比我的身高(1.78米)略低些,直径约2厘米多,顶端焊有一段约15厘米长、1厘米粗的钢筋,钢筋顶端用砂轮磨得锋利无比,闪烁着冷酷无情的钢铁光泽。这是此前北大两派冲突中从未出现过的武器!这样的利器刺出,足以把一个人刺个对穿,取其性命!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当权派,有权、有钱、有物资,他们卡住一部分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不发,给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成建制地装备棉军大衣、柳条帽、长矛,后来更以昂贵的不锈钢板材成批切割做成护胸甲,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他们都有了。井冈山兵团有什么?无奈之下,只能锯下楼内的暖气管做长矛,模仿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也在暖气管上焊上钢尖,头戴规格不一的柳条帽,身披材料不同的护胸甲,披挂上阵,应对不时前来冲击的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
在3月29日武斗之前,无论发生过什么事,对北大人的生活整体影响不大,这次武斗之后,大批师生员工逃离北大。3月29日当天,40号楼的小南门被校“文革”封锁,逃难的人群推倒了校门旁边的一段围墙,越过豁口逃生。我所住的41号楼挨着武斗现场40号楼,再住在那里很不安全了,我就把一些细软送到朋友家里,把床上的被褥和洗换衣物扛到28号楼去了。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副司令李钟奇来到北大制止武斗,听信的全是一面之词,井冈山兵团被人袭击,反而数落井冈山兵团的不是。这样的调解无以服众,也没人服从。双方的“战俘”倒是都被释放了,连被校“文革”抓去,残酷刑讯逼供的樊立勤也被从44号楼的新北大北京公社总部扔了出来,因为樊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校“文革”怕他死在他们的刑讯室里没法交代。
樊立勤事件
说到樊立勤,他可是北大“文革”时候的名人之一,当时在北大无人不知。樊胆大包天,不但挑头反对聂元梓,而且敢于“炮打”势焰熏天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因为反康生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1966年底,只有两个小组织“井冈山”(这个组织是“井冈山红卫兵”,不是“井冈山兵团”)和“红联军”支持他。北大的大多数人觉得他的观点太极端,自从他“炮打康生”,做了“现行反革命”以后,敢于支持他的人就更少了。1967年8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时,总部接纳了支持樊立勤的“井冈山”、“红联军”,但是没有接纳樊立勤。聂元梓更视他为“反革命分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8年3月下旬,校“文革”广播台突然放风,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樊立勤外逃,跟着就发出通缉令,实际上他们已经把樊秘密绑架抓捕,在44号楼刑讯室里私刑拷问逼供了。新北大北京公社的打手们在刑讯室里以骇人听闻的酷刑,强迫樊立勤承认校“文革”横加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樊宁死不从,新北大北京公社的打手们竟然以铁钉钉入膝盖、竹签插入指甲等酷刑将樊拷问了两天两夜!6月初,我去北大附属三院看一个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打断腿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樊立勤就在隔壁病房。我从窗口看到樊满身通着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樊立勤被救出以后,在三院住了很久。1968年8月“工宣队”(“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校后,又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直到1969年3月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后,才将樊送去医院治疗。樊的膝盖矫治手术失败,落下了终身残疾。1969年,我和几个同学在北大南边的海淀巧遇樊立勤,大家见他终于“出来了”,都上前问长问短。问起他的伤病,他挽起裤管,给大家看他膝盖上的铁钉留下的痕迹,大家都痛骂校“文革”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
校“文革”的围剿
和井冈山兵团的反围剿
武斗开始以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日益压缩井冈山兵团的生存空间。井冈山兵团的人去食堂吃饭被打,到海淀购物被打,在校园里走路也被打。4月26日爆发了第二次大武斗。这一次,新北大北京公社重兵进攻,井冈山兵团固守36号楼,使得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群能够从校园内部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和广播台所在的28号楼,到海淀路边的37号楼连成一线,保住内外交通线,打破校“文革”的封锁,得以苟延残喘。
1968年8月武斗结束后,我手绘了一张北大武斗形势图寄给我的父母,如今是一件难得的文物了。地图最南端是北大校园南墙,墙外东西向的海淀路是进出北大学生宿舍区的唯一道路。所有武斗割据的楼群,除了井冈山兵团总部的28号楼(原为越南留学生宿舍楼,越南留学生离开后基本空着)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总部的44号楼(原为北大招待所),都是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宿舍楼。井冈山兵团在28号楼西南端与30号楼东端之间的4楼架设了天桥,离地十几米高,各楼地下挖通了地道,地面各楼之间的甬路用双层床联通,以遮挡新北大北京公社弹弓的袭击。
新北大北京公社同学回忆说,他们的人被井冈山兵团的弹弓射出的砖块打破了头,在此,我愿向被打伤的新北大北京公社同学道歉,那时我们双方都有点失去人性。我所在的班的“老井”,为了在楼群之间架设双层床,要不断躲避新北大北京公社同学的弹弓,梁某某被弹弓射出的石块打在胸口,好半天喘不出气来,胸口疼痛多日;陶某某被石块打在额头正中,一时血流满面,送到北大附属三院做了缝合,武斗结束后伤疤仍在,好像前额长了第三只眼晴。
我所在的班级,井冈山兵团的成员有30多人,在武斗中有3人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抓捕。第一个是郭某某,3月29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攻打31号楼时,郭路过附近,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拦住,问明是井冈山兵团成员,就抓进新北大公社总部44号楼,酷刑拷打,以致打断了腿,昏迷不醒。4月初双方交换“战俘”时才放出,送到北大附属三院医治。我就是在那时跟着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程汉良去慰问他,顺便看到了九死一生的樊立勤。
第二个被抓的是我自己。大约4月10日,我在海淀镇的废品收购站想买点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元件,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强抓到44号楼,用我的衣服蒙头押到楼上,强迫我承认在海淀镇偷卖新北大北京公社成员的物资。我被人用钢管在头上、脚上暴打,打得头破血流、打裂了脚踝骨,放出来后好久都不能走路。
第三个被抓的是女生周某某。大约五六月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抓她关押数日,殴打折磨,放出来后精神恍惚。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打人,不必深究原因,但凡你是井冈山兵团成员,就足够入罪了。
如此算来,我所在的班有十分之一的“老井”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抓捕、拷打过,井冈山兵团成员一共有数百人被抓捕、拷打过。
井冈山兵团怎样生存
北大革委会已经把井冈山兵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保守组织就要打垮,反革命集团成员当然要抓!为此,校“文革”在3月20日就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任命高云鹏为总指挥。3月29日之后,新北大北京公社武力包围井冈山兵团的形势开始形成,更在其下成立了西线武斗指挥部(驻40号楼,以宫香政为西线总指挥)和东线武斗指挥部(驻34号楼,以黄树田为东线总指挥),从两边夹击37号楼的出口通道。井冈山兵团为了防卫弹弓的袭击,在37号南墙豁口架设了宽5米、高4米,用竹木苇席搭成的大棚,从37号楼直达海淀路边。大棚日夜有人把守,以防新北大北京公社的攻击。我作为17纵成员,驻守在28号楼,有时到37号楼前来“放风”。闲来无事,井冈山兵团的人也会在大棚下用长矛比试,互相切磋武艺。有时正在比划着,就看见新北大北京公社成员从40号楼旁的校西南门或34号楼前的豁口拉出装备整齐的队伍,准备向37号楼前的井冈山兵团通道出击。每到此时,井冈山兵团值班的前线指挥就会让不相干的人员离开大棚,也拉出守楼学生来准备防卫。从此,海淀路成为北大武斗的主要战场,自5月2日武斗后,双方长矛队的相互攻击都发生在海淀路上。
北大两派武斗不仅震惊全国上下,而且让外国人也十分关注,西方国家的报刊登出北大武斗的文章和照片,全世界人民都很惊讶:这个中国最高学府到底出了什么事,要用古代的冷兵器拼个你死我活?每逢武斗,海淀镇居民是现场最忠实的观众。尽管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敢于向井冈山兵团的前沿冲锋,用长矛捅进同学的身体,却不敢伤害海淀镇的居民,这使得海淀居民能够救援对阵中被长矛刺伤倒地的学生。
“老井”们要想离开被包围的井冈山兵团驻防的楼群,就得通过海淀路两边的新北大北京公社封锁线。最安全的办法是在37号楼前的大棚下等候,待到32路公共汽车向东开到马路对面南侧的汽车站时,快速越过马路,冲上32路车。由东向西的回程,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马路北侧的32路车站设在新北大北京公社把守的西南门的西边,下了车必须越过西南门才能重新回到37号楼通道。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坐到下一站“北大西校门”下车,然后往回坐一站,到海淀路南侧32路站下车,越过马路就到了37号楼。32路车不是总能等到的,如果你要步行通过两边的新北大北京公社防线,就得冒着被抓走的危险。有时大棚下的人们,眼看着一个“老井”被对方抓进去了,但是无能为力,无法救援。
在校内,数百名教职员工被校“文革”关进“牛棚”,受摧残、折磨,季羡林先生《牛棚杂忆》、郝斌先生《流水何曾洗是非》、郑培蒂老师的《云卷云舒》等专著,都有叙述,此外几十名井冈山兵团成员被长期私刑关押。新北大北京公社不仅在校园抓捕井冈山人,甚至以校“文革”名义,到外地以“抓捕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井冈山总部委员和重要成员,或者以公函形式寄给外地井冈山兵团成员的家人,诬以参加“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罪名,以致许多“老井”的家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校内武斗,校外要制造舆论帮衬。井冈山兵团没有电台,没有报纸,大喇叭声音也传不远,在北京市内就只有靠大字报了。抄大字报是件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老井”发明了油印大字报。油印的大字报有8张蜡纸那么大,就是把大字报内容刻在8张蜡纸上,油印的时候,4个人面对面站着,每人手拿2个油印网,网上沾好已经刻就的蜡纸。从第一张开始,把第一张网放在整张的白报纸上,油墨滚子一滚,这八分之一就印好了;第二张对好了缝,印上去,直至完成8张蜡纸的油印,这样一整张的油印大字报就完工了,就像出版了一份报纸。虽然也挺麻烦,但比人力抄写到底快多了。一套8张蜡纸可以印数百张大字报,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一天功夫就可贴遍全北京城。此项先进技术应用后,立刻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为“刺聂案件”的辩诬过程中,辩白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无言以对。
由于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越来越严密的围困,井冈山兵团在6座楼内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留守在楼内的人也越来越少,武斗中后期大概不过300人。当然,人多也有人多的难处,人多了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垮了,要是垮了,我们就要成为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砧板上任其宰割的鱼肉。我所知道的,在楼内坚持到武斗结束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有侯汉清(勤务组组长)、陈醒迈、谢纪康、靳枫毅、胡纯和等。
在两派大喇叭的宣传战中,新北大北京公社最得意之作,便是广播井冈山兵团成员的“下山声明”。校“文革”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强迫“老井”们退出“保守组织井冈山”。在整个4个月的武斗中,据新北大北京公社说,有1000多“老井”被迫“下山”。我们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万岁纵”(“毛主席万岁文艺宣传纵队”的简称)的乐队里一位西语系的女生,被以“不予分配”相威胁,被迫“下山”,并交出她使用的小提琴。待到武斗结束,所有人的毕业分配,表面上未受派别影响,她很后悔“下山”。
两派武斗队驻守的楼群都是4层楼结构。井冈山兵团楼群的一层门窗都被钉死,二、三、四层不住人的房间门窗也被钉死,有些楼的楼顶是平顶(比如28号楼、30号楼),就用弹簧床、双层床等家具构筑成防御工事,墙边堆有碎砖块并架上弹弓。弹弓开始用的是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胶带,然后改成汽车内胎。因为弹力不足,射程不远,重点防守区域改成乳胶管做的弹弓,弹力大增。两股橡胶内胎带或乳胶管,中间绑上篮球或排球剪成的球皮,再绑在长板凳的两条板凳腿上,板凳架在桌子上,推到窗口,在球皮里装上砖块或石头,拉长皮筋,就可以瞄准目标射击了。一般“老井”用的“炮弹”是四分之一块砖(有些回忆录说是半块砖,我以为不准确,半块砖太重,射不了多远);有时也用鹅卵石,那是新北大北京公社打过来的“战利品”。新北大北京公社用卡车从永定河的河滩拉来鹅卵石作“炮弹”(还强迫“牛鬼蛇神”为他们运石块),威力自然比砖块大得多。我们不能在各楼之间走动,要走得经过双层床构筑的通道,而新北大北京公社成员却可以在井冈山楼上看不到的地方自由行动,这让我们大为不快。有一次,我和同班的另一个同学,从28号楼北侧楼顶面向29号楼西北端,向正在打球的新北大北京公社同学射过几颗砖弹,然后趴在墙边看“战果”。我看见新北大北京公社的同学四散而逃,一个同学瘸着腿跑开,显然是被我们的砖弹打到了(不是直接打到了,是被打在地上的砖块弹射打到了),当时我们还很得意。
井冈山兵团构造的28号楼和30号楼之间的天桥快要完工时,我和很多同学来到4楼,我与同学们一起用水龙带拉住天桥往这边架,对面30号楼的同学拉过去,把天桥稳稳地架设在两座楼之间的4楼上。我还参加过挖地道,把下面挖出的土装在脸盆里,用脸盆吊到地面,泥土堆积在一楼的房间里,以免被新北大北京公社的人看到。
我通过架设的天桥,多次穿行于28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这座天桥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有人很狡猾地贴上了毛主席画像,新北大北京公社不敢用弹弓打天桥上的行人,害怕犯下攻击伟大领袖像的“罪行”。地道建成后,我只进去过一次。6月24日,北京汽车三场的卡车为井冈山兵团送菜,遭到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的冲击,掩护汽车的“老井”被刺伤,汽车三场的司机也被刺成重伤。汽车三场是运输单位,不是北大武斗参与者,汽车三场告到北京市革委会,竟然被污蔑为“送菜派”,从此井冈山兵团的后勤供给就越加困难了。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下了,将近半夜时分,17纵队长郑某某悄悄叫起几个人,说有任务,要穿上棉衣,戴上柳条帽。我们跟着他,下了28号楼的地道,跟着路标走向37号楼,地道里有蜡烛照明。到了37号楼,上了地面,只见楼里灯光暗淡,守楼的人员手持长矛不碰地面,以免出声,人们也低声交谈,一片临战前的紧张状态。我们几个人被告知,今夜有车运粮食来,我们不带武器只管卸粮。过了一会儿,听到海淀路上有马蹄声,原来是一辆马车。车夫驭住马,打算把车赶进大棚。那匹马看到大棚里黑漆漆的一大堆人,绕了一个弯不肯进来。现场指挥临时改变方案,让车夫把车停在大棚门口,我们一帮装卸工冲出去抢运粮袋。不过一分钟的工夫,粮袋就都卸下来堆在大棚里面了。这时东西两线的新北大北京公社喇叭咋咋呼呼地叫喊起来,车夫鞭子一甩,马儿发力狂奔,十几个井冈山兵团成员手持长矛、铁棍跟着奔跑护送,一直把马车送过西线40号楼的西南门。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连大门都没来得及开,抢运就结束了。
我们住在被封锁的井冈山兵团楼群内,食堂是不能去了,只能自己开伙。28号楼南端一层楼有一个锅炉房,一个浴室;南门外堆着一小堆碎煤,是去年秋天运来供浴室锅炉烧热水的,用了一个冬天所剩下的。武斗开始后,有时烧水供应大家洗澡,有时用热水蒸馒头供应大家。因为用得节省,这看着不起眼的一小堆煤竟然一直用到武斗结束。井冈山兵团总部没有能力供应全体人员的伙食,吃饭就得靠各纵队自己开伙。17纵买菜做饭,主要依靠几位女生。买菜要冒着被打被抓的风险,还得节约钱。夏天大米长了米虫,要搁在平常时期就倒掉了,如今供应紧张怎么舍得倒掉,拿水淘洗一下照样吃了。我们做饭主要用电炉,北大的水电大权控制在新北大北京公社手里,碰到新北大北京公社拉闸断电,就只能吃半生饭了。
我是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万岁纵”的乐队队员,1968年6月下旬,总部布置“万岁纵”在地质学院组织七一纪念演出以鼓舞士气。我离开了北大,前往地院。地院东方红公社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最忠实的盟友。他们接纳前来投奔的北大井冈山人,“老井”有数百人住在这里。地院分出一座楼给我们居住,一个食堂让我们自己开伙,“前线”下来的伤员不能长期住在北大附属三院的,地院的校医院都予以接纳。这里是北大井冈山兵团离北大最近、最安全的后勤基地。“万岁纵”在这里排练节目,七一在礼堂表演,井冈山兵团的同学们都很兴奋,增加了“长期抗战”的决心。进入7月,新北大北京公社对井冈山兵团的封锁日益严紧,我们得到通知,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回校去。我在地院一直待到7月23日井冈山兵团在海淀路上接高压线,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数百人冲击,发生攻防武斗之后,才回到井冈山兵团的楼内。
北大校园武斗的终结
7月27日夜,我在28号楼的楼顶值班,下午开始从临近的清华大学传来的枪声使我们非常不安。7月23日的武斗,井冈山兵团成功接通一万一千伏高压电线到井冈山兵团楼群内,打破了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的供电封锁。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冲击接电现场失败并致多人受伤,他们肯定不能忍受这样的失败,肯定会制造新的武器装备,肯定会策划新的进攻。现在,清华团派用步枪射杀四一四派(又称“四一四串联队”)人员,新北大北京公社会不会也步其后尘、对我们开枪呢?井冈山兵团的前途在哪里?井冈山兵团要是被打垮了,我们都得完蛋!
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中央派遣的“工宣队”在解放军的领导下进入清华校园制止武斗,我听到的枪声是清华团派在负隅顽抗,而四一四派已经在“工宣队”的劝说下缴械投降了。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消息传出,团派的抵抗立即土崩瓦解。原来,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直至这个“御前会议”,聂元梓还在毛泽东面前诬陷北大井冈山兵团:“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侯汉清)是研究生,父亲1963年搞投机倒把……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校“文革”)没有搞他(指樊立勤),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从7月28日开始,北京市革委会派出的制止武斗的宣传队每天数万人进出北大,新北大北京公社对井冈山兵团的封锁立刻被打破。我们走出楼群,走在4个月不敢走过的校园里,不用担心再被抓捕、再被毒打。武斗的两派成员也罢,逍遥派也罢,开始大批返回校园,到了这个时候,两派都明白,武斗结束了,学生主导运动的局面也结束了。8月19日,“工宣队”开进北大,自然就是“工宣队”当家了。趁着还没有搬回各系宿舍楼的间隙,我悄悄溜回在南京的家里,直到10月初才应“工宣队”的通知回到学校。
我们在“文革”中有底线吗?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起,一直是一个文质彬彬、书香浓郁的高等学府。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一些教师和学生,也没有发展到武斗,甚至在校园内外抓人、打人、杀人,直至肆无忌惮的地步。
如今,北大校园的武斗已经远离我们达48年了,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文革”结束后追究责任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至少有6名成员被判刑,其中包括校“文革”主任聂元梓、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高云鹏等。
聂元梓是个“革命老干部”,12级高干,参加过延安整风。1960年代靠她的哥哥聂真与北大校长陆平的私谊调入北大。1963年到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是学校党委委员。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时,中央是支持陆平的,聂因为恶意攻击陆平犯了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不得不作检讨,聂元梓怀恨在心。“文革”爆发后,聂元梓挑头签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家可以看看她在大字报最后一段写的是什么:“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显而易见,陆平要倒大霉了,聂元梓这样报了北大“社教运动”挨批之仇了!陆平就这样被聂元梓定性为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了“反革命黑帮”的头子,聂元梓也一夜之间变成全国最著名的革命造反派。其后,陆平被关押、被批斗、被审讯、被吊打。1966年8月15日,北大革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陆平,10万人齐声高喊“打倒陆平”,在雨里从下午斗到晚上。1975年,陆平被平反,调到七机部当副部长。2001年北大校友李海文采访陆平,陆平准备了9个问题,谈了一个问题就发病住院,从此不能再谈。
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被捕入狱,1983年3月16日被判处17年徒刑,后来保外就医。她的判决书指控的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多年来聂元梓一直不承认她被指控的罪行,并且企图翻案。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常常这样搪塞:“我不知道”,“我管不了”,“我不是新北大北京公社社员”。这样的话不仅不能免除她的罪行,只能让人不齿。
聂元梓是北大校“文革”主任,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校“文革”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聂元梓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所犯错误和罪行负有领导责任。正如她的朋友、清华井冈山兵团团派的头头蒯大富要对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死亡的18条生命负责一样。
孙蓬一是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忠实追随聂元梓,聂元梓所犯的罪行都有他的一份,他被判10年徒刑。1990年代我在美国洛杉矶的三联书店里,在一本有关清华和北大“文革”回忆录里读到孙的消息。他在刑满释放后深自忏悔,向他所在的哲学系的两个井冈山派教师下跪道歉。他做得对,我个人愿意原谅他。
北大武斗期间死亡的3个青年学生,都不是死在两派武斗的现场。其中,温家驹是在生物楼里被酷刑致死,事发后我们得知新北大北京公社的成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具,让守楼的井冈山人心中恐惧颤抖。殷文杰则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员用长矛刺死在44号楼新北大北京公社总部门前,身上被扎了39个血窟窿。还有一个是刘玮,他被抓到40号楼,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员轮番殴打致死。新北大北京公社成员抓人、打人,以致打死人,已经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做人的底线。我听说,每次新北大北京公社打死人,都在内部造成愤怒和矛盾,有些成员就此脱离武斗,做逍遥派去了。
井冈山兵团的成员也犯过错误。我们盲目听信“最高指示”,没有认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为北大校长陆平真的是“反革命黑帮”,我们参加了批斗陆平及北大干部和教师的各次大会,有些干部教师被逼自杀,家破人亡。对于这些事件,我们应该忏悔。但是,我们还是有底线的,因此在1966年以后,当红卫兵开始在社会上以“破四旧”为名大肆迫害平民百姓、知识分子及其子弟时,我所在的班的一些同学对抗在海淀镇横行不法的“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简称“海纠”),在海淀镇邮局与一帮中学生红卫兵论战大半夜,救出一个红卫兵企图抓走的邮局职工,因而被本系一些同学贴了大字报,攻击我们是“反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
那么,井冈山兵团的人在武斗中有没有抓过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的人呢?除去3月29日武斗过程中井冈山兵团抓的人,在以后4个月的武斗中,据我所知,井冈山兵团总共只抓过2个人。
第一个是被抓的是戴新民。戴新民在“文革”前已是北大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大“社教运动”时著名的左派。“文革”初期,戴新民被选为校“文革”委员,中后期在思想上支持井冈山兵团。4月初,有消息传出戴新民是“叛徒”。她要是叛徒,再落到新北大北京公社手里,井冈山兵团就被动了。17纵决定把她控制起来,免得校“文革”把她抓去严刑逼供,弄出对井冈山兵团不利的事来。17纵纵队长带了几个人去她家,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到了老戴(戴新民很平易近人,全系上下都管她叫老戴)家,要她跟我们走。老戴是个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想必也知道这一去没有好事。到了井冈山兵团控制的楼群,在28号楼17纵驻地给老戴安排一个单间,平时也不怎么管她,每天三顿伙食供应,只要看见她人在就行,谁也不跟她说话。日子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老戴没人跟她说话,只能看书,更加无聊烦闷。有一天老戴企图偷偷逃走,被“老井”们发现。问她为什么要跑,她说北大武斗打成这样,她要去市革委会反映。以后照旧把她控制在楼内,直到武斗结束。
第二个被抓的是一个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员。时值7月的一天,我正在地质学院住着待命,忽然有人从城里打电话过来,说“老井”在新街口被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打了,要我们赶紧过去支援。我们一行20多人赤手空拳,分批乘公共汽车前往新街口。下车不远就看到一个“老井”在马路边收拾东西,见到本派大队人马到了,赶快迎上来诉说刚刚发生的事。原来,井冈山兵团的几个人正在街上贴大字报,一辆新北大北京公社的卡车载着带长矛的武斗队赶到,抓住“老井”就往车上扔,只有他一个人逃脱。周围的市民看不下去了,纷纷前来保护“老井”,指责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抓人的恶行。新北大武斗队赶快开车疾驰而去,一个武斗队员不慎落单,被市民们抓住,已经送到新街口派出所去了。我们一行人立刻赶到新街口派出所跟警察要人,警察哪里肯给。可是我们若不能带人回去,被抓去的人怎么办?好言不听,我们也就不客气了,上前架住那人就往外走。几个警察没敢阻拦。回到地质学院,问话的结果,这人是个工人,家里有老有小。果然不过半天,校“文革”就打电话来要求谈判。新北大北京公社那边丢了一个人就闹翻了天,那人的老婆哭哭啼啼地找他们的头头要人。井风山派的头头说放人可以,你们也得把这次抓的几个“老井”都放了。那边没有讨价还价,立刻同意。双方确定交换地点在五道口,第二天双方人员就交换了。这是井冈山兵团在3月29日武斗后唯一的一次抓捕新北大北京公社人员,没有殴打,没有侮辱。严格地说,这次井冈山兵团只是把这个专程进城抓人的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斗队员带回地质学院,换回了我们被抓去的人员。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以六十三军(四五八七部队)为首的“工宣队”接管北大大权后,搞的是支持一派(新北大北京公社)、打击一派(井冈山兵团),搞出了900多个“反革命”专案,逼死了30多名师生员工。“工宣队”在北大搞得天怒人怨,连毛泽东都坐不住了,1969年3月派了八三四一部队来收拾局面。1969年4月,北大“工宣队”主任、六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不得不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宣读报告,以大量篇幅检讨“工宣队”所犯的错误,并且对校“文革”的错误作了定性:“校文革在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
清华大学校友陆小宝在他的《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中说:“‘文革运动搞得天下大乱,害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在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中失去了生命。每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锥心的伤痛。为了死去的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老暮之年,把我们当年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属于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诚哉斯言!无论是新北大北京公社还是井冈山兵团,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北大人,都应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