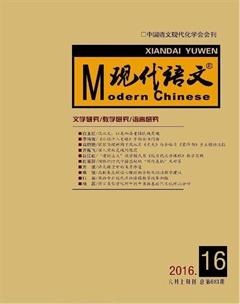深入黑奴灵魂的惩罚
齐雁飞
摘 要:惩罚行动的最终目的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运用于灵魂的惩罚。《为奴十二年》中的奴隶主所代表的规训权力,通过对黑奴精神上施加的一系列精神惩罚技巧的运用,达到使黑奴自觉规训和屈从的目的。
关键词:为奴十二年 福柯 规训权力 精神惩罚
第8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得主《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s)是根据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自己的奴隶经历所著的,185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以奴隶制度为题材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生为自由人的黑人,原本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但当他于1841年被两个白人诱骗卖作奴隶后,从此丧失了一切,体验了饱经屈辱、备受折磨而又心酸的十二年的奴隶生活。该书通过主人翁的视角向人们展现了黑奴们悲惨的生存状况,及奴隶主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严酷的惩罚手段。
著名哲学家福柯在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惩罚行动的最终目的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运用于灵魂。[1]因为,最严厉的惩罚早已不再施加于肉体,取而代之的是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1]《为奴十二年》中以残酷著称的奴隶制,奴隶主正是通过除了肉体暴力外,对黑奴的精神上施加一系列惩罚技巧,从而达到使黑奴自觉规训和屈从的目的的。
一、全副武装的监工
福柯明确指出,监视是惩戒技巧得以起作用的主要途径之一[1]。连续不断地监视可以了解个体的各种动态,并察觉和裁决个体的一切过错,也能使个体进行自我监督。为了更好地对黑奴进行监管,奴隶主时时刻刻都安排了监工或监督者对黑奴进行监视。不论是在奴隶羁押地,还是在奴隶主的庄园,到处都有奴隶主的监工,毫无例外他们都配有手枪、猎刀、鞭子,还伴有狗,骑着马。他们以这副装备跟在奴隶后面,严厉地监督奴隶劳作和活动。奴隶们的任何举动都在这种监控之下,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最残暴的肉体惩罚。在这种持续的、长久的监视的目光压力之下,每个黑奴都慢慢自觉地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实现自我监督。
二、深入人心的痛苦观念
对于旨在产生预期效果的惩罚来说,它能造成的伤害只要能超越从中获得的好处,就可以了。[1]因此,制造肉体的痛苦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痛苦的想象和记忆才能打消或收敛某些违规意图。[1]奴隶主对任何一个奴隶的严厉惩罚,不仅是惩罚受罚者的肉体,让他苦不堪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鞭挞他的内心。对于受罚者,肉体上的伤痛,会随着时间、伤口的愈合慢慢消退,但惩罚他们的种种刑具、身体上长长的永远也无法消除的疤痕、残缺的肢体、撕心裂肺的哀号声,及这种痛苦的想象和记忆比实际的痛感更强烈,会时时触动他们,让他铭记于心至死不忘,让他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正是奴隶们对惩罚的恐惧,遏制了他们头脑中任何一点不好的念头,从而达到自我监督与约束,不敢再有任何丁点的犯错的想法。
三、公开的处决
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用权力向人发泄怒火的场面换取恐怖感。[1]公开处决是侧面效应的儆戒,消灭他人重犯的最重要因素。对潜在的违规者起到威慑、警戒、引导和教育的作用。波伏地区的奴隶主们正是对违规的奴隶们使用公开的致命的拷打、非人的虐待、惨无人道的绞杀等处决,让所有奴隶们有种畏惧感,从而让他们明白顺从的必要性。当奴隶们被施以极刑时,这地狱般痛苦的惩罚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让其他见证者对奴隶主,更加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种心理上的恐惧,使奴隶们即使有再多的怨恨,即使多次拿起了致命的武器,比如镰刀、猎枪等,也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不敢对这不人道、非正义的、残酷的、野蛮的奴隶制度有半句不敬之语,更不敢向他们“魔鬼”般的主人发起任何攻击。这就是公开处决的效用,它不仅已成功地驯服了奴隶们,更使他们甚至麻木的开始割弃对别的黑奴的同情和怜悯[2]。当所罗门因反抗他的主人迪比兹,而被迪比兹高高吊起,生命危在旦夕之际,除了瑞秋冒险送来一杯水外,其他奴隶依然如往常般平静地生活,对这一切,对于这个曾给黑奴诸多帮助的同胞,他们熟视无睹。
四、话语的缺失
奴隶们是没有话语权的,哪怕他们说的是实话,是真实的吐露。他们必须遵从一些“禁止”即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对象的禁忌),不能在喜欢的时间、地点谈论什么(境况的限止),合适的人也不能谈论恰当的事(讲话主体的优先权或专有权)。[3]如果违背任何“禁止”,奴隶们就会招来最残酷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也就是说,奴隶们是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的,只能是奴隶主要求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说,而且还必须是问什么,答什么。这就使得奴隶们因为害怕违反“禁止”都少言寡语,不敢有任何辩驳,只能在无止境的“沉默”中度过他们悲惨的一生。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对于他们这样无助的黑奴,无论他们说什么,都被认为是不重要、不真实、无效的,也都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行为带来的更多的只能是主人们的侮辱、谩骂,甚至苦不堪言的鞭打与虐待。
五、无所不在的排斥
福柯认为,定罪本身就给犯罪者打上了明确的否定记号。[1]黑奴正如福柯口中的犯罪者一般,生来就被白人歧视,被白人打上了否定记号。他们生来被视为狗、牲口,不管他们多努力,不管他们多真诚,不管他们多有用,在白人的潜意识中早已对他们有了排斥的习惯,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翻新花样。如所罗门·诺瑟普可是极具才能及价值的“黑奴”,不仅能为主人想办法排忧解难,还能为主人挣取大笔的财富,加之,他还会拉小提琴,会木工、漂流筏运,还会干几乎所有的农活等,他近乎是个全能的“黑奴”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对主人很忠心。就算这样,主人们也还认为他不过是黑鬼罢了,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甚至结束他的生命。
此外,奴隶前往任何地方都必须携带主人出示的路条,如果没有路条,任何白人,哪怕是衣衫寒酸、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流浪汉的白人,都有权逮捕他,鞭打他,把他投入监狱,直到他的主人能来“证实该奴隶是他的财产,交了费用,将其领走”。奴隶们就像家畜一样,任何守法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公民,都有义务把逃跑或走失的他们抓获,关押在待领场,等待他们的主人。[4]有时,抓逃奴还成为一些游手好闲的“卑劣的白人”谋生的手段。因为,抓逃奴是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如果广告通知后无人认领,逃奴可以被高价卖出,如果有人认领,抓获者会获得报酬[4]。 也就是说,任何白人都有权随意处理任何流浪的“黑狗”。
六、自我定位
约翰·高而斯华馁曾说过:“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为了对黑奴进行控制。奴隶主通过采用各种方式剥夺黑奴的尊严,将黑奴定义为不过是会说话,具备某些高级能力的牲口[4],并竭力把这样的观念植入黑奴内心,达到黑奴自我如此定位的目的。
在波伏地区,黑奴是没有尊严可言的。首先,所有的奴隶甚至没有选择名字的权力,他们随着主人的不同,被冠以不同的姓或者名字。例如主人翁所罗门·诺瑟普原本是随父亲跟从了主人诺瑟普家族的姓。在不断买卖的过程中,他不停地更换着名字和姓,先被船长取名为斯图尔特,然后被伯奇安了普莱特的名字,随后三度易主,从普莱特·福特改为普莱特·迪比兹。其次,“不听话”的奴隶总是带着手铐和脚镣;对于说话太多,或总说些奴隶主禁止说的话的奴隶,如牲口般被戴上铁制的“口罩”;所有的奴隶,没有男女之分,不论是洗澡,还是睡觉都在一起,都是在监视之下;被买卖的时候奴隶必须光着身子,任由奴隶主验货、挑选。此外,奴隶们要接受奴隶主最粗鲁的对待,要忍受他们的粗言秽语、蛮横的说话方式和厌恶的表情。
长期尊严的丧失,就会走向妥协。慢慢地为了生存,奴隶们开始像奴隶主预期的那样,成为主人身边的一条狗,努力地讨好主人,忠贞于主人。然而,更可悲的是,慢慢的所有的黑奴也开始因为自己种族的原因和世代相传的奴隶身份,愚昧地自认为自己身份的确低微,并坦然接受如狗般的虐待。
结语
对于黑奴而言,猎狗和鳄鱼等动物,可能会在瞬间结束他们的生命,而人类,除了对他们实施肉体暴行外,还折磨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生不如死,相对前者,所有的奴隶很清楚自己最害怕的是上帝赋予了他们同样生命的人类。奴隶主所代表的规训权力,正是通过一系列除肉体外的精神上的惩罚:监视黑奴的行为,处决黑奴的身体,约束奴隶语言的使用,左右黑奴的思想等,在黑奴头脑中建构起了一种关于违规与惩罚的锁链,从而让黑奴从内心深处产生畏惧,并自我定位,用自己思想的锁链约束、指导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奴隶主对黑奴规训的目的。
注释:
[1]刘北成,杨远缨译,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104,111,222,104,63,286页。
[2]王颖:《为奴十二年》:奴隶制度下的人性扭曲论,电影文学,2014年,第23期,第95-96页。
[3]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03页。
[4]胡戈译,所罗门·诺瑟普著:《为奴十二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88,101,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