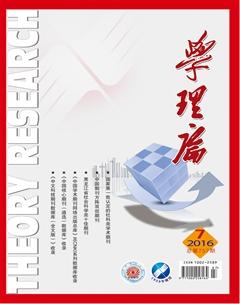孙中山论香港问题的三个向度
陈鸿惠
摘 要: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策源地以及革命运动的指挥部。孙中山把振兴中华、收复失地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并在其革命学说中针对香港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孙中山有关香港的重要论述可以归纳为三个向度,即爱国主义的价值观、主权在中的政治论、中西兼容的治理观。这些闪耀着孙中山思想光辉的重要观点,对于当前持续推进“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香港问题;向度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7-0068-03
香港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回避的重要政治问题,也是孙中山始终关注和论及的重要思想内容。本文试从价值观、政治论、治理观三个向度,探析孙中山有关爱国主义、主权在中、中西兼容的香港问题观。
一、爱国主义的价值观
爱国主义是孙中山身体力行、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孙中山认为,维护国家统一是爱国主义的核心要素和显著标志;香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来有自、历久弥坚;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团结、奋斗、救中国的重要目标。
(一)维护国家统一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流趋势,支持国家统一既是对历史演变大势的认识,也是对爱国主义价值的弘扬。
首先,中国历史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循环。分裂只是中国历史的现象和支流,只是暂时的乱象;统一才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和主流,才是长久的趋势。“由此可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1]746统一与分裂不仅事关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更是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关键所在。“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2]51
其次,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意识。这正是中华民族虽然在历史上屡遭战乱但是仍旧浑然一体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削弱这种意识。”[3]258-259
最后,爱国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坚持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划分爱国者与否的最重要标准,也是辨识敌我关系的分水岭。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一切背叛和分裂祖国、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鼓吹分裂者就是野心家。“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1]747
(二)香港中国人一向富有爱国主义传统
孙中山对香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传统有着深切的认识和由衷的称赞。
首先,香港的中国工人抗法反英斗争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人的觉悟性和团结力。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的中国工人就以拒绝修理法国船舰的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内地的抗法斗争,并由此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当时正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对于英法帝国主义的沆瀣一气极为愤怒,更从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运动看到了“中国人已经有相当的觉悟”和“种族的团结力”[4]158-163。
其次,香港中国人长年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斗争。孙中山充分利用香港既毗邻广东却又在清政府治外的独特地缘优势,使香港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补给站。不仅兴中会总部设在香港,而且广西镇南关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都在香港设立指挥部。香港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不论富家巨室还是贩夫走卒都给予革命运动以人力及物力支持。这些爱国壮举也引发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戒备和打压,此后香港中国人通过积极抗争才迫使英国殖民当局有所收敛。“从前因各商家协助革命,为政府逮捕,今可无虞,当可与予一致行动。”[2]117
(三)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统一中国、收复疆土是孙中山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包括香港中国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5]373
“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1]746在孙中山的内心深处,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港澳台将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重要历史坐标。“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6]413-414
在孙中山建国大业的日程表上,首要是统一中国内地,结束南北方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其次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关税特权和已割让领土;最终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的完全独立与统一。“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2]52
二、主权在中的政治论
在孙中山看来,英国侵占中国香港是于法无据、于理无由的野蛮行为;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并未改变中国拥有香港主权的法理和历史事实;只有打破封建军阀以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才能彻底解决香港问题。
(一)香港系为英国无理侵占
英国在侵占香港后,刻意强调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均属于英国女王。孙中山却尖锐指出,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结果,英国侵占香港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野蛮行为。
首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造成中国领土分崩、百姓遭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对领土扩张和殖民利益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14另一方面是封建主义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出卖人民利益以讨取列强欢心。“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1]14
其次,英国侵占香港是出于强权而非公理。英国在西方列强中最早以武力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非法攫取香港并实施殖民统治。孙中山明确指出中英“江宁条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蹙,国本动摇,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如英国之割香港……受兵力胁迫而偿外人之款者,如江宁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得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场……”[7]43孙中山强烈谴责英国对中国输入鸦片、侵蚀领土的无理霸道行为。“所以夺我香港……据何公理?逼我吸销鸦片,划我国土地为彼势力范围,据何公理?”[8]43
(二)香港主权始终属于中国
虽然香港为英国所侵占并经受殖民统治,但是主权无可置疑属于中国,中国迟早要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并于1895年将总部设在香港。《香港兴中会章程》明确将香港视为中国领土,总部设在香港即是总部设在中国,“会名宜正也。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9]22
在对外交涉中,孙中山一再强调中国终归要收回香港。在与英国政府代表的谈话中,孙中山坦率告知:“现在你们还要来取西藏。我们中国此刻没有收回领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国占去了的领土罢。”[1]664在此后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孙中山多次申明数年后中国人在英国的权限必然与英国人在中国的权限相等。在与日本重要人士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确指出:“惟香港、澳门则有意收回。”[7]318
(三)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打破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联盟
孙中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上经历了巨大的思想变化。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把斗争矛头对准封建主义,虽然对帝国主义有所警惕,但是仍幻想用革命道义以及承认不平等条约来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6]10
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幻想以及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封建军阀的妥协。“曾几何时,己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1]587在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过程中,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若不打破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盟,就无法断绝导致中国战火连绵的根源,也无法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5]338香港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消灭封建军阀并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1]973
三、中西兼容的治理观
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住香港问题的两重性质,即中国主权因殖民侵略而遭到破坏,以及香港的社会发展程度领先于中国内地。孙中山从香港与内地在市政建设上的较大差距,深入比较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中国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从而得出既要学习西方制度经验又要发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结论。
(一)香港问题的两重性质
在孙中山眼里,香港是一种矛盾交织、角色交叉、文化交汇的多重映象。香港既是中国内地走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车之鉴,又是中国内地地方治理的他山之石;既有欧美制度的暴风骤雨,又有中国文化的无声润物。
在领土和主权上,香港是中国内地全面沦为西方列强势力范围的前车之鉴。香港的割让只是中国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泥淖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侵略者的野心持续在神州大地上横行无忌。“香港完全割归英国,由英国人管理,是英国的全殖民地……不止是英国人在中国是这样横行,就是其他各外国人都是一样。”[1]980香港问题的根本性质是中国的被侵略以及领土的被分割,这是英国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的。“造成香港的原因,并不是几十万香港人欢迎英国人而成的,是英国人用武力割据得来的。因为从前中国和英国打仗,中国打败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归到英国,久而久之,才造成现在的香港。”[1]618
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香港的近代化程度高于苦难深重的中国内地。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巩固在港统治,逐渐吸收香港中国人的个别上层人物参与立法及行政事务。相对于中国内地从辛亥革命前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奴役”转变为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层奴役”,香港中国人的政治处境至少在表面上有所改善,其政治权利也算是聊胜于无。“就字面讲,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当然比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要高……香港割归了英国……在那个立法局里头,还有几个中国人……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1]980这种对比不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歌功颂德或者涂脂抹粉,而是又一次从反面强调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1]995,不论中国内地还是香港才可能真正享有地方自治的政治权利。
(二)从市政考察到政治研究
中国香港和美国檀香山一样,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少年时期,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生活和学习,接触并思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萌发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奋斗目标。从美国檀香山到中国香港,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从改良兴中转为革命救国,从萌发趋于成熟。
青年时期,孙中山到香港求学,在对比其家乡香山与香港的巨大发展差距之后,“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2]115,激发了推翻专制、实行共和的革命思想。“即我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2]115孙中山对香港与内地发展落差的思考结果,是香港所仿效的英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远胜于内地所奉行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就要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一组织良好之政府,中国则并无(良)政府,数百年来只有败坏一切之恶政府。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也。”[2]115
(三)政治制度需要文化支撑
孙中山对香港与内地近代化差距的思考,并未停留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原因分析,而是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底蕴。孙中山认为,西方民主共和的制度优势,加上中国人易于管理的文化特性,可以造成中西合璧、安居乐业的中国。“试观海峡殖民地与香港,前者有华人一百万有奇,后者有华人六十万,我等未往该两地之前情形如何不必论,今则皆安居乐业而为良好公民,可见中国人民乃容易管理者也。”[2]117
在思考过程中,孙中山跳出了以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窠臼,提倡中西一体、各有优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既然中国的文化和伦理优越于西方,就应该传承创新;既然西方的制度和技术领先于中国,就应该吸收消化。“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688-689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经过适当的改造后不仅可以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兼容并蓄,而且可以提供更加持久有效的精神支撑。“彼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9]560
孙中山反对从闭关自守的一个极端走向崇洋媚外的另一个极端。“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在孙中山看来,地方自治是中华民国的建国基础,唯有在地方实行自治才能使全国人民得以共治、共享。孙中山更是反对不顾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盲目引进并照搬照抄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是反对将美国联邦制套在中国大地上,导致中国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二是反对封建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而行地方割据之实,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并分裂大一统的中国。
孙中山有关香港问题的精辟论述,启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当前“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如何处理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孙中山在香港问题上始终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更是我们持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和先声。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林柏克.孙逸仙传记[M].徐植仁,译.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6.
[5]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