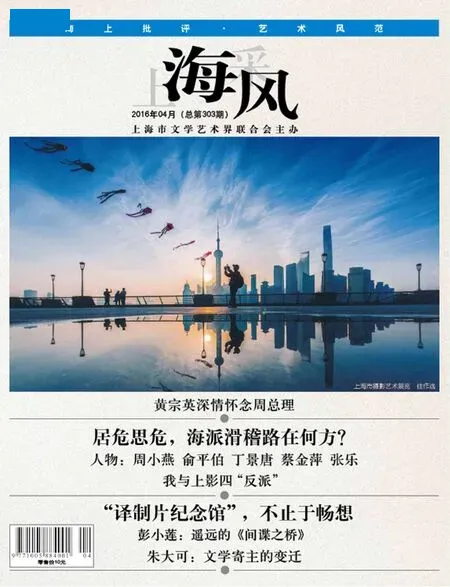被遗忘的大师
文/王 海 摄/管一明
被遗忘的大师
文/王海 摄/管一明

王海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评论主笔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一些人被遗忘了,终其一生,籍籍无名;还有一些人被时间遗忘了,她们安享岁月,以不可思议的长寿引发世人的惊诧——这一部分人,最后从名词活成了叹词。
这样的“叹词”有两枚,均出自周家:北周有光,南周小燕。2016年3月4日凌晨,周小燕在上海去世,享年99岁。在度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精彩之后,时间终于追上了她。

我和周小燕先生完全没有任何交往,我所见,与普通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如此地矍铄,强势而不强悍,依稀能瞥见岁月背后的沉静与——怎么说呢,即便在年轻时代,周先生并不能说如何美丽,只是那种极具民国调调的气场,沉淀之后化出的醇厚,比“美丽”更令人折服。我和大多数远望的观众一样,其实并不知晓她具体做过什么,甚至没有听过她“夜莺般的歌喉”,但这不妨碍我们和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恰到好处的叹词。是的,晚年的周小燕已然成为某种符号,她是自己的logo,也是岁月打盹的标志,更是这个城市气场的某个类似众筹的组成。
对许多仅仅依靠气质就可以为自己代言的人来说,最便捷的效应在于可以省却很多繁缛的认知细节,迅速征服人们的“文艺味蕾”。本文照片地的拍摄者管一明先生在拍摄完成25年后,几乎已经完全想不起当天采访的细节,但依然对周先生当天的种种风度啧啧有赞。此即一例。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和周先生有关的文章。在那篇依然属于“远望”的文字里,我臆想了二战期间滞留巴黎学习音乐的周先生,在一个著名的奢侈品箱包的广告中,将德纳芙从雾气氤氲的巴黎火车站的画面中替换下,依旧不觉违和。现在回念,德纳芙自然非常德纳芙,周小燕亦非常周小燕,她们各自属于两个伟大的城市,替换终究是戏仿,而中国夜莺并不在那巴黎的“最后一班地铁”上。
她的气场是魔都的。上海从来就不是地域概念,而属于某种文化的认同。她生于武汉,青年求学域外,之后一个多甲子与上海共呼吸。很难想象,在上海之外的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周小燕能成为现在的周小燕。上海与周小燕,互相成就,互为镜像。我未听过周小燕说话,不知道她是会讲比较纯正的上海话还是夹杂了家乡口音的一种“嫁接式”的上海话,在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过程里,有无数她这样的“文化认同感”上的上海人,操着混杂式的上海闲话度过了一生。也许直到生命的终点,她们的口音依旧是洋泾浜的,但从未有人对她们的文化归属有过丝毫的质疑。这是一个人的成功,也是一种文化的成功。

本文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2 月26日,5年后,照片上与她恩爱旖旎的张骏祥去世。当时她在美国的一双儿女回国奔丧。临走时,儿子担心母亲孤单,于是动员母亲同去美国。周小燕拒绝,说:“我不去,我的学生都在这里,我去那里干什么?”多年以后,她的儿子对记者回忆无疑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最好注脚:1970年代,周小燕的儿子还在开公交车,线路正好经过上海音乐学院。一天,他开车经过门口,发现母亲推着自行车和学生高曼华在路边说着什么。一圈开回来,她们还在说。又一圈回来,还在原地。
在复兴中路汾阳路梧桐掩映之下的上街沿,一名气韵十足的女教师手扶自行车把,投入地和学生悉悉索索——此情此景,才是最有魔都气质的,最周小燕的“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