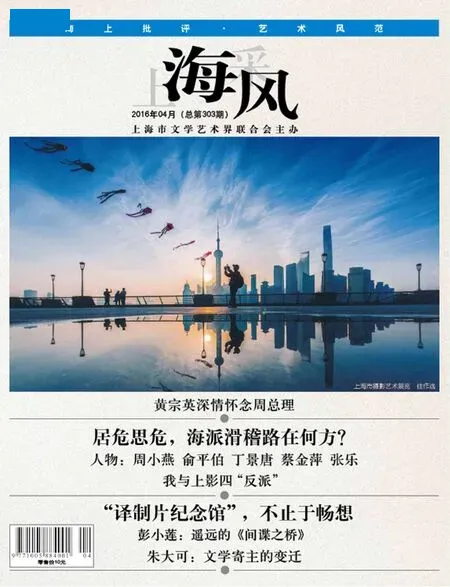文学:寄主的变迁
文/朱大可
文学:寄主的变迁
文/朱大可

朱大可
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百万字、5卷本的《朱大可守望书系》《华夏上古神系》等
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
返观中国文学的现场,我们发现,汉语文学的衰退,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的前线作家,大多进入了衰退周期,而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成熟,断裂变得不可避免。第二,重商主义对文学的影响,市场占有率成为衡量作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种普遍的金钱焦虑,严重腐蚀了文学的灵魂和原创力,导致整个文坛垃圾丛生。第三,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等媒体的兴起,压缩了传统文学的生长空间,迫使它走向死亡。
这是我关于文学衰败的基本看法。但我最近才意识到,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文学的衰败只有一个主因,那就是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然而,尽管中国文坛充满了垃圾,但文学本身并不是垃圾,恰恰相反,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幽灵,飘荡于人类的精神空间,寻找着安身立命的躯壳(寄主和媒体)。在可以追溯的历史框架里,文学幽灵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自己的寄主。第一次,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所谓“口头文学”(听觉的文学);而在第二次,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并催生了所谓“书面文学”(文字的文学)的问世。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在刻写术、纺织术、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支持下,经历两千年左右的打磨,书面文学早已光华四射,支撑着人类的题写梦想。
文学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寄主,那就是歌曲和戏剧,它们跟传统文学并存,俨然是它的兄弟,照亮了古代乡村社会的质朴生活。但就叙事和抒情的线性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口头和书面文学的变种而已。文学的寄生形态,从来就是复杂多样的。它们制造了艺术多样性的幻觉。
然而,基于个人作坊式的书面文学正在迅速老去。文学已经动身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全新的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新寄主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但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完全沉浸在对书本、文字和个人书写的习惯性迷恋之中。我们对文学的剧烈变革置若罔闻。
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也就是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爱森斯坦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指出电影与文学的本质关联,他的杂耍蒙太奇语法,企图重现自然语法的叙事功能。但很少有人相信他的实验及其信念。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修炼,在那些包括影视在内的新媒体的躯壳中,新媒体文学已经卓成大树。
《魔戒》无疑是新媒体文学的杰作,它超越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惊心动魄的影像史诗,它不仅再现了《荷马史诗》和《圣经》时代的集体创作特征,而且在宏大叙事时空里,构筑了复杂的精神符号体系,追问人类的核心价值,不仅如此,它比《荷马史诗》具有更强烈的体验性力量。越过超宽银幕和多声道音响系统,我们惊讶地看到,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幽灵,在这种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维系着旧文学的灵巧的叙事特征,却拥有更优良的视听品质。它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可以密切互动的数码艺术,结果它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抨击严酷的社会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力量。新媒体文学甚至借用商业资源,把那个最强大的敌人,转变成养育自身的摇篮。文学正在像蝴蝶一样蜕变,它丢弃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方式重返文化现场。
诗歌的命运也是如此。书面诗歌也许会消亡,但歌曲却正在各种时尚风格的名义下大肆流行,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它们是诗歌的古老变种。更重要的是,即便各种诗歌形态都已消亡,但支撑诗歌的灵魂——诗意,却是长存不朽的。宫崎骏的卡通片系列,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在那些梦幻图像里,诗意在蓬勃生长,完全超越了传统诗歌的狭隘框架。
让我们回过来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景。这类奖项的道路正在越走越窄。20世纪文学老人正在相继谢世,新一代作家软弱无力,无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文学授奖对象变得日益稀少。这是书面文学的原创性危机,也是各种文学奖的权力危机。在我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并把那些生气勃勃的新媒体文学,纳入文学奖项的搜索范围,并在保留书面文学“遗产”的前提下,加入文学的新媒体类型,如“影像文学”“游戏文学”和“手机文学”等等。文学,应当是上述各种样式的总和。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更加瑰丽的“物种”,而我们却在继续悲悼它的“旧茧”,为它的“死亡”而感伤地哭泣。文学理论家应当修正所有的美学偏见,为进入新媒体的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