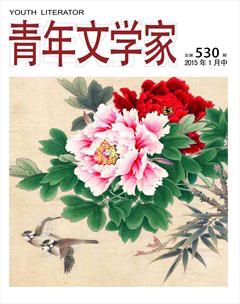杜薇恩小姐的“孤独”与“不幸”
陈琼琼+刘仪华
摘 要:小说《杜薇恩小姐》通过小男孩亚瑟的回忆,引出了杜薇恩小姐的悲剧人生。女主人翁虽然因为男权制社会的欺压成为了牺牲品,但她对自我意识的坚持、对未来的期望带给读者信心。小说流露出作者德拉梅尔对当时社会中女性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
关键词:《杜薇恩小姐》;孤独;不幸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2-0-02
瓦尔特·德拉梅尔是蜚声二十世纪英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善于使用艺术手法营造作品的氛围,评论家哈里·布拉迈尔斯称赞其为“在二十世纪善于塑造氛围的诗人中,瓦尔特·德拉梅尔堪称他们中间的大师”[1]。《杜薇恩小姐》以小男孩亚瑟的回忆开篇,将女主人公杜薇恩小姐的“孤独”与“不幸”在艺术的氛围中完整再现。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杜薇恩小姐搬家之后与邻居家的小男孩亚瑟成了忘年交,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杜薇恩不同于传统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展现在亚瑟面前。但是,杜薇恩小姐的堂妹与亚瑟的奶奶极力阻碍他们的交往,出于对亚瑟的保护,加上其本人身体健康的恶化,杜薇恩小姐选择了一个人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小说情节虽然简单,但作品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却十分重要:杜薇恩小姐的悲剧命运虽然早就注定,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一直坚守着她的“自我意识”,直到生命的尽头。
一、杜薇恩小姐的“孤独”
杜薇恩小姐在别人看来无疑是孤独的。提到“孤独”,人们最先联想到的往往就是“寂寞”、“空虚”,脑袋里甚至还能浮现出某种凄凉景象。“孤独”相较于“空虚”、“寂寞”更属一种状态,一种圆融的状态。孤独者往往都是思想者,孤独者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让自己平静,并能自得其乐。所以,孤独者并非真正的孤独,一个人能与自己的思想为伴,应该胜过庸俗的迎声附和。
杜薇恩小姐的“孤独”感伴随其出场前,作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渲染。小说从亚瑟的回忆切入,首先描绘了亚瑟孩童时的生长环境。“住在奶奶家的时候,我没有玩伴。老旧的房子紧挨着云铎河,与河流的朝气蓬勃一比,样式丑极了。青葱的岸边柳树与杨树成荫,我最常听到的不是人声而是这涓涓流水的声音,奶奶不喜欢我的陪伴。她怎么可能喜欢呢?”[2] 住所偏僻,房屋老旧,又不受唯一的亲人喜爱,只有与自然为伴,与河流交谈,亚瑟的处境也暗示了即将搬过来的杜薇恩小姐的命运:离群索居。
杜薇恩小姐搬到云铎河附近居住,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欣喜、好奇或者不安、沮丧。外部环境的变化早已不能对她有什么影响,她还是按照自己的模式生活着。虽然有时候她的某些行为在别人看来是那么匪夷所思。“她会将一株植物挖出来挪到杂草丛生的地方去栽或者将一个盆栽移到杂草密集处摆放;过不了几分钟她又将它们都复归原处,时不时地,她就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个稻草人一样,就好像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3]。杜薇恩小姐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打理花园,消磨时间,思考问题并不露痕迹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
不管在外人眼里她的行为有多怪诞,杜薇恩小姐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过活每一天。虽然她的“有悖常理”经常惹恼科宾小姐,“她(科宾小姐)总是朝杜薇恩小姐发火,就像对着电线杆讲话般地和杜薇恩说话”[4]。即使被堂妹孤立,杜薇恩小姐也不认同固有的传统标准,她的这些行为举动正是她向男权制社会无声抗争的反映,谁也无法阻止她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始终。
在男权制社会,评价女性价值时,“往往不是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根据每个个体的具体行为和成就来判断,而是用一个先定的统一的所谓‘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固有标准去求全责备。”[5]而这种固有标准则完全根据男性的喜好和观点决定,杜薇恩小姐对“自我意识”的坚持,有违传统,但正是她对男权制社会的不满抗争。
杜薇恩小姐常常形影相吊,显得十分孤独。然而她并不寂寞也不空虚。“孤独”是因为她“与众不同”,是因为她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生活在男权制社会中,杜薇恩小姐的思想却没有为男权制所固化,而这一点又让她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交圈内,所以她总是形单影只。但是这并没有让她消极厌世,反而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自己,也让她对未来的可能性充满了希望。女性意识的觉醒之路漫长而艰难,杜薇恩小姐作为一名先锋,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已经做好了孤独前行的准备,然而走在这条路上的她也绝不可能是一个人,所以孤独者并不孤独。
二、杜薇恩小姐的 “不幸”
在男权制社会,女性出嫁前依赖父亲生活,出嫁后则依赖丈夫生活。没有嫁人的女性则会沦为他人嘲笑的对象。到了华发满头的年纪,也还没有嫁作人妇,从传统观念来看,杜薇恩小姐真可以被称作是“不幸”的代名词。但是,她本人并没有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从而自怨自艾,她在姐姐的婚姻中看到了男权制对女性的迫害以及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扼杀。
杜薇恩小姐的姐姐——卡洛琳,是个富有魅力,长相出众,并富有学识的女性。“亚瑟,我姐姐——卡洛琳,也就是后来的比特夫人,是个十分优秀的女人。她的丈夫——比特上校,是个军官,为人绅士,这点我认同。但是,我姐姐她并不快乐。也许那次意外对她来说就是个解脱:我姐姐被人发现溺水身亡。……还有她的眼睛一直睁着,湛蓝的犹如‘勿忘我般”。[6] “那他们把她的眼睛合上了么”?[7]
杜薇恩小姐的姐姐和姐夫的婚姻(绅士与淑女的结合)无疑是符合男权制对婚姻的要求:门当户对。在外人看来相当登对的婚姻却无法带给卡洛琳幸福,反而在杜薇恩小姐眼里,姐姐的死亡对其来说是真正的解脱。卡萝·佩特曼认为,“婚姻是男女之间订立的契约。实际上是他们同意父权制规定的男尊女卑的身份。”[8]而像卡洛琳这样受过教育,思想不再受禁锢的知识女性对其自身的价值有着更为深层次的追求,她们不再是男权制里的丈夫的附属品,不再一味地只知委曲求全,反而迫切地想要呐喊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出自身的价值。毋庸置疑,这样先进、另类又带有颠覆性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男权制的抵制和压迫。正是由于被排斥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之外,卡洛琳才选择了自杀。
杜薇恩小姐认为姐姐的死亡对其来说是幸福的。在现实世界里难以实现的梦想,步履维艰地前行所带来的痛苦,婚姻生活所带来的束缚和压力让有独立意识的卡洛琳饱受精神折磨,卡洛琳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反抗着扼杀她生机与活力的不平等制度,所以她的眼睛没有合上,她自始至终睁着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冷眼看着这社会。“亚瑟,我想向你传达的是,我姐姐,卡洛琳,是一个聪慧的美丽女人,她内心坚定,思维清晰(根本不可能精神恍惚)。所以当他们把她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时候,我发现她溺水的姿势就好像是准备好了迎接死亡一样”[9]。对于当时的卡洛琳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却和死了毫无区别。于是卡洛琳用生命来表达她的不满,来宣示她的抗争,她的妹妹——杜薇恩小姐正是能理解她的人。
杜薇恩小姐终身未嫁,可是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恋爱过,只不过她的爱情没有以婚姻的方式结尾。“这儿,我还带着他的画像……那是一张镶嵌在盒式吊坠里的图,一位政府官员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副慵懒的,难以取悦的神情……亚瑟,你知道的,不应该沉湎于过去,这样子或许也是没教养的表现。有一天,你也可能会爱上一位可人的姑娘。我恳求你,对她真心实意。不要像这个人”[10]。传统观念通常把婚姻看做是女性的最终归宿,是女性获取幸福的唯一手段。然而终身未嫁的杜薇恩小姐抱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宁缺毋滥,在认识到恋爱对象的虚伪之后,即使依然深爱着对方,杜薇恩小姐还是没有委曲求全,步入婚姻的殿堂。传统观念里的不幸对于杜薇恩小姐来说绝非不幸,和姐姐卡洛琳的激进相比,杜薇恩小姐则更为隐忍,就像早就知道前途艰辛,需要耐心和毅力才能将信念贯彻始终。
结语
杜薇恩小姐虽然离群索居,但她并不感到孤独:思想的自由,对未来的希望让她更感生活的充实;虽然终身未嫁,但绝非是外人眼里的不幸。如果步入婚姻是要以牺牲“自我”、对男性委曲求全为前提,那么一个人独立自主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综观《杜薇恩小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德拉梅尔笔下的这位新女性形象在观念上给人们以震撼与改变,给女性主义者以支持和鼓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想要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也必须抱着坚定持久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哈里·布拉迈尔斯. 英国文学简史[M]. 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09.
[2][3][4] [6][7][9][10] 瓦尔特·德拉梅尔. 短篇小说: 1895-1926[M]. 伦敦:贾尔斯·德拉梅尔出版社,1996:40,40, 41, 41,42,45, 45,49.
[5] 贺萍. 性别视角下的透视——哈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143-145.
[8] Pateman, Carole. The Marriage Contract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78.
[11] Whistler, Theresa. The Life of Walter de la Mare[M]. London: Duckworth Publishers, 2004.
[12] Selden, Rama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