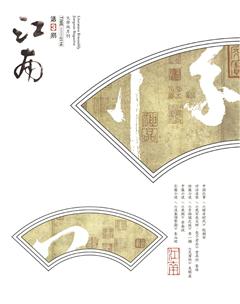今天,文学还有重提“先锋”的必要吗?
罗皓菱
背景
“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先锋文学的时候,它完全变成了理论家、批评家眼里的一些概念,毫无生命感,我无法用语言来复原那个年代的文学,它的生机、蓬勃和热情。”隔着微信语音的距离,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马原声音底层的热情,就像墨点慢慢浸透纸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残雪、格非、刘索拉、徐星、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作家,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以创新为号召的“先锋文学”浪潮,引起了巨大反响。三十年前,先锋文学如何发生?三十年后,如果重新评价那场文学浪潮,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先锋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先锋文学的发生
主持人:先锋文学的出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苏童在去年北师大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论坛上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大幕拉开的时候,所有人好像都在“裸奔”,最初的台词说完之后,大家才发现剧本没有写好,戏不知道怎么演下去,而之后的创作才是在考虑要不要穿衣服,穿什么衣服。作为在场者,我特别好奇的是当时那些创作都是如何发生的,有一种自觉意识,还是完全的误打误撞,出于一种模仿?
马 原:我认为是历史走到了那一步,因为当初我们这些在方法论上寻求突破的尝试,实际上不是开始于大家认为的80年代中期,我们少年时期就开始这么写。作为同龄人,传统的写法很容易被接纳发表,我和张抗抗写作的时间差不多,当她已经成名的时候,我的东西还是发表不出来。其实,怎么写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但是当代小说一直只关心写什么,内容至上,所以在我们这拨人出来之前,中国的小说一直在内容至上的藩篱当中,当小说真正走向怎么写的时候,小说才会像笼子里放出来的老虎一样。先锋小说这顶帽子实际是在其后十几年里陆续形成定位的,当年并不叫先锋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但是核心还是小说的方法论,方法论革命已经到了火候了,中国小说应该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当中,我认为这才是历史的大趋势吧。那个时代后来被归结到先锋小说的这批人,他们不是光有一点革命的愿望,改变的念头,直到今天,30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中国写得最好的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文学近五六十年的历史当中,他们一定是写得最好的一群,那个时代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不在今天先锋文学的名单上,但他们非常重要,万之、陈村......他们就是那些一直在关心小说该怎么写,小说方法论的先驱者,还有阿成,我们这些人是在80年代初认识的,那时我已经看到了有一种潮流,就像地下奔突的烈火一样、岩浆一样,有一种力量在积聚。
李 洱:我虽然在先锋文学出场仪式的现场,但只是一个坐在替补席上的旁观者。那天在北师大,苏童谈“裸奔”,是一种自谦,没有必要当真。别的几个作家当天也都在极力地谦虚。没有任何写作者,在他写作的时候,什么准备也没有。怎么可能呢?我相信那是一种自觉意识。他们不愿写以前那种老套的小说,想换一种写法。他们的阅读经历和知识结构,怂恿并支持了他们的写作。他们是最有才华的一代作家,这一点已被后来的文学史证明。所以,说他们误打误撞,那是对情况不了解。
主持人:要不要穿衣服,穿什么衣服,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创作者都有不同的答案,爱尔兰作家托宾先生来中国的时候,我也问过他有关“裸奔”的问题,他当时的回答是,“裸奔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你也可以试着穿上一点比基尼。”余华也说这个问题是怎么也扯不清楚的,你们是怎么看的?
李 洱:托宾说的裸奔和我们那天谈的裸奔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你听了当天的发言,你会发现,我们那天所谈的裸奔,语义复杂,其中一个意思,是要简单明了地解释先锋作家后来为什么要转向,其中包含着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现实,小说家需要重新建立文本与现实的对应关系。有些写作,在当年是有效的,比如说暂时隔断文本与当时的文学史的关系,与当时的政治的关系,使文学尽量在一个审美空间中展开。但是今天,一个有责任的小说家,是不能这么做的。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奇特的一面。
格 非:苏童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裸奔”,我觉得裸奔也不太重要,重要的还是后面还要穿衣服,要不要穿衣服,穿什么衣服。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他有一篇小说叫《青春》,我每次看都会有一种感动。就是这个船要沉的,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小艇都知道放出去了,所有的水手都要转移到那个小艇上,主人公到大艇上叫所有的水手撤退,他们发现跟风浪搏斗了好多年的水手在甲板上大吃大喝,船上火已经熊熊燃烧,马上就要爆炸。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青春,青春是什么,完全的无所畏惧。“裸奔”这个词,我相信我们的想法可能是一致的,没有准备,也不知道外面的行情,读了一些书就开始写作,靠的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记得当年读大学特别喜欢杰克·伦敦,那种洋溢的精力怎么发泄也发泄不完,那种东西在促使你写作。我们那些人在文学准备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开始写作,无所顾忌地去创作所谓自己的东西,我认为不光是文学,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中国的电影,当年你说张艺谋什么也没有,可就敢拍。陈凯歌也什么都没有,就敢拍《黄土地》。崔健、中国的先锋音乐、绘画,所有的领域都一样。大家一起去尝试某种新的文体、新的方法。
黄德海:所有的比喻都是跛足的,这个比方尤其如此。怎样算是穿衣服?索性把这个比方再使用得彻底一点,只有真实发生的一切才是赤裸的,一切行之文字的东西,无论怎样说,都已经是穿着衣服的。这么看,先锋文学就是穿着新衣服的文学。
主持人:对于所有当时那场文学浪潮的在场者,总是会不断被人问到为什么不坚持先锋到底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就像是问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变老呢?为什么不一直停留在青春期呢?但是,我后来又觉得这个问题又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能所珍视的是一种文学上的“反叛”“创新”或者说“实验”精神,那种敢于推翻一切的勇气,这些珍贵的品质为什么后来消失了呢?
格 非: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比如说80后、90后、00后他们的青春时期,他们不屑于做这样的东西?当时,我们这个国家好像不知道往哪里去,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的,大家都在考虑国家要往哪里去。80年代对整个国家来说可能也处在某种非常不成熟,尝试的一种时期,我们这些人刚好处在那样一个大的背景里。有人反复问我们为什么不写那样的作品了,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时代转眼就没有了,支持你写作的那个氛围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写作?怎么写?每个人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
李 洱:今天,所有的篱笆几乎都已经拆除了。说实话,我看很多年轻人的作品,以先锋和反叛面目出现的作品,包括引起一片叫好声的作品,说那是前人玩剩下的,都已经不诚恳了。应该说那都是前人已经玩过的,已经没兴趣再玩了。今天的文学,有另外的课题。
任晓雯:反叛和创新只是文学可以做的事情之一,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文学里不存在“推翻一切”这种事情,任何一种先锋都是有传承和出处的。
黄德海: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更为切要的问题,是敢于“反叛”和“创新”的精神消失了,还是我们因为精神的怠惰,已经不善于辨认“反叛”和“创新”了?我们在那场规模浩大的、先锋显而易见的文学浪潮里知道里面有着先锋,有着反叛和创新,而在这浪潮过去之后,先锋精神化整为零,反叛和创新隐藏得更为复杂的时候,不去细致辨认这一切,而是轻易地说这珍贵的品质消失了,是不是显得我们缺少一种辨认反叛和创新的精神或者能力?
马 原:那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先锋文学仅仅是实验而已,其实根本不是。我这么看,如果说小说历史上应该一直有先锋的革命的力量,这个事情是一代一代的小说家们都在自己的时代把这列车向前推动,也许前进一公里,一千公里,一万公里,但一直有不同时代的新的小说家去推动这个车轮,于是革命一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力量。我不太爱对先锋小说历史发言,我想说的更多的是自己,不能代表别人,他们有自己的写作历史,跟我很不一样的心得和体验。可是肯定的是,80年代末是一个节点,中国的读者和公众突然失去了对小说的兴趣,毕竟写作这个行当是作者和读者一起构成的。没人读,对小说的不关心、漠视、遗弃都是先锋文学戛然而止的最主要的因素。先锋小说被文学史家定义以后,大家就根据那个定义去判断小说是不是还有先锋精神,小说还有没有那种披荆斩棘的势头、态势,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不认同这种说法。在这里,我愿意声明,小说可能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一片阴凉,但是小说从来都是个人行为,写作从来是个人行为,所以我说千万不要把某一场文学运动、文学革命、文学造反看成一种社会潮流。小说是小说家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自说自话完成的,它是个人行为。这么讨论,其实都是在概念上面的,概念上的讨论很奇怪,没有一点生命感和活力,没有一点生机。但是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其实是充满生机的,澎湃、热情。20多年以前,我就说80年代中国小说是世界上最有生机活力的小说,这个群落肯定是最有意思的,同时世界各国的小说也都翻译过来,他们没有我们精彩。当年,那个时代真是个火热的时代,现在想起来依然非常亢奋,但是说来说去没有意思。唯有重复重新阅读,靠嘴说很难复制当时激动人心的林林总总。
二、世界视野下的先锋文学
主持人:中国先锋文学运动放置到世界现代文学潮流中处于什么位置?有人就觉得相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世界潮流,中国所谓的先锋文学其实并不先锋。
任晓雯:我就是提问中所说的“有人”。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空白处的异军突起,是追着赶着走完人家早已走完的路。
李 洱:你只需要看看,这些年最多被翻译的作品都是先锋文学作品,就知道在世界文学潮流中,先锋文学,或者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或者从先锋文学中走出来的作家,他们是可以被世界文学接受的。莫言难道不是先锋作家吗?肯定是。
杨庆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是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出一种世界文学的图景。在这个图景里面,文学的特殊性和通约性整合在一起,并没有一种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先锋文学。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并不先锋的观点,不过是“白人才是人”之类观点的翻版。
黄德海:中国先锋文学运动放置在世界现代文学潮流中,就是“中国的”先锋文学。它或许看起来不够先锋,技术上有很多模仿,精神的探索上也走得不够远,很多作品也很难称得上有所谓的普世性。可是,这样的先锋,也是中国的先锋啊。因而放在世界上,也是有其位置的。就像我们不能说,被虫咬过的果实不是果实,经了风雨的树木不是树木。说不定,正是因为虫噬和风雨,这果实和树木反而有其特殊的样子。当然,前提是这些作品真的是认真而耐心的,其缺陷能让我们看到虫噬和风雨。
阿 乙:20世纪文学,可以将之比喻为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相对于19世纪有极大的革新。中国是在80年代搭上这列火车的。中国作家虽然处于学习状态,但他们表现出的天赋和实力不容忽视。而且现在看来,假如没有这一批先锋作家,中国文学将不堪想象。余华、苏童、莫言、格非、孙甘露他们的实力并不弱于同龄的外国作家。以后他们的成就还会得到一次重估。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文学在那个时候是活跃的。哲学、诗歌,很多事物都是活跃的,创造者和受众都很振奋。
张 莉:世界文学意义上的先锋派运动与中国的先锋派运动肯定是不同的,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历史语境都不同。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先锋派运动是西方进口产品,也深受西方先锋文学影响。你去梳理先锋派作家们的阅读谱系,几乎全与外国文学作品有关,这是一个证明。我记得余华说过他是喝着外国文学的奶长大的,很对,一点儿也不夸张。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先锋派作家与西方欧美先锋派的关系。顾彬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先锋时期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先锋派文学没有让他感觉到新鲜的东西,他觉得原创性不够。这样的评价我第一次读到时觉得很有冲击力,这是与中国文学研究者不一样的视角。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视角?因为他身在欧洲,先锋派作家的写作技巧和他们的文学尝试都是欧美文学玩儿剩下的,所以,他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放在中国文学语境里呢?先锋文学又是那么重要,它是一个重要文学史的发端。那么,评价中国先锋文学的意义时,要放在哪里评价更切中?要放在法国文学或者德国文学的语境里吗?我认为,作为学者,了解所研究对象发生的历史语境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先锋文学是否有原创性、是否是步西方文学的后尘,都不影响我对它的历史意义的评价。那是革命性的一刻,如果没有先锋文学,就没有余华、格非、苏童,也没有莫言和林白。没有先锋文学,就没有一大批中国重要作家的出现。先锋文学深远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它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说80年代世界各国文学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画出那个影响的地形图吗?
马 原:有些肤浅的批评家,他们因为后来看了几本书,他们就套用现成的概念,觉得中国的先锋小说就是模仿,这特别幼稚。写小说的人比他们清楚得多,实际上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关心方法论,我相信没有谁不关心方法论,只不过在一个大的潮流趋势下,方法论没有很大的空间施展的余地。一旦时机成熟了,有了,情形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新小说出来像一场革命一样。西方文学的引进仅仅是一个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大趋势,抱残守缺的文学一定是很局限的文学,一定是一个很没出息的文学,革命、突破这些历史趋势实际上是更主要的动力,引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动能。
李 洱:我可以细致地画到毫毛,可以画到每个重要作家的演变轨迹。不过,这个工作还是交给文学史家去做吧。因为他们的误读,一来可以当成小说来看,饶有趣味;二来可以激发或鞭策作家们的创作。
任晓雯: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对于当时先锋诸君的阅读书单很感兴趣。
黄德海:如果收集的资料足够丰富,我相信可以画出一副极其复杂精微的精神传播地形图,想想都觉得精妙无比。如果这幅精神地形图出现了,所谓“80年代世界各国文学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会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可能,却同时标示着这一结论本身的不够完善。
杨庆祥:我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有其内在的诱因。从文学史的角度看,80年代的先锋文学更像是对此前社会主义文学的反动,而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模仿。当然,内在性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引爆点,80年代对世界文学的大量翻译就是最重要的引爆点之一。
三、先锋文学的传承
主持人:张莉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天的年轻人并不热衷先锋文学,除了在课本中学习,在阅读中几乎很少像阅读《平凡的世界》一样感同身受,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先锋文学更像一种文学潮流,而缺乏经典作品。你们是怎么看的?先锋文学对你个人的创作有影响吗?第一次读到是什么感受?
路 内: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刚开蒙的文学少年,读到先锋派的作品,倒不是惊讶,而是觉得自己读不懂文学作品,就像做不出数学题一样,一定是自己有问题。那个时候,我高中理科的朋友也会拿着格非、残雪的小说给我看,讨论它们的内涵。就是那种很天真的、解函数题目的方式,以为这样就可以搞懂文学。至于说先锋派叙事方式什么的,当时是没概念的。到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认识的80后的小朋友,对先锋派作家非常熟悉。但那时更熟悉的是一批很“垮”的作家,韩东、朱文、棉棉。那时的用词就变得很街头了,“牛逼”这种词大体就是用来形容那一时间段的作家的。用在先锋派作家身上会觉得古怪,文绉绉的80年代,“先锋”这个词大概就相当于后来的“牛逼”。又过了十年,网络用词叫“大神级”的作家。所有这些称号,都有别于“经典作家”这个词,经典作家是文学史的用词。今天,先锋也被放进了文学史中,但“牛逼”和“大神”不可能,因为粗俗,不合文学本色,但它们无不表达了文学青年们的喜爱或赞赏。有很多先锋派作家,到现在都是“大神级”的作家。他们返回去写先锋作品,也仍是大神,而不会再被冠以先锋这个过时的称号。
任晓雯:先锋文学不是为了让人“感同身受”。如前所说,文学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在我看来,先锋是一种少数派姿态,是一种与主流疏离的态度。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品早已摆在文学史之中,而强大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也早已吸纳了很多当年先锋文学的创作手法。我最早的写作,完全受了先锋文学的影响,它让我有一种文体自觉,使得我后来哪怕在使用看似最老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时,也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并非在说故事,而是在写文字。我能够凭借文字,走到比故事本身更远的地方。我是在大学里开始阅读先锋文学的。我记得第一次读《等待戈多》,老实说感觉很乏味。但是当时拿先锋文学和文艺青年们交流,会觉得自己很酷。而谈论托尔斯泰则是一件显得老土的事情。正是出于这样幼稚的虚荣心,我开始大量阅读先锋文学,并开始尝试一些所谓“先锋”的诗歌。
阿 乙:我的创作受先锋影响极大。余华、格非、苏童、莫言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路遥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小。首先我觉得先锋的作品是有品质的。这种品质是语言上的、叙事技巧上的、也是主旨上的。从他们开始,白话文作品才洗掉了一些土气。
杨庆祥:今天的每个人的阅读经验不一样。我的阅读经历是先读先锋文学,尔后才陆续读到如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先锋文学奠定了我基本的美学趣味,甚至是我的美学惯性,后来读到路遥和赵树理,反而有一种陌生感。据我在大学任教的经验,现在的大学生们确实不太爱看先锋文学,不仅是不爱先锋文学,严肃的文学阅读都已经被取消或者说取代了。历史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文学所奠定的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人生的联系纽带已经断裂。文学已经不是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语境中,不读文学已经很正常,何况是本来就很小众的先锋文学。
蒋方舟:年轻人不读先锋文学,大概是因为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对于先锋文学的审美还没有建立起来吧。年轻人读《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因为那是学校和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是经过官方认证过的“好”,所以年轻人觉得很受震动。关于先锋文学,我们的基础教育还不敢贸然说“好”,所以年轻人接触到的机会也不会多吧。我印象深刻的先锋文学,是大概2002年,我上初中的时候,读了马原老师选编的一本《大师的残忍:我最喜爱的恐怖小说》,选了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说,作者包括博尔赫斯、考德威尔、奥康纳等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博尔赫斯的一篇,写到同胞兄弟共同占有一个女人,当他们觉得这个女人让彼此生出嫉妒的时候,就把那个女人除掉了。我那时候觉得:“哇!这么狠!”而这种狠又非常合理。后来读到余华的《古典爱情》等国内的先锋作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拓宽了对文学的认知吧。文学亦可为罪犯写传,倾听刽子手的声音。
郑小驴:刚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最先吸引我的也是先锋文学。那时阅读了余华、苏童等人大量的作品。像《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在细雨中呼喊》《1934年的逃亡》等很多作品,最初给过我一些文学上的滋养。或者说,它提供了写作另外一种可能性,对语言和文本的理解具有很强的游戏性和探索性精神。小说既可以写成《白鹿原》《废都》这样的,也可以写成像余华、苏童他们这样的。对于后者,我当时抱着一份天然的偏爱,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觉得写一部《白鹿原》的难度要大得多。先锋文学后来之所以式微,我想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形式大于内容”上。它告诉你“怎么写”,自己却死在了“写什么”上。而且中国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对西方文学的一种借鉴和模仿,它并没有在别人的基础上将路子走得更远、更宽。这些都是中国先锋文学没能持续下去的原因,所以后来的先锋文学作家开始转型也是必然。
主持人:文学为何丧失了“先锋”精神?如果说先锋是青春的另外一种指称,每一代人是不是都应该有“先锋”的精神面相?还是说每一代人的写作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当那个氛围消失了,个人也无能为力?
李 洱:我们所指认的先锋文学,它所产生的那个语境已经变了。先锋文学产生的最大的语境是,当时绝大多数文学不是文学,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在我们尽可以指责,他们脱离了政治,它们没有直接加入当时的启蒙运动。但文学史家有必要告诉人们,他们当年脱离政治就是最大的文学政治。当他们写下那些幻想性的文学的时候,他们有如飞越疯人院。现在,语境变了。
杨庆祥:文学并没有丧失先锋精神,而是先锋精神已经发生了位移和扩散。80年代的那种先锋性已经转化为一种基本的修辞技术。80年代建基于“对抗”的先锋精神也已经失去了它的互文性基础。那么,今天的先锋精神是什么?需要批评家和作家有意识去建构。
蒋方舟:关于这个时代的先锋文学为什么不再那么兴盛,大概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变得更难定义了吧。人们的阅读习惯变成了在网络上阅读,文学的载体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社交网络。我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在微博上发表小说,题材和写法也是奇特而荒诞的,可它们能够被“文学史”接纳吗?我不知道,这种写法算是“先锋文学”吗?我也不知道。
任晓雯:我不认为先锋是青春的另一种指称。至少对于我自己,在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先锋时,我已经不再青春了。我不太去想“一代人”或者“历史语境”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我个人眼中,整部文学史是扁平的,没有历史和地域的区分,有的只是一条以私人标准建立起来的优劣评价轴线,所有曾被人类写出来的文学作品都分布在这条线上。而我唯一要做的事,是把我自己的作品,往“优良”那个方向上稍微挪一些。我甚至不需要去关心“主流”在哪里、大部队在往哪个方向走。有时我或许会离主流远一些而显得先锋,有时我或许会完全泯灭于主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路 内:对于历史的特定语境这个说法很赞同。90年代初期,实际上先锋派已经结束了,但我当时阅读的大量作品都带有先锋写作的痕迹。很多作家,现在已经不被提起。也就是说,我认为先锋小说不是终结了,而是稀释掉了。它成为了当代文学的某种基因,有时候你会在某个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一眼看出先锋的影响,有些作家则终身与此不沾边。这种基因,既有传承,也有演进。尤其是叙事句法上,因为汉语小说的叙事句法无法完全拷贝翻译作品,会产生翻译腔的所谓弊病,先锋派的句法和节奏似乎是它的最强基因。仅就此来说,不应遗憾。
主持人: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有重提先锋的必要吗?或者说未来可以预见到类似8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文学实验吗?
李 洱:我依然认为,重提先锋文学很有必要。文学史当然绕不开,小说家则需要以自己的方式重建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几乎是小说家终其一生的使命。我把这种精神,称为先锋精神。大规模的文学实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对写作者个人来讲,你的写作每天都在实验。你在不停地对焦,你在书写中艰难地寻求对话:与自己,与历史,与现实。
杨庆祥:我只想再强调一点,文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已经不重要了,非常不重要。因此,文学仅仅对个人产生意义。在这个语境中,任何对文学抱有的集体主义或者运动主义都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
阿 乙:文学总是在实验。重复已有的成功,容易使写作变成商业生产。80年代先锋最大的遗产是:作者在追求高级的读者,在追求世界范围的交流。今天我觉得有的作家堕落,正是在于他在用一大批看电视剧的读者来交换以前的精英读者。
张 莉:尽管先锋文学是重要的,值得尊敬的,但我还是觉得它没有留下经典的作品,这是至为遗憾的地方。我认为,与现实的对抗与紧张关系、疏离感是先锋文本的重要特征。如何理解虚构与真实、现实的关系,是先锋文学遗留下来的至为宝贵的文学财富,也是一代作家在形式探索外壳之下所做出的最核心的文学贡献。余华、格非、苏童在年轻时代完成了向惯例和写作成规的挑战,从而也为自己开出了一条新路。但是,今天的新一代作家只是偶有几位意识到如何理解文学与现实这一问题的重要,大部分作家面对现实的态度是缓和的,亲密无间且不带反思意味的,这也意味着先锋文学的重要财富并未在更多年轻人那里得到回响,年轻一代也谈不上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创新之路。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有重提先锋文学的必要,不是重学先锋文学的书写方式,而是重新学习它的先锋精神。
蒋方舟:我最近在东京访学,看了很多漫画。真的非常奇妙,所有的题材都可以被画成漫画: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学的。比如我看了一部讲夏目漱石等明治时期文人的漫画,非常好看,恐怖的、奇幻的、反乌托邦的。我自己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在于它拓宽了我对文学的认识。漫画家也同样在展示他们的世界观,更新他们的技法和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但他们比小说家幸运,他们能接触到更广泛而大众的群体。文学的受众还是太狭窄了,所以要不要重提先锋文学不重要。不断地写、以各种方式写、以各种技法写、以各种想象力写,并且最大程度地触及活着的大众,这才是最重要的。
任晓雯:不知道“重提先锋”的主语是谁。写作是一个私人事件,每个人都有选择写作风格的自由。形成规模和潮流,并非出于写作个体的意愿。
路 内:没有必要重提。要求应该更复杂了:阶级、意识形态、语言、诗性、认知和视野、全球化……其中一些似乎是九〇年代开始就提出的文化问题,已经越过了八〇年代的先锋派。把小说写到难读,或语言的华丽,结构的繁复,但可能仍无法掩盖一个作家在认知上的幼稚。因此我觉得,文学实验如果仅限于文本,可能只是一些个体的事情,不太会成为规模。如果有大的社会或科技变化,影响到文学,这就不在预料之内了。
马 原:当然不可能再有了。我已经说过,20多年前就说过,我们是小说这台节目的最后落鼓,小说已经进入博物馆,成为博物馆艺术。现在还在做小说的人只不过是因为情怀,绝不是因为小说这个物种还在。小说真的像诗、话剧一样走进了博物馆,小说已经是博物馆艺术了。一种博物馆艺术,你能够期待它引起全体公众的热情、还有一个黄金年代吗?
黄德海: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重提什么主张,引来什么潮流,让作家安安顿顿地写自己的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样子,不是很好吗?规模浩大的浪潮,总是因为背后更为浩大的灾难或运动。如果我们不希望那些灾难或运动再来一次,那就不要期望这种大规模的文学实验了吧。当然,如果有一天,这种实验真的来了,那就是来了,期望真的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