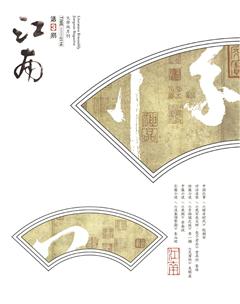灵薄狱
吴明益
象从梦中醒过来,眼前的森林一片火光。尖锐、前所未闻的咻咻声穿过林梢,每个闷响都伴随着几棵树着火。烟雾四起,温暖得吓人,太阳一样明亮的金色火球在几分钟内不断升起落下。
象狂乱不安,伸长鼻子,张开耳朵,发出高亢的喇叭声。长老象围绕着幼象,把它们推到圆圈的中间。一个被炮弹碎片击中的驯象师说:“带着象走另外一条路!另一条路!”
象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被卷入这些事,象的身体、象的意识、象的经验都没有给予它们去面对这样世界的能力。作为一头已被驯服的象,它的生命除了饥饿、发情、睡眠以外,还多了背负,它唯一理解的事是:只有听令于驯象人才有食物,才不会受惩罚。
象在驯象人的带领下,依序通过一条被火光照得发亮、漩涡处处的河流,进入对岸那片更深的丛林。它们不安地摆动着鼻子,嗅闻四周。很快它会发现,每一枚这种被人类称为炸弹的东西都创造出一种新的气味,端看它击中哪里,把什么东西化为烟雾。如果炸毁的是石头,浮起的烟尘就会发出石头的气味;如果炸毁的是树,那就会产生那种树的气味;如果炸中的是人或兽,将会是一种全新的嗅觉经验,被烧烤过的动物尸体没有死亡的悲哀,反而带着一种香气。
但此刻象并不知道,逃离火的森林并没有脱离战火,没有脱离永无止境的背负使命。战争并不是穿过一座森林、越过一条河流、翻过一座山那类的事。
象的身上背着一个依照它的肩宽所打造的大木架,然后听从命令,用鼻子将沉重的木箱放进木架里。
即使背负了重物,象的步行依然几近无声,那是因为垂直的巨大脚骨承受了惊人的体重,脚底的软垫则缓冲了压力的缘故。面对陌生的道路,象习惯先以长鼻试探前方的气味与状况,接着肩头往下一顶,肩胛圆圆鼓起,膝盖曲弯,带动那覆盖趾甲的宽脚从泥地上稍稍抬起,往前画出一个半月弧,而后伸直膝盖,重新放下,肌肉相互牵曳,脚趾扩张。那步伐从容、安静,几乎让人以为象无所畏惧。
象已经在这个世界演化了千万年,它们的外貌显示出生命如此被动又主动、定向又无定向地回应环境。它们的头骨前后距离渐渐变短,上下渐渐变长,臼齿齿板由少变多,齿上的珐琅质由厚变薄,鼻吻与象牙在一万年一万年的尺度里微幅增长。象的身体就是时间本身。
曾经象是这片丛林、山脉的精神,它们巨大又罕行杀戮的身躯是慈悲的化身,细小却闪现智慧的双眼暗示着情感与灵性。
人们曾经崇拜象,以为象有知晓人类命运的灵通;当时他们仍然认为,人是动物里最微不足道的,最缺乏与神沟通能力的一群。
但那个时代过去了。
象适应了这片丛林,此刻正在学习适应天空掉落火球,铅弹穿透皮肤、卡在内脏里头,随时都在发生森林大火这样的事。它们无言地听从驯象人,而驯象人听从另一群操用陌生语言的人,或许那些人也听命于另一种象不能理解的主宰者。一条又一条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他们,没有人知道怎么挣脱。
某一日在竹林歇息时,“另一边的人”将驯象人骗走。事实上,骗走了驯象人等于带走象。象回头看见一个与它最亲近的驯象人与一名士兵逃进那个比战火更没有希望更残忍的丛林里,知道自己从此将会跟从年幼照顾它的驯象人走向不同的道路。
但象似乎也感觉到,被“另一边的人”带走对自己的命运而言并没有任何差别──依然要面对饥饿,难以控制的情欲,贫乏的睡眠与沉重的背负。
只是彼时象也没有预料到,它们将跋涉千里到山另一边的国度去。当象群被驯象人驱使北行时,远远看见一条巨蛇趴在群山之中,在山腰与山脊之间绕行,那是象演化以来从未见过的画面,一种不安定感油然而生。
象的鼻子里充满了令它们厌恶的、走在前头的骡子的气味,它摆摆头,试图摆脱那个,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嗅觉是无法关闭的器官。
队伍越过一个星期前仍在激战的野人山区,沼泽里堆满了尸体,残肢从树枝上垂挂下来,好像是某种不知名的寄生植物。到处都是被风吹得弯起如弓箭的树,兽穴遍布其间。它们跟着部队沿着罩着一层淡蓝雾气的河川逆流而行,走过春雨泛滥的山丘,直到人与象的腿上都爬满了水蛭,皮肤长疮,眼睑下方孵出长相奇异的寄生虫。无论身体承受多大的痛苦,象依旧缓步而行,因而显得庄严。
队伍走出丛林山路后,世界变得刺眼明亮,那儿没有森林,道路四周都是草木不生的孤丘与高山,风一吹就尘土飞扬。炙热的太阳让象频频扇耳降温,用鼻子吸取地上的红土,撒在自己和前后亲族的背上,借以缓和皮肤的刺痛感。碎石则刺烫得象脚趾肿胀,半月形趾甲的边缘淌出血来。士兵用死去士兵留下的军服帮象包裹受伤的脚掌,然而那丝毫缓和不了巨大体重加诸其上的疼痛。
只要队伍一停下来,象就开始用牙铲翻泥土寻找盐分和水,如果时间足够,它甚至可以用鼻子和牙、脚掌挖出一口井来。
如果能遇上一条溪流或泥浆池就是幸运的。象会愉快地长鸣,并且无视于驯象人的阻止进入水中。它们恣意地互喷溪水或泥浆,把象鼻伸进涌水处享受快感。但很快地它们就会体认到自己并非在野地,自由是奢想,士兵会毫不客气地在象的尾巴上点火。火带给象的不只是疼痛,还有像地质一样古老的恐惧。在见到火光那一刻,象忘记了自己是拥有力量的生物,它们变得卑微、怯懦、臣服。
象感受那个疼痛与恐惧,并且认定这就是象的一生所要承受的,象的一生,就是一个忍受各种折磨的梦。
所有的象群都有一种神秘的灵感,知道谁已经接近死亡。象的队伍里已经有五头象被死亡的阴影缠住骨头,它们正用象独有的低频发出悲哀、绵长的声响,表达痛苦。较具活力的象会在休息时张开耳朵,试着庇护这些幼象与病象。在缺乏水源时,强壮的象会把象鼻伸入嘴中,抽出珍贵的水来,送进病象的口中。
病象离前头的骡马部队愈来愈远,有时候要深夜才能赶到宿营地。它们几无时间休息,就像是一生都在走路似的。
敏感的驯象人发现了象群不对劲,通知了士兵,士兵通知医务兵,医务兵报告医官。医官试着为每头病象注射进三筒马的药剂,没有医过象的医官毫无把握。果然病象仍持续委顿,失去活力。
隔天正午,砰砰两声巨响,土地微微震动,一头公象以及年纪稍大的母象倒在自己的粪便与尿液里,发不出声音,做不出反应。公象的象牙在倒下时像玻璃一样折断了,它是群体中唯一成年的公象,才经历过狂暴期,此刻瘦得就像只有四条腿,尿液仍有强烈的费洛蒙酮体味。
两天后,另三头象接连倒地,它们巨大的耳朵平贴地面,好像在倾听什么似的,深深吸气,响亮吐气,微微张开嘴巴,摆动头颅,直到最后一口温热的气息离它们而去。
隔天黄昏,象群位阶最高的母象也倒地了。
象已经习惯突如其来的死亡,不论是人的或是象的。它甚至目睹过自己母亲的死亡。一枚流弹击中碉堡,周遭霎时被数以千万计的碎砖碎石笼罩,细碎的锐利物飞溅到母象头部、侧腹的肌肤里。连续好几个星期,驯象人替母象清理伤口,挖出一个水桶的铁屑与石头,但仍无法阻止死神。
人类有一天会知道,象和他们一样理解黑夜、森林、雨季与伤心。当长老母象倒地时,其他的象完全停步,围绕着它。它们用长鼻摩挲着彼此的背,发出不可思议的轻柔低哼声。夜晚气温逆转,较接近地面处形成较佳的传音层,那低哼声因此得以传到远方的山谷,而后又嗡嗡回响回营地。那被放大的、多层次的音响让一旁的士兵感到凄怆而温暖,他们体会到了象的伤心,因此也为自己伤心起来。他们想起了远方的情人与亲族、死去的同僚、曾经握着阳具与枪的断臂,以及不可能再长出来的眼珠。
象的睡眠远比人类短,因此士兵们在那个悲伤的夜晚先行睡着。醒着的象站立望着远方的星辰、山脉与树影,直到更深的夜让所有勉强活着的象都入睡。它们的鼾声逐渐绵长,逐渐和缓,就仿佛海潮环绕礁石所发出的圣乐。
隔天一早阳光出现,亿兆微尘、花粉、不到一毫米的昆虫四处飞散,世界迷蒙一片。士兵挖了一个巨大的坑,掩埋长老母象。此时排列最前头的母象发出了低沉却明亮的反复音节,一声一声像阶梯般逐渐扬起,到最高峰的时候,稍作停步,而后开始一句一句往下坡重归宁静。如斯三回后,第二头象加入,两个音场相互回荡;接着是第三头象、第四头象加入……那既非合唱也非重唱,而是各自情感流动的即兴哀鸣,却又像爱抚般彼此对话。每一头象前额鼻道和头骨间微微跳动,空气中的声音有生命似的钻到士兵的身体里渐渐膨胀,让他们感到难受、恐惧、不知所措。十几分钟后那声音骤然停歇,领头的象迈开步伐,士兵们才发现自己满脸泪痕。那眼泪毫无目的性,因此流泪的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静与干净。
当象走进村落时,就知道这不是以前它所认识的任何一个村落,影子的位置已经变了,空气里的炊食气味也大不相同。
村落的人们看到部队并不惊讶,这是一个到处都是士兵的时代。但他们看到象队时,以为是一个恶作剧。他们互拍了彼此的脑袋与肩头,确认自己并没有分不清楚现实与梦境。怎么可能是大象呢?这世界上真的有大象?眼前是一群大象?
身形比一些房子还要巨大的象群在村落的街道间静静走过,或者沿着街道、铁轨,或者走上不稳的桥,人们跟在象群后头,仿佛着魔。这个村落贫穷而污黑,象看到死去的魂灵站在村子口,徘徊踯躅,在他们的亲族经过身旁时,伸手抚摸。魂灵也围观着象,并且以村民听不到的声音表达惊奇。
象高高举起鼻子,再甩回地面左右晃动,借以搜寻、嗅闻空中与地面各式各样的气味──黏附在路面缝隙间的蔬菜叶、破了的鸡蛋流出的浓稠蛋黄、打铁铺的风箱吐出的温热气息、一层层凝结在肉摊两侧的残余肥油……这一切都让象感到新奇又痛苦。它把长鼻蜷在嘴前,试图拒绝或品尝那样的气味。在一个鱼贩摊前,象闻到了刺鼻的蛤蜊、虾壳的腥味,这气味要到它搭上那艘拥挤的船舰,被载运到小岛时才获得唤醒、证实。
因为此刻象仍未理解海,未曾识得海。
多数的人看到小孩走近象时都赶紧把他们拉走,但孩子们总在大人没注意到的时候偷偷接近象──多么不可思议的巨大长鼻动物,就像是一本他们永远没有机会阅读的童话。
象也再次嗅闻到人类的婴儿。
战场只有死亡,没有新生。一个婴儿躺在小摊旁的藤车里熟睡,象把鼻子伸了过去,婴儿的母亲想伸手阻止,却被硬生生推开,直到驯象人赶来喝止。象对那样的气味既陌生又不那么陌生……它依稀记得野地里母象产出小象那一刻,也记得在故乡丛林的边缘远远嗅闻到人类村落婴儿降生时的激动。
就在那一刻,一头短腿黑色的猪冲到象队的前面,也许是刚刚的婴儿气味与此刻奔跑的黑影激起了象的兴奋感,它将长鼻伸出,以极快的速度把猪卷起举到半空,然后使劲往地下一甩。猪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就此死去。象举起鼻子高鸣,而后又若无其事地以安静、庄严的步伐朝前走去。
士兵们感受到象群的焦躁,以及一再经过小城镇可能引发的混乱(象推倒了一间民宅的墙,并且踩毁了农民新播的稻田),他们也担心象再有任何死亡——十三头象,只剩七头了。象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象征,是他们从那个丛林里杀死敌人,胜利并且顺利生还的象征,他们接获的命令是,务必带回活着的象。
于是指挥官决定驱象上车,为防止象的骚动,它们流着脓血的脚被绑上铁链,并且被强迫喂食盐水与药物。在药物的迷幻作用下象觉得自己能漂浮水上,它从未以这样的速度移动,从来没有看过这样速度下的风景。村落在眼前掠过,空气中满溢陌生树木与果香的气味,天空出现不可思议的彩霞,一队士兵在旷野中行走,夜色好像裙摆似的拖曳在他们身后,然后彩霞隐没,光隐没,星辰与大如银轮的月亮取而代之,照亮整个草原。
仿佛听到了什么,象张起耳朵──一波声浪把草压低了传送过来,第二波紧随其后,第三波稍缓,正在开花的茅草被声浪抑或是风压得忽高忽低,数十只巨大的鹤从那个草原里飞了出来,啪啪啪啪地掠过车队上方。
车子将象群运到一个大城镇,暂时性地停留下来。象的脚掌踩在石板路和发烫的柏油路上,它的耳朵不时传来河流的声响,让它怀念起潮湿的丛林,以及树枝与树叶拂在背上时,仿佛造物主在搔它痒的感受。
造化没有倾斜地执行着此等韵律:春去秋来、生老病死,没有任何感伤。对象而言唯一的小小感伤就是一天早晨醒来,克伦族驯象人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后来才学习的中国驯象师。那些带领象长大的人们已经完全离它而去了。
操持着生涩象语的新的驯象师命令象在人群之前蹲、跪、站、躺、翻……它们从战士变成马戏成员。那些围观的、被战争压抑的人们好久没有放松了,看到这种巨大生物的滑稽表演,觉得自己仿佛又找回了一点尊严。有些人大笑之后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交给缺了手脚的士兵,或把钱丢在象鼻握住的帽子里。
象甚至会在驯象人的命令下,把掉落地上的铜钱捡拾起来,那鼻子的灵巧动作获得掌声。
象队一边表演,一边前进。几日后到一个新城市时,迎接他们的是机枪般的爆击声,让象群一时陷入恐慌与困惑。它们并不明白,那是战争结束的消息,翻越山岭传到这里来了。
人们像节庆一样跟在象队的旁边走,他们手上抱着白糖、水果、馒头,扛着桌子、米粮、小孩与姑娘。士兵拿水桶装满了水,要象吸饱了,喷洒人群。一些饥饿的人群聚在灰黑静默、被炸弹轰掉屋顶的庙宇前,他们被水淋到时的欢呼声仿佛哭泣。
然而在欢庆过后,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队伍里的人与象都知道,战争不会走了。它霸占了房子、身体,不肯让任何人睡觉,即使睡着了也终身受那梦境侵扰。
即使是驯象人都不知道,象偶尔会在夜晚里,把那充满皱褶、粗糙的象鼻放在高出人的头部两寸的地方,嗅闻人的梦境,彼时它只能吸气,不能吐气。象并不为那些梦境感伤、痛苦、快乐,它们只是好奇。
这个晚上象把它的鼻子放在一个鼾声大作、沉沉睡眠的士兵头上。象的脑中因此出现了一棵巨大无比的树的影像,那广袤的树冠足足有五百个象步圆周。大树的气根四处伸展,有的十分粗壮地插入地面,成为另一根树干,就这样支持着连象都撼动不了半分的壮观树群。
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刀子各自闪亮,弹火从树叶的缝隙像鸟一样,穿进穿出,形成以树为核心的火的网络。想要杀死树的火线时而从附近的丛林、高草草原窜出,树则以炮火响应。树的枝叶紧密繁茂,使它看起来更像一只蜷缩的刺猬。
象飘浮在树上,看着士兵脑中这幅树与树、草原、丛林驳火的画面,它忍不住用象鼻子拨开树叶,寻找并揭露藏身在树杈里的每一个士兵,那些士兵无视于象,石头一般紧握着枪,扫视着前方。象如游戏般,猜测每一个士兵藏身之处,然后用鼻子掀开树叶证实。他们有的正在砍藤取水,有的正在嚼食芭蕉根与竹子,有的眼巴巴望着天空祈祷下雨,有的断了手,有的绑腿下空无一物,有的刚刚失去一只眼睛正在适应倾斜的世界,有的失去了部分的牙齿或者身上带着断裂的骨头……黑色的血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就像过剩的涎沫,沾染在肮脏的军服上,草地因为吸吮了血反而看起来温润而满足,只是颜色变得不那么翠绿。有一个士兵在草丛里像孩子一样哭,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哭。
突然间一个士兵因为树叶被象掀开暴露了位置而中弹,他闷哼一声掉落树下,蚯蚓、推粪虫和乌鸦聚在树下等待着那个时机一拥而上。
与清醒的世界不同,那些抢食者连骨头都吞噬殆尽,唯一留下的就是眼珠。因此树下与草地上有数十颗,不,数百颗眼珠遗留。眼珠就像珍珠一样在莽草里发着光,将丛林反射成一个圆弧状的世界。象伸长象鼻将那些眼珠啵一声吸进嘴里,含住它。眼珠的味道难以说明,据说在靠近瞳孔根部的地方有神经连结到大脑,因此每个士兵的大脑内容决定了眼珠的味道。
不久银绳般斜斜的雨鞭打树冠,太阳升起、落下,星辰明亮复又黯淡,苍蝇聚集在树上、树叶间与树下,各种昆虫像意念般嗡嗡作响;破晓之前亿兆片叶子不同步滴下露水,那微细的声音在丛林里回荡成啵啵滴、啵啵滴的声响,夜行的士兵刻意让爬树与脚步的节奏与水滴声一致,以掩蔽踪迹。炮弹劈断了一处树茎,再劈断另一处、另一处。象凝视了两度月圆、两度月缺的时间,巨树满布弹孔,却仍挺立如常。
死亡像低雨云一样庞大、暴烈、灰暗,树根一样疯狂地四处攀附、盘绕,几乎快把在梦境里的象困住。
只能吸气的象警觉到自己气息将窒,赶紧将长鼻收了回来,吐了长长一口气。它的额头上的皱纹因此多了几道,胃里留着那些湿湿滑滑的眼珠。它后悔自己的好奇,后悔自己总是无法控制地想去感受这些士兵的梦境。
离开城市后,象队的行军复走向与家乡类似的丛林山路。象为此获得了短暂的愉悦,因为可以再次吃到树梢嫩绿的树叶,以及尚未被猿猴搜刮殆尽的芭蕉。有了树荫遮蔽象的皮肤,伤口也因森林的力量而慢慢愈合。
森林的尽头是条大江。
在这里象第一次体验了搭船,并且誓言不再重历这种痛苦。士兵为了控制不愿上船的象,用小刀刺进它的耳朵里,然后一步一步把象拉到船上去。象站立船上,几度晕眩无法保持平衡。人与象都因为那样的恐惧,而决定把船停到最近的一个码头,继续步行。
如是象群晃晃悠悠、行行停停往下游而去,草原路、田间路、丛林路、水路、柏油路、石板路,象与士兵终于到了最后的城市。
这里是千里行军的暂时终点。
在那个城市里,象被驱使去驮负石头,搬运木材,踩平碎石。象窃听了士兵的对话,知道自己建筑的是悼念死者之地。死者的头盔、腰带、残肢或是衣服被埋进土里,当士兵敲钟时,它们以为听到的是枪声。
碑塔建好之时四头象被车辆载走,剩下的象被用麻绳做成的大网,从腹部捆绑吊上了巨大的船(这回不是那摇摇摆摆的小船了)。它们的四条腿被精钢打造的链条锁在甲板,面向大海。海在面前无边无际展开,象站立着看着天空的星星、雨雾、光与暗影,以及不知名动物在海面上喷的壮观水柱。没有一头象知道这是陆地与海洋最巨大哺乳动物的短暂交会,它们被跃出水面的鲸的壮丽打动,一如鲸为象的庄严倾倒。
当夜幕低垂,海上的天空柔和了下来,先是变灰,再变得几乎无色,然后才渐渐浓重成黑。和草原或丛林里的黑夜不同,那远比黑色更深邃,且充满动态,就好像无数的黑色蝴蝶遮蔽天空。象不知道海是否和丛林一样存在着边缘,一如它们也不会知道,满天闪烁的星星其实是类似太阳的恒星。
当象来到这个炎热、气息与故乡丛林有点类似又不尽相同的岛屿后,它们从士兵的表情、作息,以及肢体动作可以看出来,那已不再是随时都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动物的气息。士兵的梦境不是谎言,战火终于远离了。
只是象有时会怨恨起自己的记忆,以及感受其他象经验的能力。在每一天的某些时刻,象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那场让人痛楚的战争里头去,那可能是因为吞食了太多梦里死者留下来的眼珠的关系。
这一个晚上,象梦见自己的子宫里有一头小象,它在那里流着血,身上满是炸弹的碎片。它用长鼻子伸入阴道将它掏出来,那是唯一能拯救它的办法。尚未完全成形的小象用它的鼻子勾住母亲的鼻子,然而因为力量太大,通道却太窄,那被掏出来的小象已然窒息,而母亲的阴户则被碎片割开一道一道的伤口。
日复一日,象被迷乱的梦境折磨,有时不自禁地把头往砖墙上撞,有时用它坚如岩石的头骨,撞向驯象人与士兵。那天清晨,象不分东西地跌进士兵所挖的散兵坑洞里,它感到虚弱、无望,悔恨自己活着,不,象不懂悔恨。
被救起的象放弃进食,它弃绝生命的意志如此强烈,开始硬把魂魄一个个逼出身体。一天清晨,尚未天光的时分,象听到树一样的脚步声。它感到全身舒畅,众多象群的大长老们,以它们的象鼻,温柔、没有犹豫地抚触它的皮肤,深入每一寸的皱褶、眼窝的深处与私处。
象觉得一切都在放松──大地、空气、眉毛、瞳孔、头皮、舌头、耳朵、脸颊、嘴巴、咽喉、眼皮和腿。那四条腿曾带领它步行无数的里程,此刻则已带它到此生的终点。它跪下了右前脚,像一间倾倒的老房子,而后左前脚也跪了下去。它的肛门放松,四条腿随之失去气力,巨石从山上滚落,长长的睫毛遮盖住小而曾经明亮的瞳孔。
从此它再也听不到另一头象为它悼念的、从草原那一端传来的、仿佛寂静雷声的低沉哀音。它将永远踱步在灵薄之狱,那里只有家乡的丛林、高山与激流倒映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