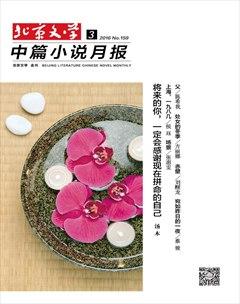创作谈:树梢上结满星星
侯珏
我的故乡深藏在广西北端的一片丘陵地带里。我是宋朝戍边军民的后代,算是桂北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少数民族。在数百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我的祖先们已经向优秀的侗族人民学会吃鱼生、腌酸菜、造木屋、织棉布和唱山歌,但是最近十几年又悉数归还给方志办了。在我九年义务教育的三百个同龄人中,除了三十来个同学考上大学被城市收割而去,其余人据了解,不是去广东进厂制造牛仔裤扣子和手机配件,就是到江浙搞水电装修或者为高楼大厦挖地基。这还算好的,差一点的人若误入传销组织被弄得头晕脑胀两手空空,回到家乡基本可以排进“废人”行列中的最外围一层。
如今的农村,到处都是“废人”,扎堆赌钱是他们最高级的游戏,脑子最精明的人最受人崇拜,他们往往是赌桌中稳坐庄家位置的那两三个人,而我只是混迹在他们中间最有“文化”的一员。在乡下榨油坊里赌钱的这一群农民子弟们,对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根本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开玩笑时从嘴里漏出的故事片段,大部分会成为我的创作素材。我用自己了解的“国情”,加上他们提供的五花八门的“事情”,编制成了小说。《上海,一九八几》就是其中一篇。我想呈现的是农村青年中已经步入城区谋生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很有做人的自觉,也很努力,但是驱动他们生活向前的发动机往往是外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梦想软件是安装在别人脑子里面的。因此,世界如果停电,他们就会一片漆黑。但话又说回来,即便世界漆黑一团,他们也不会愚蠢地去担心地球是否会停止转动。他们的命运就算再不济,也要维持最原始的生存本能或生育责任,这是民族繁衍下去的集体意识。
奔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我孤独地从事写作。我看见城市与时间赛跑,看见农村青年在辛苦地追逐城市的尾巴,看见他们从丰满的梦境回到骨感的现实。我同时还看见村庄前的树梢上结满星星,这是农村的伙伴们所想不到的。他们希望树上结满果子,而我希望星空永远存在。这是我一直关注城乡间游移青年题材的原因,和从事写作的一种责任。在这方面,广西的文学前辈们值得我深入学习。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其它文章
- 父
- 创作谈:“老炮儿”归来
- 处女的冬季
- 创作谈:那一个春末夏初
- 赤壁
- 创作谈:再向青春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