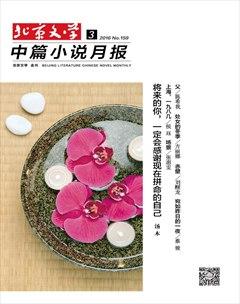创作谈:“老炮儿”归来
陈希我
中国人不喜欢谈“老”,“老”意味着“死”。但“老”又并非“死”,甚至往往“老”而不“死”。我的祖母最后20年是在床上苦熬的,她终于死时,我的心喊着:“好了,好了……”这使我写了小说《母亲》,《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曾经选载过。《父》算是《母亲》的姐妹篇吧!
但《父》写的不只是父亲,是父辈。说起老人问题,常有人说是世界性问题,但在“中国特色”的中国,也具有“中国特色”。美国朋友约翰·威尔逊看了《父》,说它写的是“老炮儿”,让我愣了半晌。这并非偶然巧合,我们的父辈都是“老炮儿”。他们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的父辈,尽管经历了种种变故,但仍是传统的中国人。普通中国人从没有像父辈那样在国家强大原则层面上被动员起来,被铸就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集体人格。
这种原则改革开放后实际上还在继续,从“政治革命”置换到“经济革命”是不需要换血的。
《父》最初名字是《雄狮》,雄狮不仅指父亲,还有他的儿子们。很多人看到这小说写的是儿子对老父亲的抛弃,其实还有一群青壮年狮子对垂垂老父的抛弃。有人说这小说写的是“审父”“弑父”,更准确地说是“恶”审“恶”,“恶”弑“恶”,暴父把暴力之血遗传给儿子,暴子以同样的残暴回敬暴父。阿克顿勋爵说:“暴虐统治之后就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小说就是以此结构的。
写作时,我一面被令人发指的黑暗推动着,一面自问:如果是我,如果我老父母自动消失,我会怎样?过去总听父辈喊“上有老,下有小”,但他们父母对他们并没有太多要求。他们的子女,即吾辈,也没那么多事,读书,分配工作,尽管挣得很少,但也自立了。但现在,我们的子女即使刻苦学习,即使努力工作,资源已经被前辈吃光了。同时偏偏又整个社会鼓着饕餮的暴欲。他们是否会成为“小炮儿”?只要暴血延续,“革”父“命”似乎并不难,一如从“政治革命”转换到“经济革命”。“炮儿”永在,离开了的还会归来。这不,《父》的最后,孙子看见爷爷回来了!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其它文章
- 父
- 处女的冬季
- 创作谈:那一个春末夏初
- 赤壁
- 创作谈:再向青春致敬
- 宛如昨日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