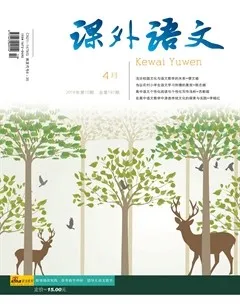清渭浊泾
【摘要】对比论证是议论文论证方法之一。欧阳修的《朋党论》采用了对比论证,把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阐述得泾渭分明,并用大量的史实充分说明了两者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劝谏君王重用君子之朋,远离小人之朋。
【关键词】朋党论;对比;论证
【中图分类号】G733 【文献标识码】A
世上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好与坏,善与恶,真与伪,成与败,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只有通过正反对比,才能深刻阐述事理,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使读者明辨是非曲直,获得正确的思想认识。这就是议论文体常用的论证方法——正反对比论证。它是把两种矛盾或对立的事物加以对照比较,从而推导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作者要表达的观点呼之欲出的论证方法。
因采用对比论证而具有了强烈对比效应的政论文就有很多。贾谊的《过秦论》从回顾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强盛到秦国终因强权酷法失去天下的鲜明对比,告诫汉朝统治者要汲取秦亡的历史教训。同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由于采用了对比论证,使文章具有了超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杜衍、富弼、范仲淹、韩琦等酝酿政治革新,希望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后形成的时弊,遭到朝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舆论上大做文章,污蔑富弼、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是谓“朋党”。
朋党,一般指封建朝廷政治斗争中的帮派。朋党在历朝历代的党派斗争中,败坏政治风气、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最令统治者害怕和仇视,朝臣对此恶名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太史公曰:“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自古以来,“帝王最恶是朋党”(唐·李绛《对宪宗论朋党》),可见朋党之争与朝代更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末的党锢之祸加速了汉王朝的衰亡,牛李党争使晚唐统治日益危机,这些政治斗争的阴霾还未散尽,此时被污蔑为朋党的革新派岂不成为皇权的巨大威胁?皇帝怎能不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保守势力的险恶用心一览无余。
为了国家兴亡治乱,在庆历新政面临危机的情势下,面对政敌的恶意攻击,欧阳修在朝堂上仗义执言,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从理论和历史事实的对比论述中澄清朋党之说,维护支持革新派,希望君主能明辨真伪,权衡是非,重用君子之朋,远离小人之朋,粉碎保守势力置革新派于死地的诛心之论。
但是,要为革新派辩护,就要涉及朋党的话题,也必然会触及皇帝的逆鳞,引起统治者的怀疑和猜忌,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欧阳修没有选择回避,也没有消极地为改革者辩解,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纵观历代政治斗争的实际,开篇直接立论,一击切中要害:“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承认朋党之说从来就有,不是北宋特有的产物,但是朋党也是有区别的,以同道为朋的君子与以同利为朋的小人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人君要能够分辨并区别对待。欧阳修首先变被动为主动,把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在结党的思想基础、目的意义上作了区分,采用排比对偶句式使“同道”与“同利”更显泾渭分明,这一对比的目的是为了让皇帝辨识君子与小人,这既是识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识真伪朋党的基础。你不是怕议朋党吗?我不绕弯子,就谈朋党,使皇帝没有转圜的余地,只得接招。就事论事,不枝不蔓,义正词严,文章的议论因此具有了强劲气势。
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就告诫后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交朋友自然就有交君子之朋与交小人之朋的区别。如果不权衡是非曲直,一概斥之为“朋党”,视如水火,不利于国家的治理,社会的安定,也不能收获人心。所以要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关键在于判别君子与小人是以“道”还是“利”结党,这是衡量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标准。“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小人结党谋求的是利是财,当利益一致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旦为利发生争斗,则互相侵害,甚至是兄弟亲友也会反目成仇。因此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即使有那也是虚假的朋友;君子之朋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志同道合,相互扶持,奉行的是对国家的忠义,爱惜的是名誉气节,同心同德为国家效力。无独有偶,孔子也曾说过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欧阳修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种种表现加以对比,从理论上充分阐述二者的根本区别,两相比较,清渭浊泾,忠奸分明,可见朋党并不可怕,但是要看是什么性质的朋党,皇帝应该任用什么样的朋党,使谈朋党色变的君主对朋党之说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欧阳修顺理成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只有这样,君主才是智慧贤明的君主,这才是真正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君子之朋也才能人尽其才,为国家所用。
写文章不仅要言之有理,还要言之有据。欧阳修接下来列举了六件史实,反复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对比,照应文章开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的论述。“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这里有三个正面史实,三个反面史实。首先从正面列举了尧时,有舜辅佐,斥退共工等结成的小人朋党,重用八元、八恺的君子朋党,国家太平;舜继位后重用二十二个部落首领结成的君子之朋,他们互相赞美、推举和谦让,天下安定;周王朝时,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均受到重用,周也因此而兴的历史事实。反面则列举了商纣王当政的时候,他的臣子各怀异心,不结朋党,但纣也因此而亡国;东汉末年汉桓帝、灵帝两度大肆拘捕和杀害朝中名士(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等到黄巾军起义,汉朝天下大乱,才后悔醒悟,解除对名士的禁令,把他们全部释放出来,但为时已晚,混乱颓败的东汉王朝已经无法挽回了;唐昭宗时期,以党人之争为由将朝廷中的名士加以杀害,有的被投入黄河,还说什么“这帮人自命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进浊流中去”,于是唐朝也随之灭亡的前朝往事。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作者将周王朝任用三千人朋党而兴与商纣王的臣子人心背离作对比,说明只有君子朋党同心同德,才能成为江山社稷柱石,小人朋党离心离德,相互倾轧,是国家灭亡的祸根;将尧舜时期重用君子朋党国家长治久安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昭宗残害名士的行径相比较,说明皇帝信任并重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强大兴盛,反之对君子之朋大肆残害,任意杀戮,最终也逃脱不了亡国的命运。这些历史事例从正面、反面的对比中有力证明了用君子之朋就兴国,滥杀有为之士就亡国的道理,透彻分析了用君子之朋的积极意义,退君子之朋的极大危害,这是历史教训,是前车之鉴,鲜明深刻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和观点,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所以,无论是使人心不一而结成朋党的,没有人比得上商纣王,能禁止好人结为朋党的,没有人比得上汉献帝,能残杀高洁之士结成朋党的,没有哪个像唐昭宗时代了,其结果都使他们的国家遭到灭亡;尧舜能明辨君子与小人,用人不疑,重用贤臣,周武王时三千人为一党,周朝因此兴旺发达。欧阳修意犹未尽,为使文章在论述过程中没有重复累赘之感,这一段欧阳修先反面后正面,用列举的史实作了进一步对比分析,明明白白的对照再次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血的教训是以“兴亡治乱”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是前代名士用自己的生命去诠释的。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欧阳修在文章的结尾,水到渠成得出结论:历朝历代的兴盛与衰亡、安定与混乱的历史事实,做君主应该以此为鉴啊!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大业。请求宋仁宗接纳谏言,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营造一个去伪存真、清明坦荡的朝局,使国家强盛起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关键在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面临亲君子还是亲小人的选择。欧阳修正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使文章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宽广的心胸视野。
文章由于在主要段落均采用正反对比论证,围绕君子之朋、小人之朋的不同从理论到历史事实反复展开论述,层层深入,气势充沛,有理有据,剖析透辟,达到驳斥保守势力的谬论,为革新派鸣不平的目的,使文章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欧阳修写作《朋党论》的出发点是为了劝谏仁宗皇帝,遗憾的是宋仁宗不仅没有被说服和感悟,反而将欧阳修贬谪出帝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参考文献
[1]夏海.品读国学经典[M].北京:三联书店,2014.
[2]朱士钊.古代散文鉴赏[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编辑:马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