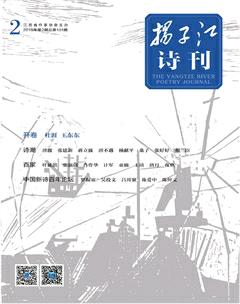[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选
程一身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生于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及画家。出版过戏剧集和多种诗集。被布罗茨基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在圣玛利大学和西印度的牙买加大学读过书,毕业后搬到特立尼达岛居住,并从此成为艺术评论家,在其作品中,探索和沉思加勒比海的历史、政治和民俗、风景,有强烈的历史感。他的诗因“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而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
白鹭
1
细察时间的光,看它经过多久
让清晨的影子拉长在草地上
让潜行的白鹭扭动它们的喙与颈
当你,不是它们,或你和它们,已消失;
因为嘈杂的鹦鹉在日出时发动它们的舰队
因为四月点燃非洲的紫罗兰
在这个鼓声隆隆的世界里它让你疲惫的眼睛突然潮湿
在两个模糊的晶状体后面,日升,日落,
糖尿病在静静地肆虐。
接受这一切,用相称的句子,
用镶嵌每个诗节的雕塑般的结构;
学习明亮的草地如何不设防御
应对白鹭尖利的提问和夜的回答。
2
这些浑身洁白、鸟喙橙黄的白鹭多么优雅,
每只都像一个潜行的水罐,茂密的橄榄林,
雪松抚慰着在雨季里猛烈咆哮的
一条溪流;进入那种平静
超越欲望摆脱悔恨,
或许最终我会到达这里,
棕榈叶在阳光下像轿子一样低垂
伴着下面虎纹般的影子。它们还会
在那里,在我的影子连同它所有的罪孽
逐渐进入遗忘的绿色丛林以后,
连同一百个太阳在圣克鲁斯山谷上空的
升起与降落,那时我爱得多么徒劳。
3
我看着那些巨树在草地边缘摇晃
像没有浪峰的大海起伏,竹林像被绳子
套住的马突然垂下它们的脖子,当黄叶
从振荡的树枝被撕下来,变成一场雪崩;
这一切都发生在骇人的暴雨骤降之前,
天空那湿透的帆布像一次绝望的航行
狂风大作,完全笼罩了山峦
似乎整个山谷成了安然度过风暴的一条船
树林不再是树,而是奔腾的海浪。
当闪电炸裂,雷声吱嘎作响如同诅咒
而你是安全的,躲在圣克鲁斯深处的
一间黑屋里,随着电光熄灭,当前突然消失,
你暗想:“谁会为颤抖的鹰、完美的白鹭
和云色的苍鹭,还有看到黎明虚假的火焰
就恐慌的鹦鹉遮风避雨呢?”
4
这些鸟一直为奥杜邦充当模特,
我年轻时,一本书里的雪鹭
或大白鹭会像翠绿的圣克鲁斯草地
一样显现,深知它们看上去多么美好,
昂首阔步的完美。它们点缀着岛屿
在河畔,在红树林沼泽或牧牛场,
在池塘上滑翔,然后在小母牛光洁的
脊背上保持平衡,或在飓风天气里
逃离灾难,并用它们迅捷的戳击
啄出记号,似乎研究它们是完全的荣耀
在神话般的幻想中
它们扑扇着翅膀从埃及飞越大海
伴随着法老的朱鹭,它橙色的喙和爪
呈现的轮廓安静地装饰着墓穴,
随后它们展翅起飞,扑扇得越来越快,
它们扑扇翅膀时就像六翼天使。
5
那永恒的理想是惊奇。
凉爽的绿草地,安静的树,那边山丘上的
丛林,接着,一只白鹭的白色喘息使
飞行进入画面,然后它笨拙的步子
摇摇晃晃地停下,站直,一枚白鹭徽章!
另一种思想的惊奇:一只鹰站在
树枝的弯处,悄无声息,像一只猎鹰,
突然冲上天空,在赞美或责备之上盘旋,
带着那种和你相同的极度冷漠,
此刻它落下来,用爪子撕扯一只田鼠。
草地的页面和这打开的页面是相同的,
一只白鹭使这页面惊奇,那只高空的鹰
对着死物尖叫,一种纯粹是虐待的爱。
6
圣诞周过了一半,我还不曾看见它们,
那些白鹭,没有人告诉我它们为什么消失了,
但此刻它们随这场雨返回,橙黄的喙,
粉红的腿,尖尖的头,回到草地上
过去它们常常在这里沐浴圣克鲁斯山谷
清澈无尽的雨丝,下雨时,雨珠不断落在
雪松上,直到它使旷野一片模糊。
这些白鹭拥有瀑布的颜色,云的
颜色。有些朋友,我已所剩不多,
即将辞世,而这些白鹭在雨中漫步
似乎死亡对它们毫无影响,或者它们像
突临的天使升起,飞行,然后又落下。
有时那些山峦就像朋友一样
自行缓缓消失了,而我高兴的是
此刻他们又回来了,像怀念,像祈祷。
7
伴着一片正落入林中的叶子的悠闲
浅黄对着碧绿旋转——我的结局。
不久将是旱季,群山会呈现锈色,
白鹭上下扭动它们的脖子,弯曲起伏,
在雨后捕食虫子和蛴螬;
有时直立如保龄球瓶,它们站着
像从高山剥落的棉絮条;
随后当它们缓缓移动时,它们移动这只手
用双脚张开的趾,用前倾的脖子。
我们共有一种本能:贪婪喂养
我钢笔的鸟嘴,叼起扭动的昆虫
像叼起名词并把它们咽下去,钢笔尖在阅读
当它书写时,愤怒地甩掉它的鸟嘴拒绝的。
选择是白鹭教导的要义
在开阔的草地上,当它们专心安静阅读时
头不断点着,一种难以言传的语言。
8
我们在圣克洛伊一个朋友家的游泳池边
约瑟夫和我正在交谈;他忽然停了下来,
我本希望他会享受这次访问,
喘了口气,指出——并非静止或潜行
而是固定在这棵大果树里——这使他震动的一幕
“就像博斯的某件画作。”他说。那只大鸟
突然出现在那里,或许带走他的是同一只,
一只忧郁的白鹭或苍鹭;说不出的话总是
伴随着我们,像欧迈俄斯,第三个同伴
而捕获他——他爱雪——给他鼓舞的
是那只鸟,泛着幽灵似的白光。
如今每当正午或傍晚,在草地上
白鹭们结伴静静地向高处飞翔,
或者像赛船那样航向海绿色的草地,
它们是天使般美丽的灵魂,像约瑟夫一样。
致我的敌人
愿我的敌人随这些波浪安静下来
因为它们是美的即使对他的邪恶来说,
愿这场细雨是对他心灵的祝福
就像它是对我的;他们在这里说那个恶魔
鞭打他的妻子当阳光照彻细微
细微的雨丝。并非我的心宽恕
我的敌人他可恶的肉体欲望
而是一片叶子的闪光,一只有斑点的鸽子的疾飞,
浪花列队行进的白色法衣溅入港湾
如同忏悔者进入放着圣餐桌蕾丝的圆屋顶;
因此美塑造的既非惩罚也非救赎
就像我的敌人的教堂的教义,摔跤的
小天使和痛苦的圣人的大教堂
以及缤纷的紫色云;尽管我有理由
我会和敌人分享这个世界的美
即使他们的贪婪毁坏了我亚当岛的
天真。我的敌人好像壁画里的
一条大蛇,他所有的
鳞片、毒液、闪光的脑袋都是
这个岛的美的一部分;他无须忏悔。
七十七岁
什么,你在七十七岁时会成为超人?
减轻你的体重?好。你已减掉七磅,
但你也减掉了对天堂的信仰
当亲爱的朋友辞世时。他还在巡视,
邮递员,割草者,巴兹尔,无论你叫他什么——
骑自行车的人在星期天静静锻炼
沿着一条洒满木麻黄条形影子的街道
泡沫崩散在防波堤的墙上。我
确信人人皆知它迟早会发生,
游艇,在所有船坞里点头赞同,
身着教士服的黑鹂,青蛙断断续续的赞歌,
再减掉七磅,你将需要一口细长的棺材。
你承受着奇痒,它在你的脖子和前臂上
引发红肿,因此现在你一大早
就去游泳以避开太阳;恐惧融化
在黎明的美之前,尽管咳嗽着。
在海滨
丛林中一匹母马的红褐色臀部,
她在一声发抖的嘶鸣中伸直的脖子
从乌切洛或马里尼的画中径直伸出,
这个饱含希望的清晨在通往海滩的路上。
一场美妙的薄雾把我带到别处——
这雾气意味着梦奇在下雨,
也许在鹅卵石街道上(记忆在此停顿)。
那个面对锡拉库萨的海滨旅馆叫什么?
它会浮现像她的颧骨,她面孔的
天生对称,都会浮现,
我祈求的谜一般的事物将会失去,
那被激起如低音大提琴一般的声音,
和滨海大道的名字……帮帮我,缪斯。
谁想到这会发生,那褪色的
黄色旅馆,以及此刻,天哪!她的名字?
只有海滨的阳光保持原样
对一位海滩上的老人来说,波浪已不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