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她的幸福世人不懂
○彩 霞
十年,她的幸福世人不懂
○彩霞

愿陪伴服侍到终生
“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1932年10月20日,父亲买回的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让住在南通娘家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震惊了。令她震惊的,不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三个字,而是报纸上刊登的照片,那分明是自己的丈夫李老先生。
“难道他就是陈独秀?”潘兰珍几乎晕倒在地。她流着泪喃喃自语:“李先生,你这个李老头,原来你是陈独秀!”沉浸在回忆里,眼泪把报纸打湿一大片,她竟全然不知。
美丽是一场劫难,十七八岁的花样年纪,出身贫苦人家、在上海无依无靠的潘兰珍被一个工头纠缠、强占,忍受着非人的折磨。两年前,22岁的她终于逃脱恶棍的魔爪,孤身租住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后楼的亭子间里。曾经的遭遇,让她对男人有一种本能的防备。
然而,下班途中,当朴实善良的她看到一个“身穿破旧长袍,脖子里绕着条围巾,礼帽扔在了一边,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可怜老头蜷缩在路边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同时,她也认出,他是住在前楼的邻居。
在潘兰珍的小屋里,看到身材娇小、圆脸大眼、举止有些拘谨的她时,苏醒过来的陈独秀自我介绍:“我姓李,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为生。”同病相怜,潘兰珍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陈独秀的内心,则百感交集。
这样的温暖,久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总书纪职务被撤消,党籍被开除,两个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蒋介石正悬赏三万大洋到处缉拿他。血雨腥风中,他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胃病不时来袭,买药的途中不幸晕倒在地,来自这个陌生女子的温情,让陈独秀冰冷的心生出了些许暖意。
楼前楼后,两人不时碰面。看到他博学多才、整天奋笔疾书,没有读过书的潘兰珍崇敬不已,她满含敬意地称呼他“李老先生”。他孤苦伶仃,她便照顾他,包揽了他的家务,渐渐地,两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说笑。空闲的时候,他教她读书识字,唱歌诵诗。在他的启蒙指导下,她很快就能对着报纸读上几句了。
令潘兰珍喜悦的是,这位看似潦倒的李老先生,骨子里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儒雅和热情。他唤起了她的女性自尊心,他的关爱,让她逐渐走出了饱受创伤的心理阴影。
悉心的照料,和谐的相处,身体和精神重新振作,陈独秀也和之前判若两人。“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在政治失意、人生跌入低谷的最艰难时期,是潘兰珍,让他意外收获了家庭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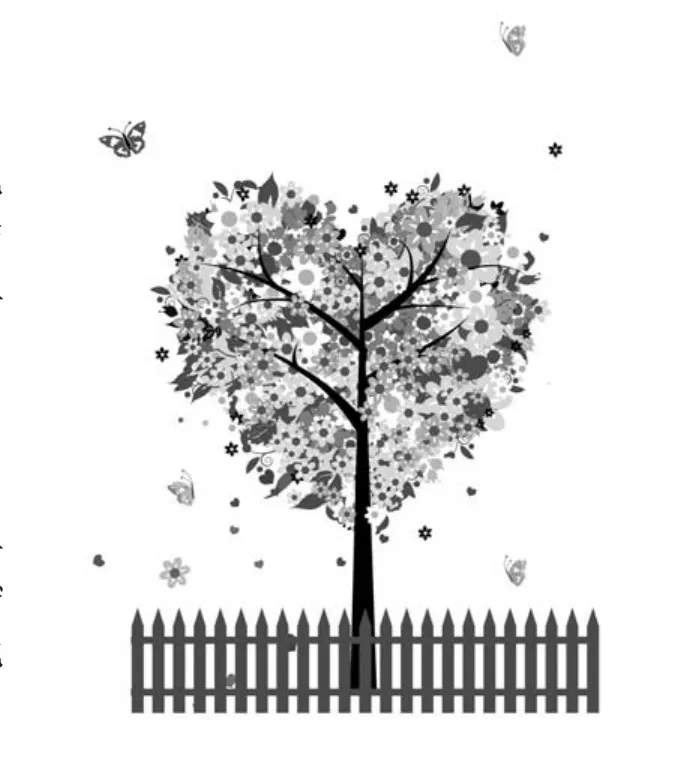
外人眼里,他们的关系像父女、像师生,对比自己小29岁的潘兰珍,一向不羁的他只有感激和敬重。然而潘兰珍的感情却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他明事理、谈吐不俗、待人平等,这些都给了她全新的感受,和他在一起,她的内心安全、笃定。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向他表白。
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陈独秀也喜欢上了这个遭遇坎坷纯朴善良的姑娘,但前途渺茫、自身难保,他又能给她什么呢?惊讶于她的勇气的同时,他劝她慎重考虑。
“只要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服侍到终生。”就这样,在邻居大姐的见证下,他们正式结为夫妻。尽管,除了姓李,潘兰珍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
婚后,除了上班,潘兰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李老先生身上。他的行踪,她从来不问;他没有收入,她就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撑起小小的家。生活虽清苦,两颗孤寂的灵魂却有了依托,她珍惜这简单的、来之不易的幸福。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她怎么也想不到,一起生活了两年的丈夫竟然是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共党要犯”陈独秀。
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曾发表宏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产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对于监狱,他并不陌生,也不惧怕,押解途中,他悲哀地想:也许这一生再也见不到兰珍了,夫妻一场,我连真姓名都没有告诉她,她那么年轻,还会要我这个身陷囹圄的老头子吗?
而此时,安顿好女儿的潘兰珍已经在奔赴南京的路上了。不管他是李老先生还是陈独秀,他都是她的丈夫,无论如何,她都要陪伴他。
作为“危害民国”的政治犯,监狱为陈独秀“量身定制”了“三不准”: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几天后,狱中的陈独秀收到一张纸条,写着“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传达人说,是一女子,自称是他的家属。凭感觉,陈独秀知道,是潘兰珍来了。那晚,他多喝了两碗稀饭。
以绝食抗议,“三不准”终成“三允许”。潘兰珍的到来让陈独秀既欣慰又难过,连累了她,他非常歉疚,自己的被捕,对于苦难之中的她,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刻,潘兰珍是他唯一的牵挂。在狱中,他多次写信给好友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一生叛逆、耿介固执的陈独秀,对于这份感情的愧疚和不安,令人动容。他甚至希望她从此离开他、忘记他,免得为此受到牵连。
然而潘兰珍心意已决,生活的艰辛磨炼了她倔强的性格。陈独秀判刑后,她辞掉上海的工作,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执意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
1933年夏天,南京老虎桥监狱,潘兰珍终于见到了陈独秀。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潘兰珍未语泪先流:“侬究竟是什么人?”他叹息一声答:“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无需更多的解释,只这一句,就够了。
十年无悔
潘兰珍的不离不弃感动了典狱长,再加上宋美龄及一些国民党高官对陈独秀的探视,陈独秀在狱中相对自由。他把监狱变成了研究室,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堆满了经史子集。他读书看报、著书立说,研究文字的同时还自学起了德语。她则天天探监,为他洗衣送饭,整理诗作,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给别人缝补洗涮维持生计的同时,她充当了他的腿,采购他需要的书籍,联络各项事宜,全力以赴支持他写作。
与他相伴,监狱就是家。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时候,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逃过一劫。他劝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可她说:“死就死在一块儿吧。”
有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陈独秀以多病之躯写出等身著作。其中,由蔡元培亲自作序的《独秀文存》第九版,后被评为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时人评说,“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陈独秀丰硕的学术成果,潘兰珍功不可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政治犯被提前释放。蒋介石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他严词拒绝;胡适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也婉拒了。生活再困窘,仍是铮铮铁骨,潘兰珍敬佩他的风骨,始终无怨无悔,相伴左右。
“老先生,阿拉听侬的。”他走到哪,她就陪到哪。跟随陈独秀来到四川时,恰逢他的三子松年带着祖母、妻子和孩子也流亡到四川,一家六口住在一起。潘兰珍对陈独秀的养母极其孝敬,为其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深得婆母赞赏。艰难的日子曾一度无米下锅,她悄悄当掉自己的戒指和耳环,用无私的爱撑起这个多灾多难的家,让他得以尽孝尽慈。
潘兰珍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许多年后,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他们隐居在江津城外的石墙院。在这里,潘兰珍开荒种菜,学着当地农民种些土豆、南瓜。夏天,她用锯木屑和药粉制成蚊香,为他驱赶蚊蝇;冬天,他的手冷得无法握笔,她就亲手制作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烤手。这期间,“除却文章无嗜好”的陈独秀整理完成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为后人留下“语言学方面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多舛的命运里,她就像别在他衣襟上的一朵花,静静地散发芳香。
1942年,多年的贫困潦倒以致病情加重,病魔没有同情潘兰珍“救救侬老先生”的泣血呼喊,5月27日,陈独秀含恨离世,临终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一首诗道尽陈独秀一生。那一年,他63岁,而潘兰珍,仅仅34岁。
整整十年,风雨与共,留在她记忆里的却多是甜蜜。她犹记得,他教她写字,写得好时,他学着她的上海腔说:“阿珍,侬写得蛮好嘛,可以拿去卖钞票。”她睡觉时踢掉了被子,正在写作的他放下笔,为她盖好,摇头笑笑说:“真像个伢子。”
十年,她的幸福,世人不懂。十年,无悔。
(编辑张秀格gegepretty@163.com)
他像阳光,洒入她幽深的井
王敏彤又名完颜立童记,满州人,曾祖父是军机大臣,外祖父是满清贝勒,母亲是乾隆皇帝的后人。虽然她出生时,大清已经风雨飘摇,但她依然是那个时代尊荣无限的格格。
她漂亮、温婉,一举手一投足,皆是大家闺秀风范,自幼便深得父母宠爱,亲朋称赞她像一颗耀眼的明珠。
若不是遇到溥仪,或许她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番光景,可命运有时候,就是喜欢在不恰当时,把不恰当的人推到面前。
王敏彤的表姐婉容嫁给了溥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那年,婉容和溥仪只有16岁,而王敏彤,不过是一个9岁女孩。她只能用仰视的目光,站在一角,看着他们。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溥仪,原来他一点都不古板迂腐,也没有生杀予夺的霸气,有的只是一张文静的脸,一抹如清晨露珠般清澈的笑容,像邻家哥哥,让人忍不住想亲近。
此后,她真的有了很多亲近他的机会。去皇宫看望表姐时,会碰上他正握着她的手,抵头相依,共看一本有趣的书。用餐时,他姿态优雅,西装上没有一丝皱褶。他会对着她友善微笑,会忽然蹦出几句幽默话,逗得她忍俊不禁。他有时也会愁眉不展,为政事忧心伤神。
他的一举一动,像一缕缕阳光,洒进幽深的井里。她对他,由仰慕到崇拜,又变成喜爱,最后,不知不觉变成少女对意中人隐隐绰绰的爱慕。
远远看着他幸福,像欣赏一幅活色生香的画,也是好的。可时局动荡,母亲不得不带着她远遁天津。从此,她与他相隔两地,远远看一眼,也成了奢侈。
在天津,母亲为她订了一门亲事,对方年龄相当,也姓爱新觉罗。点头答应的那刻,她知道,她与溥仪的距离将越来越远。
天翻地覆,遥望他的起伏跌宕
可谁能想到,成亲前,未婚夫与戏子有染,风流韵事闹得满城风雨。这亲事黄了。母亲痛心疾首,所有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王敏彤却轻轻舒了一口气。
这样也好,她就还能保存心底那点痴恋,幻想着有一天,她可以走进溥仪的生命。
命运真的给了她走近溥仪的机会,却是那样让人啼笑皆非。
溥仪的弟弟溥杰离婚后,为了避免他被迫娶日本人为妻,溥仪紧急张罗,要在宗室女子中挑选一人嫁给溥杰。溥仪选中的这个人,正是王敏彤。
在溥仪眼里,王敏彤端庄大方、漂亮温婉,又出身高贵,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可对王敏彤来说,这是无尽的心酸与悲切。原来,他对她,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男女之情。
她想的只是,这样可以解他烦忧,可以离他更近一点。所以,她积极主动地筹备,希望促成此事,希望从此以后,她和爱新觉罗家生死相依。可命运偏偏连这样的机会也要夺去。
因为日本人阻挠,最终,溥杰无奈地娶了日本女子。
从此,大好年华的王敏彤,再也不曾订亲。她像一朵原野上寂寞的花,孤独地开,在镜子中看流年暗换,看容颜渐逝。
窗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她与溥仪再没有机会见面。大清灰飞烟灭,他们都成了新中国最普通的公民。
原以为这一生就这样蹉跎而过,谁曾想,命运再次给了他们相遇的机会。
那年,他53岁,刚从监狱里出来,历经坎坷,一身风霜。她46岁,没有工作,靠变卖旧物和给人缝缝补补维持生计。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那额上的皱纹、松弛的肌肤,那不再光彩照人的脸。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她等了半生,如今他一穷二白,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亲近之人。唯有她,依然深爱他,愿意用余生温暖他。
这一次,再没有什么牵绊,她可以毫无顾忌,不再压抑隐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