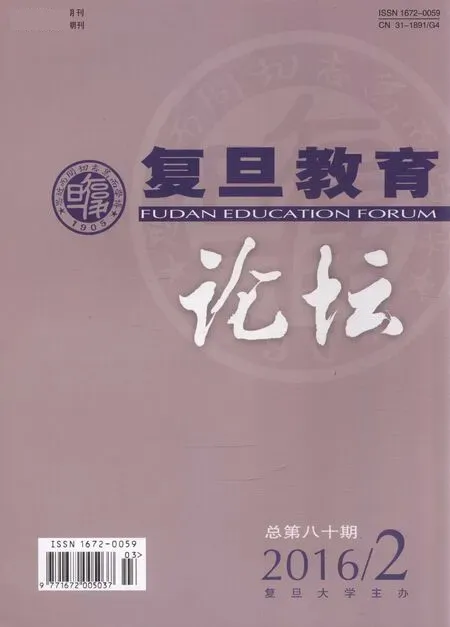论高校学籍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戴国立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200042)
论高校学籍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戴国立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200042)
学籍是学生身份的象征,学籍的注销或开除意味着学生身份的丧失。因此,学籍问题与公民的受教育权紧密相连,关系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高校的学籍管理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学籍的剥夺行为对学生权利影响巨大,超出学校自主权的范围,应当将其纳入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之内。《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规定学生对学校的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学校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诉,但不应将申诉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同时,法院在审查高校的学籍管理行为时,应主要审查其作出行为的依据、程序等是否合法。
学籍管理;受教育权;行政诉讼;司法审查
自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及之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以来,高校教育行政领域产生的纠纷就逐渐进入了司法的视野。当前,对因高校学位授予行为引发的诉讼基本得到了司法的认可,但在学籍管理领域,对于该种行为的性质及其可诉性,各地法院的认识尚不统一。2004年最高法院曾拟就《关于审理教育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规定》(征求意见稿),并考虑在继续研究的基础上尽快颁布出台,以指导各地法院对教育领域司法审查,统一受案和审查标准;但经历十年之久,该规定也未出台,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对受教育权纠纷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未予明确规定。因此,目前仍有从学理上研究学籍管理司法审查的必要。
一、对高校学籍管理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一)学籍管理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
犹如国籍是判断公民身份的标志一样,学籍是判定学生身份的标志。《教育大辞典》将学籍界定为“标志着学生取得参加学习的资格。对学校组织来说则是组织管理学生的客观依据。逾期未办理注册或复学手续,以及因故退学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则丧失学籍。”[1]86学生一旦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某所高校的学籍,学生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也就同时确立,学校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安排教育教学过程、提供教育教学资源、保障学生接受相关教育训练、保障学生各项合法权利。因此,学籍与学生的受教育权密切相关。
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接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从宪法的价值角度而言,受教育权的功能表现在普及教育,为人的文化生活和有尊严的职业生活提供必要基础;推动国家整体文明的提高;通过行使受教育权,社会成员获得建设民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哲学基础。[2]307因此作为一项实现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其本身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既包含了公民在高等教育、义务教育方面的权利,也包含了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权利。从教育体制来划分,还包括了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3]159因此当受教育权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转化到法律层面上时,就相应分化为接受教育、获得物质帮助、取得毕业认证、取得学术认证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而其中较为核心的是公民作为受教育者所应当具备的基础地位,即公民之为学生的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学籍”。高校开除或者注销学生的学籍,实质上是剥夺了学生在该校继续学习的资格。相应地,公民在该校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也就被剥夺。
(二)高校管理行为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①(以下简称《高校管理规定》)第三章的规定,高校学籍管理涉及“入学与注册”“考核与成绩记载”“转专业与转学”“休学与复学”“退学”五方面内容。其中直接涉及学生学籍管理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学生学籍的取得,高校对学生学籍的登记;二是对学籍的剥夺,包括了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进行学习的、入学考试中弄虚作假的、退学等情况。除此之外,《高校管理规定》第五章还将开除学籍作为纪律处分的形式之一。在《高校管理规定》中,对包括开除学籍在内的纪律处分和退学处理规定了内部申诉和行政申诉两种救济途径,对是否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未有明确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规定了,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可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实践中对申诉和诉讼的范围也存在认识不一的情况。虽然行政申诉具有权利救济的作用,但是不能就此即认为高校学生的学籍权益就以此获得了保障。行政申诉毕竟还是一种非正式的救济方式,与行政诉讼抑或与行政复议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现实中高校对学生学籍管理包括行使纪律处分权还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如2002年重庆邮电学院某女大学生因谈恋爱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案和之后的2004年成都某大学两男女大学生因在教室接吻拥抱被学校勒令退学等。[4]96虽然上述两起案件发生于新《高校管理规定》颁布以前,但是即便2005年新的《高校管理规定》明确了对高校学生退学和纪律处分的情形,学校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就能避免裁量过度,在缺乏有效救济的情况下还是存有疑问的。
二、对高校学籍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一)学籍管理行为的性质
依据《高校管理规定》,学籍管理行为从广义上涉及学籍的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转专业与转学、休学与复学、退学、学业完结等六个部分,对之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四种行为:其一,学籍登录行为,即大学对招考入学的学生进行复查后,予以注册并赋予其学籍的行为;其二,学籍剥夺行为,即通过积极作为使学生丧失学籍或丧失取得学籍的资格,如因弄虚作假取得学籍的,大学可以取消其学籍,又如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其入学资格;其三,学籍存续期间的学业管理行为,包含了转学和转专业、成绩考核记载、休学与复学等;其四,颁发学历证书的行为,即按照规定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肄业证书、结业证书的行为。
高校的学籍管理和学历证书颁发及学位授予行为都属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但学籍管理的内容更为宽泛,其贯穿学生学习生涯的全过程,而学位授予及颁发学历证书是对学生学业结果的认可或证明。《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因此,学位授予权并非高校固有,而是属于授权所得,行政法学将其界定为授权行政行为。对高校学籍管理行为究竟属于高校自主权的范围,还是属授权行政行为在认识上尚不统一。
一般认为,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招生录取,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是高校具有一定社会公益职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表现,因而行使的权力是行政权力。从行政行为的概念要件来看,学籍登录行为、学籍存续期间的学业管理行为皆属于事实行为,直接发生事实上的效果,而不发生法律上的效果,[5]23一般不涉及行政诉讼问题。而学籍剥夺行为是剥夺公民的受教育者身份,对公民权利影响较大,已经超出了学校自主权的范围,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
(二)学籍剥夺行为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契合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是1989制定并于2014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方面,较之修订前有了明显扩大,但对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是否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仍未有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高校的学籍管理行为能不能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从这样两方面来考虑:一是,高校自主权与学籍管理之间的关系。前述已提到,高校对学生学籍管理易产生争议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学籍的剥夺上,既包括退学所造成的学籍丧失,也包括取消入学资格和开除学籍所造成的学籍褫夺。而高校学籍管理不仅包括了学籍的剥夺,还包括了学籍登记、成绩考核、休学复学等。对于学籍剥夺之外的学籍管理行为,自然属于高校的自主权范围,司法不应过多干预,这是各国司法审查的惯常做法。如日本最高法院在富士大学案件中认为:“大学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以教育学生与学术研究作为目的的教育研究设施,即使在法令没有规定为了实现该大学设置的目的的必要事项的情况下,学校具有制定学校规则等规定的自律性职能,形成与一般市民社会所不同的特殊的部分社会。”这就是日本司法审查排除范围中的“部分社会论”,但是对具有自律性法律规范的部分社会行为,如对于从该部分社会排除其构成人员的行为、实现该部分社会终极目的的行为、与人权具有密切联系的行为等则属于司法审查的对象,其中也包括大学对学生的惩戒处分。[6]87因此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应仅涉及学籍的剥夺,对于其他学籍管理行为或是纪律处分则没有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
二是,学籍剥夺与公法上人身利益的关系。《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列举和概括两种方式总结了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笔者以为学籍剥夺虽不属于明确列举的12项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种,但可以视为第12项规定的“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概括范围内。有的学者指出:“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行政行为,……这类行政行为主要涉及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受教育权利、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利等。这类权利并非一概排除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是否属于受案范围应当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7]127将受教育权笼统地归入“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利值得商榷。受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本身具有包容性,当其从基本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时,也就由权利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其一。其二,《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概念沿用的是民法上的概念,其中人身权包含了人格权和身份权两个方面,而身份权又可以分为亲属身份权和非亲属身份权,非亲属身份权包含了非亲监护、知识产权身份权等。[8]379可见以民法理论涵摄行政诉讼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实中行政诉讼受案的一些情况早已经超出了一般民事意义上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如对调整连续工龄决定的审查。一方面,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考量已经超出了权利范围,涵盖了对“合法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考量标准还涉及公法调整领域的扩展和变化。因此从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来考量学籍剥夺行为的可诉性,则可以将学籍视为一种公法上的“身份利益”。学籍就是“作为受教育者的身份”,②强调学籍的身份意义其实就是强调学校的公共行政属性;相应的“学位”学术称号本身也是一种身份,是公民的一种学术身份,因此也属于人身利益的范畴,因而具有可诉性,这点是以往学位行政诉讼中所没有论证的。
三、剥夺学籍行为的救济方式及行政诉讼审查的重点
(一)行政诉讼与其他救济方式
依据2005年颁布实施的《高校管理规定》,对剥夺学籍的情况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取消入学资格,是指高校新生报到后三个月内复查不通过的,或因身体健康原因保留入学资格一年,在一年内经体检复查仍不通过的。这一阶段学生虽不具有学籍,但取消入学资格与学籍的剥夺具有同质性。二是,取消学籍,在通过入学复查取得学籍后,发现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而取得学籍的情况,学校应取消学籍,或是在休学期满后未提出复学申请,或复学申请未通过复查的。三是,基于退学而自动丧失学籍。四是,开除学籍,即作为纪律处分的一种,在七种情况下学校可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
对前述第一、第二类情况《高校管理规定》未明确规定内部或外部救济途径,在此种情况下学生应当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例如,江苏警官学院某学生在入学取得学籍后,经举报被查出在入学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后被江苏警官学院取消学籍。该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并作出了判决。[9]108对于后两种情况,《高校管理规定》中明确学生可以在收到决定后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对委员会的申诉处理不服的,可以向高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的申诉处理属于内部救济方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的申诉处理属于何种性质,则不无探讨的余地。2009年复旦大学学生魏某在选修课考试中找人代考,被学校开除学籍。魏某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后不服,向上海市教委申诉。之后对上海市教委处理决定不服,又以市教委为被申请人向教育部申请复议。教育部受理并作出维持决定。魏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该案中魏某寻求救济的途径来看,分别经历了校内申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申诉、教育部复议三种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教育行政部门申诉制度与复议制度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教育行政部门申诉处理与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处理之间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两种申诉制度之间具有独立性。
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的处理是否能改变高校的处分决定或退学决定,还存有疑问。毕竟高校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不是上下级行政关系,高校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不是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而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因此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类似于行政仲裁。对于类似行政仲裁的行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也无前置于诉讼的必要性,也不具有可诉性。而对于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申诉处理,虽然《高校管理规定》中明确经学校申处会处理后,学生才能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但毕竟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不是正式的救济程序,对学生的权利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校内申诉程序是否前置并无决定性意义。而对于行政诉讼而言,如强调校内申诉救济的前置,则一方面须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则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从目前来看这两方面都不满足校内申诉程序前置的要求,另外对于取消入学资格和取消学籍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前置性的程序设置,因此,对于因退学而丧失学籍和开除学籍纪律处分提起行政诉讼,在现有情况下也不应将校内申诉作为前置性程序。
(二)学籍剥夺案件司法审查的重点
对于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学籍剥夺案件,如何进行审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在作出特定行为时属于公法法人。如今尊重大学自主权,防止行政及司法的干预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已经被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但是,我们应当从两方面来理解高校自主权:一方面,为了激发大学的学术创新,提升办学特色,保障学术自由,需要给高校一个自由宽松的办学环境,减少外界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高校的自主权不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自由,高校作出的某些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或者作出的某些严重失范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司法的最终审查。
因此,司法机关对高校自主权的介入应当是有限度的,如果这一限度把握不好就会侵害大学的自主权[10]33-36。笔者认为对于高校学籍管理的司法审查应当把握好以下三点:
1.应当具备正当的程序
大学是一个自治的领域,但是任何自治的领域同样也受到社会基本法治规则的作用和影响。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的职权、依据、内容、程序四项要件中,对大学自治而言程序是首要的审查内容。程序表现为规范认定和事实认定的过程,但程序的实质是通过行为的分化和独立,来实现行为的恣意控制。[11]15-16而对高校剥夺学生学籍的行为,虽然相当一部分实体内容处于大学自治的范畴,但是对决定实体的程序过程依然处于司法的掌控之中。如《高校管理规定》第5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第56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当然《高校管理规定》中对作出学籍剥夺行为的程序规制比较原则,且局限于纪律处分部分。那么对于法院而言,有限度地运用程序性基本原则,有意识地控制高校行为,推进大学自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该是确有必要的。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的一审判决中法院即有意识地运用了程序正当原则,对学位评定程序进行了合理的司法评价,使得该案在高校司法诉讼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在这类案件中有条件的引入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平原则、程序参与原则等,对高校剥夺学籍行为进行审查是很有必要的。
2.平衡法定规范和自律规范
对剥夺学籍行为,在哪些方面属于大学自主权范围,哪些方面属于国家法律法规控制范围,可以从《高校管理规定》中作一初步的界分。对于取消学生入学资格,高校的行为依据是“国家招生规定”。对非自愿退学的五项情形中,四项涉及“学校规定”: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在开除学籍处分的七种情形中有两项涉及的“学校规定”: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秩序,侵害他人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从上述简单的界分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依据“国家规定”对已入学的学生进行复查外,其他的剥夺学籍行为或是要依据学校内部的规定和章程进行,或是没有明确依据何种规范而赋予高校以自主裁量的权力。如退学情形中“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开除学籍规定情形中“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到底什么属于“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什么行为“性质恶劣”,显然是规章赋予高校的判断余地。
因此在剥夺学籍案件中,法院在依据审查中应当确立如下标准,即:对存在法定规范的,应当适用法定规范审查;对适用学校内部规范的行为,应当审查内部规范的合法性,如学校内部规范超越了其管理权限或是侵害了学生的基本权利,法院就不应认可该内部规范的效力。如学校规定学生不得在学校内牵手、接吻,显然既无合法性,也不必要,依据这种内部规范所作出的行为也不能被司法所认同。对于适用何种规范不明确而赋予高校裁量空间的,应当在尊重合理裁量的基础上,对裁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3.学籍剥夺的裁量应符合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控制行政裁量的基本手段,是拘束违法行政权力最有效的原则。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则。该原则要求高校在剥夺学生学籍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几个标准:[12]50-51(1)学生资格剥夺在两可之间的,不应剥夺学生的学籍,在这一点上入学资格的取消较少裁量性,但也应当审慎决定;(2)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不应剥夺学生的学籍,这点尤为体现在纪律处分上;(3)剥夺学籍对学生而言应当与其行为的性质、动机、目的及一贯表现相适应,同时也要兼顾相同情况相同处理的原则。如在“王圣钦不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行政决定案”中,原告与网络上结识的李某发展恋爱关系,后王圣钦提出分手,李某先后两次来学校要求恢复恋爱关系,2007年李某再次来南京要求恢复关系,王圣钦置之不理,李某便乘其不备,从南师大教学楼跳楼自杀身亡。后南师大对王圣钦作出开除学籍处分。[13]551《高校管理规定》第54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予以开除学籍。而所谓“学校规定”则指向《南京师范大学本科学生管理规定(试行)》第95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就这两项规范而言,并未明确何种行为是“严重”的以至于应当开除学籍。而被告南师大认为原告不符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中关于“自尊自爱、自省自律、男女文明交往”的要求,故而援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学生管理规定(试行)》第9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之作出开除学籍处分。显然就原告的行为过错程度而言,对之加以开除学籍处分似乎失之过重,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三)对剥夺学籍行为违法的判决选择
对高校错误的剥夺学生学籍的行为,法院一般应当选择确认判决,在个别情况下可以选择撤销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撤销判决主要针对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当高校作出剥夺学籍行为时,如果违反《高校管理规定》中实体或程序规定,则可以判决撤销高校的相关决定。其他如依据不合法的内部规定、违反正当程序原则、违反比例原则等应当判决确认高校行为无效。撤销判决针对的是一般性的违法,确认无效判决针对的是行政行为的无效,即行为自始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对学生学籍的剥夺,不仅影响到公民作为学生的身份问题,其本质是影响到公民享有和实现其基本权利,对于这种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自该行为成立时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公民也无服从的必要。
总之,学籍作为公民作为受教育者的资格具有基础性。大学是教书育人,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学术机构,其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本身是大学自主权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自主权不能超越法治的限度,更不能随意剥夺学生的学籍而使之丧失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平衡大学自律的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管理相关的制度和规范,更需要向公民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认清学籍对公民的重要性及其权利性质。这有益于我们理清法律关系,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理论。
注释
①2005年3月29日颁布,同年9月1日实施,原1990年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应废止。
②还有人认为,开除学籍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进而侵犯了受教育者已经投入的学费等财产权。(参见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8年行政审判案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557.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牵强,开除学籍可能间接影响公民的财产利益,但不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另外,比如对学生入学资格的取消也不涉及学费,但同样也具有可诉性。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7卷)[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2]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程雁雷.高等教育领域行政法问题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行政法学研究,2006(1).
[5]佑启.论公共行政之发展与行政主体多元化 [J].法学评论,2003(4).
[6]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7]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李锡鹤.民法基本理论若干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9]李雅柳,刘进星.取消学籍不属于行政处罚[J].人民司法,2009(22).
[10]程雁雷.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J].行政法学研究,2000(2).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胡肖华.论学校纪律处分的司法审查[J].法商研究,2000(6).
[13]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8年行政审判案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The Judicial Review of 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 Administ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AI Guo-li
(Faculty of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Graduate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 is the symbol for student identity.The cancellation or dismissal of one's enrollment status means the loss of his or her student identity.Thus,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citizen's right to education,exerts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rights.Due to the broad range of 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 administration,the dismissal of a student from a university exerts huge impact on the rights of a student,which is beyond the scope of university authority.Therefore,the cancellation of 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in court.Regulations on Student Administration for Regular HEIs rules that whether who is unsatisfied with the withdrawal or dismissal from 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he can appeal to the institution o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However,appealing is not a prepositional procedure for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court should put the legality and procedu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t the first place when review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
Student Enrollment Status Administration;Right to Education;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Judicial Review
2015-11-27
戴国立,1982年生,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法学、教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