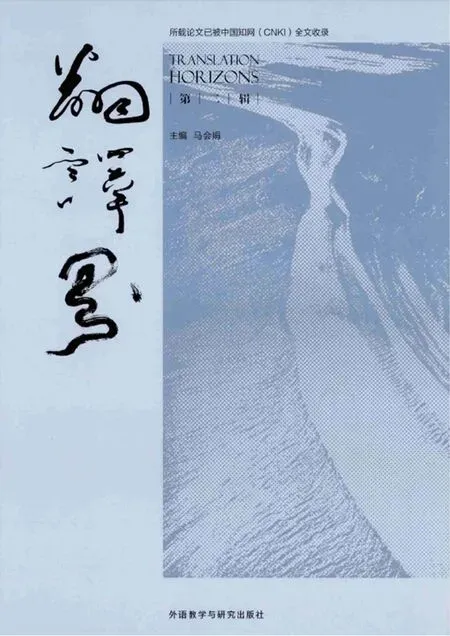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名的翻译暴力探析①
张景华
湖南科技大学
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名的翻译暴力探析①
张景华
湖南科技大学
在清末民初,西学术语汉译的命名面对两种翻译暴力:一种暴力是采用归化的译名,抹杀西学术语的文化差异性,迎合中国学术界的自恋心理;另一种暴力是采用异化的译名,保留其文化差异性,挑战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这两种暴力的根源产生于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传统学术与近代学术的冲突。会通法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可以淡化翻译暴力,调和各种学术思想冲突,但仍然无法避免历史局限性。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翻译暴力的弱化也是译名演变的原因之一。
西学术语;译名;翻译暴力
1.引言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令人瞩目的学术论争当属1910年由章世钊和胡以鲁发起,后有容挺公、朱自清等诸多学者相继加入的译名论战。这场学术论战一直延续到1919年,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当今学界对这场学术论战有不少探讨,如王宏印(2003)、李养龙(2011)、陈福康(2011)、朱志瑜(2013)、孙晓娅(2015)等。但是,学术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关于西学术语译名的论争从清末到民初其实就未曾停止,logic、science、philosophy等术语的翻译都是典型案例。由于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学术迥异,西学术语汉译命名问题甚多,其译名要么准确性不够,如logic译为“名学”;要么缺乏可接受性,如philosophy译为“斐洛索非”;此外,译名演变现象也非常引人注目,如science的译名由“格致”演变为“科学”。所以,从清末到民初,如何实现“准确性”与“可接受性”的辩证统一始终是西学术语汉译命名过程中的难题。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清末民初译名的准确性与可接受性问题,本文拟借鉴后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暴力”概念,从历史语境深入剖析其复杂性。
西方学者如Chamberlain(1988)、Spivak(1992)、Venuti(1995)、Arrojo(1995)等都曾运用“翻译暴力”的概念来分析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冲突、权利关系和文化霸权问题,但对这一概念的术语化贡献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Venuti,Venuti认为翻译暴力“存在于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本身”,主要涉及两种伦理态度:一方面,翻译存在一种归化原文的倾向,即以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抹杀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自恋(Venuti, 1995: 18);另一方面,译者也可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彰显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抵抗和挑战目的语的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同上: 308)。Venuti的论述揭示了两种对立的翻译态度: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而这两种态度根源于相互对立的翻译动机,即民族中心主义与反民族中心主义。Venuti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并将翻译“问题化”,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转换,而关注相关的文化和价值冲突,因此笔者拟借鉴翻译暴力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清末民初译名问题,以期对译名的准确性与可接受性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2.归化的译名与解读的暴力
在Venuti看来,归化翻译在英美文化中一直大行其道,Nida的“动态对等论”就是这种翻译传统的理论代表,主张让译者用目的语的习惯用语来替代源语表达法,以便使译文读者产生“同等反应”,这种翻译策略通常彰显了目的语的“文化价值”,抹杀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Venuti, 1995: 20-21)。归化策略通常对外语文本造成“解读的暴力”,偏离原文的概念甚至歪曲意义(同上: 47-61)。在晚清西学政治术语汉译的译名中,归化现象尤为明显。譬如democracy的翻译,由于中西政体的差异悬殊,当时汉语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述democracy,麦都思(W.Medhurst)的《英汉字典》(1847)沿袭了马礼逊(R.Morrison)的《华英字典》(1823)的译法,将democracy译为“民主”。
晚清知识界将democracy译为“民主”,但其涵义为“民之主”,而不是当今的“民为主”。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1898)中说:“尧舜为民主”,“惟《尧典》特发民主义”1。 1874年《万国公报》中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文章中出现了“美国民主易人”、“选举民主”等词汇2,1890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了华盛顿的像,其副标题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3。这里的“民主”显然是旧义中的“民之主”(熊月之,2011: 79-81)。康有为等晚清士人受经书的影响,认为西方民主政治不过是中国“三代之治”的遗风。在19世纪凡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士人都批判现代“民为主”的概念,所以对于democracy译名的确定,在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下,暴力性解读不可避免,因为译名问题已不单是词语选择的问题,而是两种政治思潮的冲突的表征。
在清末民初社科术语的译名中,对西学术语进行民族中心主义式的解读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将president译为“皇帝”、“头人”或“酋长”。晚清学术界在西学中自然科学术语的翻译上同样无法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化学制剂的ether(乙醚),在《光学》(1876)中的译名是“传光气”4,在《光学须知》(1890)中的译名是“以脱气”5。谭嗣同作为百日维新中著名的六君子之一,他不用“传光气”和“以脱气”作为译名,而选用了“以太”,谭嗣同对这一译名从传统学术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以太”被视为“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的原始建筑材料,是无形,无维、“至大、至精微的”东西。谭嗣同不仅取法佛教的“生 ∕灭”和“不生 ∕ 不灭”来解释ether,而且还引用《易经》中“聚散”和“隐显”来解释“以太”的“生灭”和“轮回”6(谢弗, 2012: 267-80)。当然,这些术语的汉译命名说明晚清知识界对西学的认知过于浅薄,但我们也应更深刻地意识到,在中国近代西学术语的汉译中,译者要面对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传统学术与近代学术的冲突,用中国传统学术概念解读西方近代学术概念的做法不可避免,在译名的生成和解读中,偏离西学术语概念,甚至脱离原意的暴力性解读也屡见不鲜。
3.异化的译名与接受的暴力
为了避免归化翻译的暴力性解读,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确立译名似乎更为可取。从译名的准确性来看,异化的译名似乎也更有利于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诚如朱自清(1919: 41)所指出的,那些不准确的译名“虽是修辞方法高明的很,又有何用?再说,若是我们有了许多确当的学术上译名,国语的科学、哲学等自然会一天一天的发达;世界上新学术、新思想渐渐可以普及到中国来”。但是,异化翻译是否能避免翻译的暴力呢?Venuti认为异化翻译也可能产生暴力,这种翻译为反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在译文的接受过程中这种暴力可能质疑或冲击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Venuti,1995: 309)。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许多西学术语的汉译会涉及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一些异化的译名因为与传统观念相左而无法成为通用术语,“地球”(globe)这一译名在晚清的接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在明末《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文字中,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将拉丁文术语globus译为“地球”(罗其精, 2003: 115-19)。李之藻也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在《请译西洋历法等疏》中提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体皆圆,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徐宗泽, 1949: 254)。“地球”这一译名的学术基础是地圆说,因为“地球”这一译名所持的“地圆说”与传统的“天圆地方”相矛盾,中国知识界到了清末仍视之为“暴力”而没有完全接受这一译名。
“天圆地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地理概念,先秦典籍《周礼》中就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7在《系辞·上》中,“天圆地方”还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和伦理内涵:“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8因而近代地理学术语“地球”进入汉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19世纪70年代,李圭仍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指出:“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9。清末地理学者张继大在《沅湘通艺录》(1897)中则将“地方”和“地圆”各打五十大板,以为均不可信:“谓地方如棋,固难为定论,谓地圆如球,亦有可议论。”10(冯天瑜, 2004: 149-50)所以,“地球”这一译名到19世纪末仍无法为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不能成为通用的地理学术语。
通过对明末西学东渐与清末西学东渐的比较,冯天瑜(2004: 150)痛切地指出:“地球”这一术语以及一系列地理术语入华,“为近代中国研习外域知识,形成正确世界观念的语文条件。但由于旧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语文条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术语与普通名词不同,接受什么样的术语就意味着接受其话语系统,接受“地球”这一术语就等于接受了“地圆说”,“地球”这一译名在清末仍然过于异化,知识界仍然习用“坤舆”、“世界”、“乾坤”等本土词汇对应earth和globe,因为“地球”这一译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地理概念的颠覆。所以,新名词在清末民初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大受挞伐,守旧派人士时常指责新名词是“护过饰非”的工具、“民德堕落”的根源,甚至是“亡国之兆”(屈文生, 2013:93)。由此可见,异化翻译能够创新译名,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新译名会产生翻译暴力,比如constitution之译为“宪法”,public之译为“共和”,这些译介中产生的新名词及其承载的思想对晚清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构成了一种挑战。
4.会通译名与翻译暴力的淡化
清末民初中西学术思想差异悬殊,采取归化策略抑还是异化策略是一个两难问题,梁启超(1897: 18)曾指出:“译书有二弊:一曰循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循西文而梗华读,”这实际上指的是归化翻译的解读问题和异化翻译的接受问题。不过梁启超却在论及至此时给予严复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而且“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相去不远,乃可语于是。近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同上: 18)。梁启超对《瀛寰志略》、《水师章程》等书所载译名俱不满意,唯独赞扬严复,当然是因为严复对《天演论》等西学著作中的术语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思想有深刻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严复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批评的声音也有很多,如邓伟(2010)、时世平(2012)等,韩江洪(2006: 158-68)甚至认为严复的西学术语翻译中有很多“无意识的误读”。但是,高中理(1999)、俞政(2003)、张德让(2010)等却充分肯定了严复在会通中西学术方面的贡献,这种能够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对严复的评价是更为可信的。对于西学翻译的译名问题,严复(1896: 203)曾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可见他也意识到西学术语译名的准确性非常重要,但因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鸿沟,解读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从清末的学术语境来看,严复等将会通法运用于西学术语汉译的定名是非常明智的。严复对所译术语进行了深刻的学术探讨,他使用的会通法在实践上有利于融通中西学术,既能淡化术语解读的暴力,又能淡化术语接受方面的暴力。比如在讨论liberty的译名时,有些人认为应该翻译为“公道”,而严复(1903: 208)认为这不够恰当,并对该词的内涵进行了翔实的考证:
谨案: 里勃而特,原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繇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挂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人被囚,英语曰To lose his liberty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释系狗,曰Set the dog at liberty使狗自由,不得言使狗公道也。
严复在翻译西学术语时采用中西文化相互比较和相互借鉴的方法,一方面尽可能准确翻译原文术语,准确输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减少解读的暴力,正如他在考究liberty的词源、文化精神内涵、词的近义和反义、语境以及用法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它的译名确定为“自繇”,也解释了以“公道”定名不妥的原因。另一方面,他考虑到了近代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在术语的定名上尽可能挖掘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减少接受的暴力,比如他指出中文的“自繇”含有“放诞无拘、肆无忌惮”的贬义,不过他认为这不是“自繇”的本义,因而指明liberty在英文中的含义首先是“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规矩之道,君子所持以平天下者矣”(同上: 209)。严复将西学中的自由平等思想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修身养性之道联系起来,这样的相似性联想确实可以达到“活跃中国文化固有的生机”之目的(高中理, 1999: 49)。为此,考虑到liberty在英文中有selfexistence(自我存在)之意,严复认为这既与道学中的“造化真宰、无极太极”之意相对应,也与佛学中的“自在”对应,“乃言实践一切六如,变幻起灭,独有一物,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以其长存,故称自在”。为此,严复还引用了柳宗元的诗句“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繇”来说明liberty的含义就是汉语的“自由自在”(严复, 1903: 208)。会通法不仅可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而且能够通过中西文化的相互比照实现中西学术思想的交流。由是观之,在中国社会对西学缺乏认知的条件下,严复采取会通法来确定西学术语的译名,在译名的草创时期既可减少对原文术语的解读暴力,也可减少其在目标文化接受中的暴力,算是找到一条基本可行的译介策略。
5.翻译暴力与译名的动态演变
尽管会通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翻译的暴力,促进了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但它用中国固有的学术概念去解读西学近代科学概念,必然牺牲译名的准确性,最终还是无法避免翻译的暴力。随着历史的演变和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它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到了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严复的译名批评越来越多,贺麟(1925: 218)就引用张君劢的话,指出严复“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由此可见,用会通法翻译西学术语有利于译名的接受,但这是以术语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逻辑性为代价的,有学者甚至认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在中国先秦诸子的古典哲学思想方法之上直接嫁接近代科学方法”(高中理,1999: 摘要),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翻译相去甚远,例如他将evolution(进化)译为“天演”,将syllogism(三段论)译为“连珠”,将science(科学)译为“格致”等等。会通法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桎梏,从本质上来看不利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清末民初译名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义演变,这种语义内涵的演变与近代翻译暴力的演化密不可分。“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在佛经汉译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借助汉语固有的词汇来表述佛教术语的含义,使汉语词汇的内涵逐渐变更,造成“汉词佛化”的现象(冯天瑜, 2004: 112-23),比如“功德”原意为功业、德行,如《礼记》中的“有功德于民者”11,在佛经中指的是“施善(功)得福报(德)”。“汉词佛化”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译名草创时期与本土概念妥协,淡化译名接受的暴力,并在词语运用过程中逐渐让佛学理念渗透其中,所以丁福保说:“佛学书中之名词,往往滥觞中土典籍,而后人多昧其所由来(同上: 112)。”清末民初西学术语的许多译名又何尝不是“汉词西化”呢?上文提及的democracy之译为“民主”即是一例。“民主”的内涵是逐渐从“民之主”向“民为主”变迁的。据熊月之(2012: 79-81)考证,1864年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中最早用“民主”译democracy,其中提到“如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12。到戊戌变法前后,还存在“民之主”与“民为主”混用现象,甚至有“君主”和“民主”的争论,及至1902年《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出版,democracy才被明确地译为“民主之国政”,对应英文中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所以,王人博(2006: 33)认为democracy与“民主”的翻译对等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漫长的跨语际话语实践完成的。当democracy对目的语来说不再是一种暴力时,democracy与“民主”才能真正地实现翻译对等。“民主”这一译名的语义演变不但体现了汉字的灵活性,也说明了翻译暴力的变化与译名演变的联系。通过“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可以有效地淡化翻译暴力,使译名及其所承载的西学概念逐渐为本土所接受。从历时比较来看,近代中国学术界在翻译西学术语时时常采用本土术语作为译名,而后在不断译介西学的过程中“别赋新义”,比如economic(经济)、right(权利)、geometry(几何)等译名的厘定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些译名不但促进了汉语的近代化,也潜移默化地传播了西方学术思想。
清末民初译名演变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以新译名替代旧译名。德国学者阿梅龙(Amelong, 2012: 211)发现,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科技界普遍将mechanics这个术语译为“重学”,译者这么做是受“西学中源”的影响所致。阮元(1764-1849)用自鸣钟的原理解释了晚清知识界将mechanics译为“重学”的原因:
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学。重学者,以轻重为学术,凡琪琪皆出乎此。而其作重学以为用者,曰输,曰螺。是以自鸣钟之理则重学也,其用则轮也螺也。……综其理,皆由重以减轻,故曰重学也。此制乃古刻漏之遗,非西洋所能创也。(转引自阿梅龙, 2012: 220)
这段话对西学术语概念的解读暴力是明显的。随着晚清物理学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先前的译名“重学”的内涵不断扩大,学者们发现“重学”这译名不但造成了力学知识体系的混乱,也无法准确表述其分支学科的术语,因此逐渐出现了“力学”这个译名,如statistics(静力学)、dynamics(动力学)、f l uid mechanics(流体力学)等。到1910年左右,李善兰等学者逐渐用“力学”作为其译名(聂馥玲, 郭世荣,2010: 65)。可见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当术语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思想不再被目的语文化视为“暴力”时,运用新术语替代传统术语就成为可能。
无论是“缀华语而别赋新义”,还是以新译名替代旧译名,译名的演变都表明译名规范化既要考虑译名的准确性,又要考虑译名的可接受性。翻译暴力的存在使译名的规范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翻译暴力内涵的演变过程。从清末到民初,logic一词的译名经历了从“名学”、“名辩学”、“辩学”到“逻辑”的演变。严复在翻译的《穆勒名学》中首创音译“逻辑”,却还是沿用“名学”这一旧译名。章士钊曾在1910年发表的《论翻译名义》一文中批评严复不敢大胆采用涵义更为准确的音译名。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严复时代西学翻译的定名之难。其实,严复对术语翻译之准确性之重视并不亚于后世学者,他曾强调“今夫名词,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魏向清, 2012: 142),在他看来,确立译名是西学翻译的关键,如果术语翻译不准确,整个西学翻译事业就迷失了目标,只不过他在中西学术悬殊的背景下以更为现实、理性的态度看待译名问题,对logic译名问题的讨论足见其“一名之得,旬月踌躇”的良苦用心:
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精深广大矣。
严复虽首创音译“逻辑”,但他明白直接音译不仅会质疑中国传统学术,甚至可能促使中国传统学术解体,所以还是选择了与中国传统学术妥协的路径,翻译为“名学”。严复追溯了logic一词的词源,分析了一些学科英文名称与该词的构词关系,指出逻辑学是西学的根本,他明白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logic的译名最终会从“名学”演变为更为准确的“逻辑”,后世学者便可“知其精深广大”。虽然解读的暴力会有损术语概念的准确性,但是接受的暴力也影响着西学译介的效果,这种学术环境使严复意识到西方学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表明他选择的策略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6.结束语
从翻译暴力的角度来探讨清末民初的译名问题,至少可对这一时期译名的准确性与可接受性问题得出以下认识:第一,由于中西学术差异悬殊,清末民初的译名要么产生概念方面的解读暴力,要么给目标文化造成接受的暴力,所以译名要么准确性不够,要么缺乏可接受性;第二,清末民初西学术语的译名往往涉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传统学术与近代学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冲突,所以无论是讨论译名的准确性,还是研究其可接受性,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学术语境;第三,在探讨清末民初译名问题时,学术界对译名的准确性和规范化关注较多,忽视了译名的可接受性与生成译名的话语语境;第四,在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与接受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译名演变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翻译暴力的存在使译名的厘定过程旷日持久。反思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下,我国学术界目前所呼吁的中国学术“走出去”也会面对很多问题:中华术语的外译是否要考虑中西学术思想的差异?我们是否要考虑中华术语外译引起的思想冲突和价值观冲突?除了考虑译名的准确性,是否还要考虑其可接受性?中华术语的外译是否需要经历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清末民初西学术语汉译的翻译史研究或多或少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注释
1.参见(清)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38页。
2.参见《选举民主》,《万国公报》,第316卷,1874年12月19日。
3.参见《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万国公报》(新刊),第22册,1890年11月。
4.参见(清)金楷理(Carl T.Kreyer)、赵元益译:《光学》(Optics),上海:江南制造局,1876年。
5.参见(清)傅兰雅译:《光学须知》,上海:益智书局,1890年。
6.参见(清)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6-307页。
7.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2页。
8.参见(宋)朱熹注:《周易本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9.参见(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313页。
10.参见(清)张继大:《周髀家言地方如棋局论》,载(清)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卷5, 1897年。
11.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12.参见(清)丁题良:《万国公法》,北京:崇实馆,1864年,第13页。
Arrojo, R.(1995).Feminist, “orgasmic”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their contradictions.TradTterm, (2), 67-75.
Chamberlain, L.(1988).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Signs, (13), 454-472.
Simon, S.(1996).Gender in translation.London: Routledge.
Spivak, G.(1992).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In M.Barret & A.Philips (Ed.),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 (pp.177-200).Cambridge:Polity, 1992.
Venuti, L.(1995).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London: Routledge.
Venuti, L.(2013).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London: Routledge.
阿梅龙.(2012).重与力: 晚清对西方力学的接纳.载于郎宓榭(编).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 (2012)(201-242页).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陈福康.(2011).中国译学史.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邓伟.(2010).归化与欧化: 试析清末民初翻译文学语言的建构倾向.文艺研究,(3), 69-74.
冯天瑜.(2004).新语探源.北京: 中华书局.
高中理.(1999).《天演论》与原著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韩江洪.(2006).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贺麟.(1925).严复的翻译.载于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009)(213-246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
李养龙.(2011).20世纪初译名论战的现代解读.外语教学, (3), 106-110.
梁启超.(1897).论译书.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8-20页).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罗其精.(2003).中西大地形状学说考: 兼谈“地球”一词进入汉语的历程.吉首大学学报, (2), 114-19.
聂馥玲, 郭世荣.(2010).晚清西方力学知识体系的译介与传播: 以“重学”一词的使用及其演变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 (2), 65-69.
屈文生.(2013).从词典出发: 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世平.(2012).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5), 79-84.
孙晓娅.(2015).如何为新词命名?文艺研究, (9), 47-57.
王宏印.(2003).中国传统译论的经典诠释.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人博.(2006).庶民的胜利: 中国民主话语考论.中国法学, (3), 30-45.
魏向清.(2012).术语翻译研究导引.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谢弗.(2012).谭嗣同思想中的自然哲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载于郎宓榭(编).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2012)(267-280页).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熊月之.(2011).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宗泽.(1949).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 中华书局.
严复.(1896).《天演论》译例言.载于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009)(202-204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严复.(1903).《群几权界论》译凡例.载于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009)(208-211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
俞政.(2003).严复著译研究.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张德让.(2010).翻译会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朱志瑜等.(2013).中国传统译论.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朱自清.(1919).译名.载于中国翻译协会(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39-58页).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责任编辑 邵雪萍)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学东渐与清末民初译名问题研究”(批准号:13YJC7401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张景华,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硕导。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作者电子邮箱:zhjinghua9064@sina.com